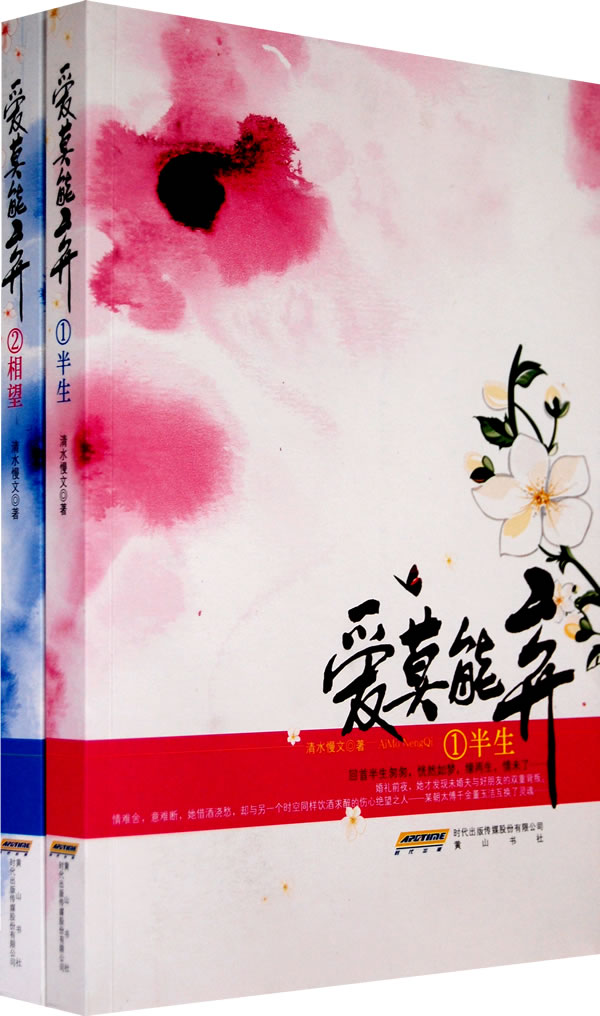这该死的爱-第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好,他才三十岁,可是头发都有白的了,还会吐血,吃饭都会呕吐,你也看见过他,你知道他现在瘦得有多惨,医生都是全天的跟着他,他真的很惨……”眼泪横在张黑脸上,狼狈尽现。
我蹲下身子,对着罗白的脸:“罗白,看着我,他很惨?嗯?我很惨的时候他在哪里?你们这些兄弟口口声声嘴里一个唯少,唯少的叫我着我,暗地里却跟我对着干,什么歹毒的方法你们没用过?那时候你们想过他没有?啊?”我伸出手,解开袖扣挽起袖子露出前臂露出那条白色伤疤:“看见没有?这是当年你们整我的,疯二狗带着一帮人砍我,你们躲在角落里暗笑,我手就差一点点毁了,你们竟然还能跟着李越天帮我收拾疯二狗,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嘲笑我?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嗯?”
我拍拍他的肩,“罗白,干过什么你们心里有数,别逼我全部说出来,这套别来,这比黄鼠狼给鸡拜年更让人难受。”
第七章
站了起来,拿起外套,这出兄弟情深,演得真让人感动,如果我不是曾深陷其中,都要为之喝采了。
拉开门走了出去,回去的车开得有些快,差点闯了红灯,不过还是在临冲过去前踩了刹车,夜色里的灯光点点,霓虹闪耀,我最热血美好的年华,我所有对幸福的憧憬,就是在这个五光十色里城市里被湮灭,我在爱情面前赤裸裸守护着它的美丽,终是输了,我坚持着哭着痛着死心着最后也甘愿认了,我曾想过爱是要让人幸福的,不爱了我也会让他继续幸福下去,只要他乐意。可这个世界,老天不会因你是个好孩子而对有所善待,往往,所遇非人,而偏偏,让你幻灭的也是那个你最爱的人。
终还是,从头至尾,我只有自己才能保护我自己。
等候绿灯时,我打电话给聂闻涛:“我明天八点半的飞机到L市。”
说完静静等着他的回答。
久久,久久,久得我以为听不到回答,那边“嗯”了一声。
我笑了,眼泪从眼角滑下,冰冷的滑下我的脸,绿灯了,后面的车在按着嗽叭,开动车,我微笑,至少,知道这世上还是有人爱着你,真好,寂寞再深悲伤再浓也不会让你孤独到窒息。
寻找新的幸福,代替旧的伤痕,勇气不减,信念不灭,我活着,还是那个站着就能顶天立地的人,我不会错误再继续充斥在我的生命里,即使,我只能挪着我残破的身心一步步的往前走……
在飞机上发现自己高烧,挺着下了飞机,飞机场里那么多的人,却不见任何我认识的人,偌大的场内,我拎着包,拿出烟点上,稳了一口,吐出烟雾。把包甩在肩后,笑笑,向门外走去,找个地儿歇歇吧,烧退了再说。
刚出飞机场,门厅柱子前站着一个人,笔直地站在那里,黑得发蓝的眼睛向我看过来,我向他招手,“过来。”
他不为所动。
我再招呼:“过来。”
他还是不动,只是站着拿着他墨蓝的眼睛带着点不着痕迹的审视看着你,这个男人,这么多眼,眼神还是跟以前一样,要么飘忽,要么凶狠,要么难以琢磨。
我笑,眯着眼睛:“过来,老子要晕了……”我想我至少烧到四十度以上出现头昏眼花了,要不那个男人我怎么看着有两个头了。
我摇摇头,下一刻感觉有人拖住了我的手,有粗糙的手探上我的额头,“妈的”,聂闻涛低咒。
我呵呵直笑,任由他拉着走,像飞着跑似的,包早已被他动作粗鲁但力度不大的手抢过拿着,到了不远处的停车场,我一上车坐着就觉得在飞机上耗着把能量用干了,这时候聂闻涛要是把我拖野外给活埋了我没也力气反抗。
“喝点水。”一瓶水伸到我面前。
我勉强睁开眼,面前的男人还是毫无表情,看不出喜怒哀乐,更看不出有什么担扰,如果我不是知道这人从小到大都这么一号表情,我都会以为我就算真死了他也不会眨下眼。
不过……想起我“葬礼”上这个男人前所未所的惊慌表现,我的嘴就不由得想向上翘。
还好,虽然我不是很了解面前这个男人,但至少,我了解了对我有利的那一方面。
“喝水。”瓶子被放在我的手上,瓶盖已开,我就着喝了两口,偏了偏头要睡:“到了再喊我。”
“系安全带。”硬板板的声音在说。
我实在没力气再理他,把头偏向车窗边,“就这样了。”
一只手伸过来帮我过来扣安全带,带着一股带着温暖的清爽味道。
突然鼻酸,多少年了?时间长得好像这一辈子都是我一个人在照顾自己,就连跟李越天的那些年都是我在照顾他,有多少人真正为我着想?我偏头把眼睛埋在椅背里,这该死的高烧,烧得我跟一女人一样脆弱。
第八章
真是烧得太过,身上湿汗连连,眼皮连抬起都觉得吃力,浑然间察觉聂闻涛停了车打开我这边的车门看着我半晌不动,而后我感觉到我的脸上被一根粗茧的指头挫了挫,我勉强半抬起眼,看见那男人蹲在我前面,面无表情地看着我,那根指头在我抬眼间收了回去。
“起来。”他说。
我想笑,笑得虚弱,这小子,真他妈的有趣,没看见老子连睁眼都困难了么?
“没死就起来。”声音有点不高兴了。
我顿感全身心都充斥着无力感,天,我怎么会觉得这个男人有趣了?这人完全……算了,不予置评,怎么说这也是我的眼光问题,就算是鬼迷心窍了。
我挤了挤喉咙,话一出口竟然是嘶哑的:“背我……”
他又用那种带着审视的眼睛看着我,好一半会,我觉得我眼睛都快支撑不住要闭上了,他伸过来把安全带解开,然后转过身蹲在我前面。
我用尽最后一点的力气把自己扔到他背上,那宽阔的背毫不意外地挡住了我往下倒的身体,他的手从背后伸起来,稳住我,慢慢地站了起来,关上车门,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我眼睛早已闭上,知觉却还灵敏,我知道在背上我的瞬间,那个男人抖了两抖,电光火石间我恍然想起很多年前,这个男人还没有这么宽阔健壮的背时,他用着他瘦小的身子把他的母亲从城外背到城里,而他的母亲在他幼小的身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那紧紧拘住我脚弯处的手越拘越紧,那男人像是在粗喘着气,好像不堪我这个包袱的重力,停下脚步,那人说:“说话。”
我想说话,只是半抬了眼,发现喉咙被火热挡住,张不开声,感觉身上的汗一滴一滴地滴在了他的身上,而那个男人的呼吸越来越严重。
我只能把嘴伸到他耳边,用力张开枯竭的喉咙“快点,找医生……”天,让这个男人在我没被烧死之前找个医生帮我降降温吧,我估计得不错的话,我那颗没按上多久的心脏这时也受刺激了。
老子要晕过去了,丫的,接下是死是活交给他了,最好他别让我死在他手里,要不老子绝对死不瞑目……
眼睛能睁开看见人时,我觉得烧退了我也不怎么高兴,因为我见着了一个光着头却满脸皱纹的老头摇头晃脑地踱着步盯着我看,那眼神活像我是外星人似的。
“醒了?”那怪老头把他的怪头伸到我面前。
天,我竟然能看见那头上有四个戒疤?丫的,老子实在不是想大惊小怪,但我对那四个黑黑的洞实在倒胃口,往后缩了缩,吐了吐口水:“您老,退后点……”嗓子还是有点哑,不过说话不困难了。
“醒来了就好。”那怪老头嘀咕一声,转过身说:“好了,我要走了,以后要是治这小子的话,就不用找我了,不想活的人治了也没用。”
我跟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发现聂闻涛坐在角落里椅子上,还是那种毫无情绪的脸,没有温度的眼睛,此时正对上了那怪老头的眼睛,怪老头肩膀缩了缩,没好气的说: “这小子做了换心手术还百无禁忌,发高烧还灌烈酒,神仙也救不了,我救得了这次救不了下次,别找我,要是死了你会给我好果子吃啊。”
我听了无语,飞机上为了止轻微的恶心就喝了两怀威士忌也给看出来了?
果然人生地不熟,是个人都不把你当回事,例如那个男人……此时就用那种很凶狠的眼神转盯住我。
不过没几秒,那眼神就又回到了怪老头身上,那黑角落里坐着的男人发出的胁迫力果然有点狠,只见那怪老头把手上的医药箱重新放到桌上,转过身气势磅礴地对着老子说:“从今天开始,想要活命,不得喝酒。”
我瞠目结石,看着这个显然是外星人的人,怀疑自己所听到的。
酒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从小就拿着当饮料喝,不要心脏也要酒,我妈都制止不了这理念,虽然家里找不到任何一瓶包括啤酒的含酒精饮料。
我那风华绝代的母亲也就是因为这个不给我钱,连工资都要想着法子藉著名目扣,老子自那以后就无比热爱宴会,因为可以喝到免钱的美酒。
我连这种丢脸没有风度的事都做出来了,就为能喝到我的心肝宝贝们,而这老头,竟然拿老子自己的命来威胁我的命根子?
太扯了。
第九章
撂完这句话,那老头雄赳赳气昂昂的走了,我看了看还扎着吊针的手,翻了翻白眼,得了,让这老头在我面前抖一把吧。
“给我怀水。”我看着屋里头的另一人,然后补充了个字:“请。”
那男人站起身离开房间,我四处打量了下我现呆的地,水泥地板红砖墙,十足的……原生态,身下的床是单人床,被单瞅着还干净,颜色居然是我最喜欢的天蓝色,房间很大,大得单人床在这里面像个小摆设,而房间中间那个大沙包和一堆健身器材,加上那个桌球台子显然占据了这个房间的主要位置。
我用脚趾头想都知道这房间是聂闻涛的,我敢拿我所有财产跟任何人打赌。
他拿着水进来了,很显然,我不能要求它是装在杯子里的,是瓶装水,很显然不打算放我手中,他放到了旁边的那个堆满了杂志报刊的小桌上。
拿过来一拧,嗯,是拧开了的,顺便瞧了瞧那些个书,看到一本杂志的封面上,老子那张笑脸堂而皇之地印上面,我再仔细一瞅,居然是回顾“王双唯”一生的特辑。
“我多少也算一名人啊,算死得其所了。”我调侃下自己,放下水,看着他:“你说我出门要不要整个容?”
聂闻涛哼都没哼一声,走到另一边堆着电脑的地方,坐下开机,从头至尾目不斜视,瞄都不瞄我一眼。
又来这一套?我叹笑,看着那电脑桌底下那个黑色蓝球,怎么瞅着怎么熟悉,这不是我以前用过的那个?不是漏气让我给丢了吗?
我再仔细看看四周,找不到其它的了,要不我还真以为他以前爱跟我屁股后头就为捡些我不要的东西。
我认真想了想要不要跟他提这个球的事,但还是放弃了,好歹也是在人家地盘上,多少也得收敛点。
于是我很客气地问他:“我问你件事啊,其实这事我也早忘了,现想起问你一下,就是当年,嗯,哪年?”我偏了偏佯装想了想,“就是全市高中篮球比赛那年,我高二那会?”我一脸翼望地看着他。
他狐疑带看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