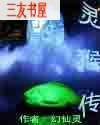贵女薛珂传-第2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程野看着我以极其不雅的姿势挂在墙头,无语半响,方道:“你站这别动,我进去看看。”
结果程野跳进去也没声音了。
“程野你没事吧?”我听不到回应,心里一急,双脚一蹬便不顾一切地跳了进去。
刚起跳,便听见程野沉声道:“陷阱,别进来!”
可是已经晚了,我吧嗒一声,以一条优美的抛物线掉入半人深的烂泥坑里!
上官静、阿史那阙、程野和我,四个人像四只胡萝卜一样栽在烂泥里,面面相觑……
上官静和阿史那阙捶胸大笑。上官静更是贱贱道:“我就是故意不做声,故意不告诉你们这下面是个烂泥坑!哈哈哈!你们果然一个接一个地栽进来了!”
我&程野:“……”
“上官静!我【哔——】你大爷!”我仰天怒吼,随手抓起一把烂泥便往上官静脸上糊去!
结果还没怒吼完,便见一精神矍铄的老大爷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操着鸡毛掸子冲过来,眉须倒竖吼道:“小兔崽子!谁许你们进来的!”
嗯?这声音好耳熟!
我转头一看,手上的泥巴团当即吧嗒一声掉落,上官静亦是惊愕地张大嘴。我回过神来,泪眼汪汪道:“张老爷子,快救我上岸!”
作者有话要说:武崇敏神补刀……哈哈哈!
本来想这章就写到政变的,结果稍稍偏离了……不过张老爷子是政变的一个核心人物,在章末让他出现也是为政变埋伏笔。
且看女主怎么逐个击破!
PS:最先留评的亲我都会给晋江币作奖励,算是对一直支持我的亲们的回馈,看到没~~~~~
、30神龙政变(一)
妈蛋!早知这里是张老爷子的窝,我宁可去跳崖也不会跳进来啊!
程野脱了泥水浸透的裤子,换了身小厮的衣裳,身子如青松般站得笔直,一本正经地对张谏之道:“是我和阿史那阙想偷桃,与她俩无关。”
阿史那阙笑容僵在脸上,炸毛道:“干嘛把我也拉下水!”
“你还说!”我愤愤地瞪着阿史那阙,恨铁不成钢道:“要不是你没见过世面想要吃桃,我们会集体掉进泥坑里么!”
“就是!”上官静一脸沉痛地附和。
“……”须发皆白的张谏之脑门上滴落一颗好大的汗,忍无可忍,抖着满脸菊花褶子训道:“你们都是身居高位的贵族子弟,有事来说便只管走前门,何以做出爬墙这等有失体统之事?万幸桃树下只是个备着挖井的泥坑,若是个粪坑,岂不让全神都笑掉大牙!”
我和上官静对视一眼,汗颜道:“真不是来找您的!我们不知道这是您老的家,若是知道,便是打死也不进……”
还没说完,便见张谏之胡须倒竖,举起梨木拐杖佯作打人状,怒道:“再胡说!”
拐杖举在半空中被程野和阿史那阙一左一右抓住拐杖,张谏之愣了。
张老德高望重,官至宰相,便是太子李显也是他一路打大的,若说张谏之想要教训哪位皇子皇孙,那是无人敢拦,更何况他也并非真的要教训我和上官静,只不过是做做样子。如今却被两个后辈堂而皇之地拦住,张老面子上有些挂不住,虽没说什么,面色却有几分难看。
阿史那阙眯着翡翠眼玩世不恭道:“您息怒,喝口茶先?”
程野放开手,恭敬道:“若是不解气,您尽管打我,别动薛珂。”
闻言,我小小地感动了一把。阿史那阙在我和程野身上扫视几个来回,嘻笑着吹了声口哨。
“来来来,您坐您坐!”我故作殷勤地扶着张老坐在席子上,自己跪坐在一旁,恭恭敬敬地给他上了杯茶,狗腿道:“还是张老聪明!一眼就看出来我爬墙来找您定有要事!”
其实我掉进这院子纯粹就是个误会,压根不知道这是张谏之罢官后的家!不过今儿既然遇见了,有些话早点说出来也无妨,反正有些计划迟早都要实行的。
上官静一头雾水的看着我,我朝她挥挥手,示意闲杂人等一概退出去。
等到房里只剩下我和张谏之了,我才正襟危坐道:“薛珂着人在西街堂口寻了几处房舍兴建学堂,以供神都好学的寒门子弟入学,六月开讲。只是如今还缺了几位先生,不知张相公可有兴趣去讲学?”
张谏之愣了愣,半响才摇头笑道:“你这小妮子,真是好胆!我堂堂一国之相,做了几十年的太子太傅,教出来的都是驰骋天下的皇亲国戚,敢请老夫去市井讲学的,你还真是第一人!”
我大言不惭道:“这不是看您老罢官后太寂寞了嘛!”
张谏之啜了口茶水,道:“你且容老夫好好想想。”
“这个不急,薛珂另有一事请教。”我望着彩瓷杯里漂浮着的茶叶,虚着眼缓缓道:“有一个皇后,在夫病子弱的情况下接过家国重任,治宏贞观,稳住了千秋大业;还有一位皇子,趁着自己的母亲病重时联合当朝宰相,提剑入宫,血洗阶前,逼死母亲取而代之……张相公以为,这两人相比,哪个才是大逆不道?”
我每说一个字,张谏之的面色便要寒上三分,等我说到最后一句时,张谏之已是怒瞪双目,须发颤抖,枯老的手掌经脉暴突,简直要将茶杯捏碎!
茶水从颤抖的杯中溅出,张谏之‘啪’地一声重重放下杯子,厉声道:“治宏贞观?这皇后弑夫杀子、篡位改朝、豢养男宠,罪孽深重!而那皇子只是拿回原本属于他的东西,何罪之有?!”
“属于他的东西?”我拢起袖子,淡淡道:“这天下原本就是天下人的,有能力者居之,什么时候成了私有物了?”
张谏之勃然大怒,甩袖道:“县主,此言大逆不道!”
“言之属实,何逆之有?”我不动如山,淡淡道:“张相公只看到皇后的坏,却不承认她在这深宫六十余载所做的努力,不顾天下百姓安享太平,一言以蔽之,薛珂以为这对皇后太不公平了。”
张谏之老脸涨红,严肃道:“人伦纲常,祖宗之法不可废!”
闻言,我轻笑一声,“其实对于天下人来说,只要过得盛世安稳,没有外忧内患,任谁当皇帝都无所谓。而之所以有人无事生非,找出千种理由万般借口,说到底,不过是嫌她是个女人罢了。”
张谏之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我起身,悠悠道:“天地无疆,而人生苦短,没有谁能千秋万代坐拥江山。时间就是为了改变和消亡而存在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迟早是要被时间抹杀……包括张相公所说的人伦纲常、祖宗之法!”
“你、你这是什么歪理?”
“不是歪理。江山若回到李氏手中,几十年后照样要垮。”
“口出狂言,真是大逆不道!大逆不道!”
“何为道?张相公不妨指给薛珂看看,我逆了哪条道?”我起身,慢吞吞道:“政变逼宫,乃不忠;逼死亲母,乃不孝。张相公您倒说说,您谋划的这等不忠不孝之事,又是走的哪条道?”
张谏之彻底说不出话来了,单手撑在案几上直喘粗气。我又到了杯热茶递到这位浑身发抖的七旬老人面前,面露不忍道:“男宠乱政,该除的还是要除。只要张相公和太子放下执念悬崖勒马,这朝堂依旧太平。”
张谏之费尽力气推开我的手,咬牙不语。
我叹了口气,后退两步道:“晚辈告辞!”
“你等等。”
张谏之叫住我,双手撑在案几上,努力想要撑起自己伛偻的身躯。他望着我,干瘪的嘴唇张了张,良久才咳嗽两声,沙哑着嗓子道:“你那学堂办成后,我去讲学。”
我眼睛一亮,面上却是不动声色,只拢袖长鞠一躬,久久不起身,恭恭敬敬道:“薛珂倒履相迎!”
张谏之沉默着,撑着案几迟缓而僵硬地起身,双目浑浊不复清明,白发干枯凌乱,整个人好像瞬间耗尽了全部生命力,苍老颤巍地好像随时都会倒地而起。
我一时心酸无言。
出了门,看到上官静和程野站在屋檐下望着我,一个面色古怪,一个面容沉重。而阿史那阙站在一旁,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我知道他们多少听到了一些谈话。正想着怎么打破沉默,就见上官静凑过来道:“哎,你跟老头子说什么了,他发这么大火?”
“没什么,不过是学术讨论罢了。”我心情大好,嘻嘻笑道。
上官静一头雾水:“……学术?”
我没理她,只朝程野道:“张谏之以前来找过你?”
程野也不避讳,大方地承认道:“去年找过。我在擂台上赢了倭国武士,之后没多久他便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做太子门客。”
我故作惊奇,打趣道:“那你怎么不答应?”
程野看了我一眼,淡淡道:“呆在你身边比较舒服。”
我乐了。上官静悄悄用肩膀顶了顶我的胳臂,笑道:“行啊,薛珂!还真收服他了?”
“先别管我,说说你自己吧。”我白了她一眼,抬头望天道。
上官静顺手扯了根墙缝里的狗尾巴草叼在嘴里,跟女痞子似的挑眉道:“我有什么好说的!”
我也学她的模样扯了根狗尾巴草,用食中二指夹着,将草杆放在嘴里吸一口,然后做了个吐烟的动作,痞痞道:“说说你,到底喜欢李隆基还是许未央!”
“……”
闻言,一旁的阿史那阙悄悄将身子往我们这边移了一点,狗耳朵竖起。
上官静尴尬,一掌拍上我额头,恼怒道:“胡说八道什么!咱就纯粹的师兄妹关系!”
“不喜欢李隆基?”我无语道:“那去年在祭祀台上,你干嘛拼死为他求情?婉姑姑当时若是没有打你那一巴掌,你恐怕早被五马分尸了!”
“如果那天犯罪的不是李三郎而是许未央,我也一样会挺身而出的!”上官静信誓旦旦,说的好像真的似的。
“哟,多博爱啊!多平等呐!”我叼着狗尾巴草冷哼一声,道:“你觉得你们三儿只是纯粹革命友谊关系,别人可不这么认为!清醒点吧上官静,多情便是无情,再摇摆不定,只会害人害己。”
“你今儿吃错药了?怎么这么烦哪!”上官静一把摔下狗尾巴草,大步朝前不理我。
我也摔下狗尾巴草,伸脚碾了碾,这才在后面负着手优哉游哉道:“离李隆基远点,就当是为了你娘。为了最爱的人而不惜和最亲的人作斗争,那是无傻子才干的事儿。”
“薛珂你怎么这么烦呐!还能不能愉快地做姐妹了?”
我装作没听见,自顾自道:“其实我觉得,阙特勤和你挺配的。”
一旁的阿史那阙忙不迭点头,附和道:“薛大人终于说了一句实在话!”
作者有话要说:暴风雨前的宁静,好多乱七八糟的线索撸不清……摔!
其实从下章开始,差不多就要改变历史了,不能接受改历史的亲慎入!
、31神龙政变(二)
神龙四年八月,盛夏。
我刚洗了头发,正挽着翠花纹的襦裙袖子,眯眼坐在中庭藕池的栏杆上纳凉。太阳镶嵌在湛蓝透亮的空中,暖风夹带着荷香拂来,没一刻钟,披散至腰臀下的长发便自然烘干了,散发着清淡的皂角味儿。
程野从殿前走过,见到我在藕池亭边纳凉,脚步一顿,便转身朝我走来。
他脸上的疤痕淡得几乎看不见了,恢复了原本英俊的面容,但不知为何,他却固执得不肯取下那半边银面具。我有时候觉得那面具于他于我而言,都有着特殊的意义:戴上我送的面具,程野这个人便完全属于我。
带着几分定情的意味。
程野手一撑跃上亭边的栏杆,曲起一条长腿坐在我身边,沉声道:“送你。”
说罢,他朝我摊开手掌。掌心躺着一支檀木制的梅花簪子,酱红色,抛了光,打磨得很平滑匀称。
我接过簪子,翻来覆去看了片刻,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你做的?”
簪子的背面用小篆刻着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