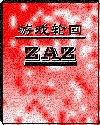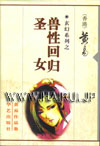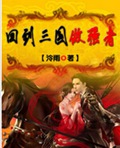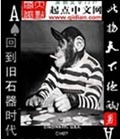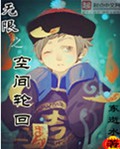春去春又回-第5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谦睦,官千户。时宸濠之乱,皆受其害,兄卒,弟戎之,平乱居功不受,辞帝赏,归家尚武。慕女不得……长斋绣佛。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八章
赤日炎炎,南京图书馆成了除商场和茶餐厅以外广大群众一致好评的消暑圣地,不过人们大多挤在二三楼,四楼的图册馆已见稀寥,七楼古籍部更是空空荡荡,整层楼弥漫着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的安静。
这里借书不仅需要图书证,还得同时抵押身份证,林筝轻手轻脚地站在工作台前,唯恐惊扰了其他人:“您好,我看报纸上讲,你们这里有《吴姬百媚》可以借阅?”
灰色制服的工作人员起身去了书柜,不一会把薄薄两本深蓝色册子交到她手里,林筝心情可谓如获至宝,皆因前天她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消息:
明朝万历年间的奇书《吴姬百媚》神秘现世,因系孤本备受瞩目,藏于国家图书馆,后经由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正式与民众接触。
林筝印象中,最早提到此书的是鲁迅的《集外集拾遗补编》,当时只记得一些很美的书名滑过眼前,诸如《绿窗女史》、《幻中真》、《隔帘花影》……还有这本《吴姬百媚》。
没人说得清这书怎样现世、作者是谁、动机何在,只知道是一本选美图册,全书三十九位江南美女,二十五幅画像,像科举制度那样排名分次,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而且还不止评选了一届。专家称,这本书有着太多太多的谜团,除了书上明确出现的讯息,其余一概无法推测,这种选美活动是青楼文化还是民间风尚?其书是出自当时的文人墨客,还是青楼女子们的一时无聊?是官方的还是自发?是一群人的画集还是一个人的手笔?全都不得而知。
林筝一页一页翻着,画像的线条异常简单,比方景物,有的都是虚勾几笔,勾出个外廓便罢,但却不可思议地风情满纸,其中一张上的女子梳燕尾环髻,小小巧巧的鹅蛋脸,削肩细腰,穿圆领宽袖及地长衫,腰间束一条细软的坠带,不着任何饰物。她一手牵领一名男子,一手微抬,指着嶙峋山石小径,欲往中间而去,笑容于娇憨之中带着戏谑;男子看约四十开外,戴宋朝常见的翅冠,卧蚕眉,穿交领道袍,脸上竟是无比顺从享受的神情,头放松地抬起,肩膀都塌了下去。
另一女子,翘腿坐在竹椅上,裙裾曳地,一手轻架于椅背顺势垂下,一手放在膝头打着拍子,笑意朦胧,微带轻佻之感。
林筝不由生出些感慨,今人以为妓女必浓妆艳抹,满头珠翠,其实从古画看来,她们最迷人的却多为神态韵味——温暖、跳脱、天真烂漫、翘首以待……林筝看着看着,眼前竟幽幽浮出冯小屏那袅娜柔软的身姿。
几年前她在扬州红园结识了一位古玩摊主,他也提到过一本和《吴姬百媚》内容性质非常相似的古书《月照扬花》,书中所载乃是弘治年间的江南美妓,这几年林筝陆续发现,明清时候,才子为名妓撰像写评十分流行,此类书籍流传于世的,还有《闲情女肆》、《青楼韵语》、《金陵妓品》等,《月照扬花》是林筝目前听过,年代最久远的一本。
只可惜无缘得见。
林筝把扬州小屏的照片拿出来,同《吴姬百媚》中状元王赛并排摆在一起,看得出了神。
虽然《月照扬花》已毁于大火,林筝却依然能想象出来在那本书中,冯小屏巧笑倩兮的样子,她甚至能想象出那本书被火苗舔噬时,她躺在艳光中浑不在意地笑着的样子。
林筝发着呆,冷不丁手机震起来,在这屋子里,连震动声都极为明显,她急急忙忙还了书,跑到外面走道。
电话是姑姑打来:“林筝,你不是一直想知道那扇屏风的事?捐赠者回国省亲,现在就在我们博物馆,你要不要来?我多留她一会儿。”
林筝大喜过望:“要!姑姑,千万留住他!”
她回身要了身份证,打车飞奔民俗博物馆。
屏风的捐赠人姓戴,姑姑称她戴女士。林筝被领到会客室门口,来时的雀跃心情此刻全转为了紧张。
她推开门,目光对上一道背影,不由愣了愣。
在林筝概念中,捐赠人应该是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很有可能满头银发,行动迟缓,然而眼前的女子身形高挑,乌黑长发盘成三十年代好莱坞女星流行的髻式,穿了有垫肩的夏季西服,显得肩膀挺拔,而后背像一道袖珍的峭壁;下着包臀过膝鱼尾裙,灰色丝袜,高跟凉鞋,她站在窗前,似乎正翻看着什么相册之类的东西。
林筝愣了好一会儿,直到姑姑端着一套茶具进来。
戴女士回过头,她的容貌感觉比背影看起来还要年轻,雪白的皮肤,胭脂一样红的嘴唇,眼角一粒针尖大小的棕色小痣,林筝不由结巴道:“您是戴、戴……”她想,坏了,该怎么称呼对方,才显得礼貌又亲切呢?
戴女士笑了,合上博物馆年鉴,冲她招招手:“林筝,过来坐。”
她对林筝倒是一点也不生疏。
姑姑寒暄了几句就离开会客室,把空间留给这两个人。
林筝主动表演功夫茶,这是她在博物馆打工期间学会的一项小小技能。戴女士含笑看着,说:“你的手法还挺老到。”
她始终是那么和蔼,林筝也完全放松了,笑着捧起一杯茶,恭恭敬敬递给她。
戴女士喝了一口,点点头,把茶杯放下,说:“我叫戴逢卿,你知道,逢卿是哪两个字吗?”
根本无需思索,林筝下意识就脱口而出:“与卿相逢?”
看到她的微笑,林筝知道自己猜对了。加上她的姓,林筝又说:“等待……与卿相逢?”
戴逢卿微微颔首。她来到世上是为了等一个人?林筝想,她等到了吗?
“我听说你对那扇扬州小屏很感兴趣?”戴逢卿问。
林筝被一提醒,立即兴奋起来,想了想,又有些不确定的问:“您知道屏风上的女人吗?”她生怕戴逢卿说这扇屏风是从旧货市场收来的等等。
还好,戴逢卿给了她肯定的答复:“她叫冯小屏,是弘治年间人,扬州青楼‘扬花尘’红极一时的头牌。而她的这幅像,出自当时扬州名流顾震寒之笔。”
林筝露出了惊讶的神色:“顾震寒?”这是她接触扬州小屏以来,首次听到的名字。
戴逢卿的表情变得有些恍然,带着一丝似有似无的笑意,她侧身靠在沙发扶手上,手肘屈起,指尖轻轻触摸着额头,样子仿佛陷入回忆。
“顾家五代经商,家底殷厚,府上也出过入仕的大人物,成化年间,那位大人物因进言废黜西厂,得罪宦官,被革去功名,不仅如此,子孙后代也不许为官。”
戴逢卿看一眼听得聚精会神的林筝,笑道:“当然了,后来新帝登基,大赦天下,自然也就无视什么子孙后代不许为官这种不讲道理的规定了,只是,顾家子弟似乎深受那位大人物的遭遇影响,觉得伴君如伴虎,个个无心仕途,不是专注于诗画文学,就是拼命做生意。顾震寒就是在这种家庭环境下长大的。”
“他很聪明,才华横溢,又风雅多情,喜欢结交三教九流,不拘世俗,不爱束缚。”戴逢卿微微偏着头,眼神温柔,目光似对着矮几吊兰,却又似乎透过垂花缝隙,望去了很远的地方。
杯中的茶冷了,林筝浑然不觉,好奇问:“他和冯小屏相爱了?”
戴逢卿淡淡一笑,林筝觉得自己问了个蠢问题,好笑道:“那是肯定的,那他们在一起了吗?”
戴逢卿没有回答,却说:“在扬州今天蜀岗一带,曾经有个梅花谷,荒无人烟,谷中有屋三间,有墓冢一座,所葬之人正是冯小屏。”
林筝心头一震。
葬在荒山野岭?
“顾震寒呢?”
“我在一本族谱上找到了他的名字,他明媒正娶的妻子叫孙瑶瑛。”戴逢卿淡淡道,“育有一子一女,男孩叫锦书,女儿叫沁文。”
林筝忽然觉得非常压抑,当场就愣在那里,那种感觉难以言喻。
看她皱起眉头,戴逢卿笑着说:“茶很香,再来一杯吧。”就这样把低靡的气氛化解于无形。
两人喝了几口茶,心头舒缓不少,林筝闷闷说:“我一直有种感觉,我和冯小屏很有缘,也很亲近,没想到她的结局这么不好,真是……有点接受不了。”
戴逢卿笑道:“也不用这么郁闷,林筝,你相信前世今生吗?”
问得林筝呆了呆。
被戴逢卿柔和的目光静静看着,她最终点头:“我信。”
“那就行了,你只要相信,她今生过得很好,想等的人也等到了,圆满无缺,不就得了。”
林筝一阵好笑,明明是安慰敷衍的话,由戴逢卿口中说出来却特别有信服力。
她想起屏风,喃喃自语:“那扬州小屏是谁绣的呢?”绣工了得,精通书画,这样一个绣娘,与冯小屏又是何种渊源?
戴逢卿微笑道:“你跟我来。”
两人离开会客室,来到安置屏风的二层小楼,小楼这些年来已修缮一新,里面光线亮堂,戴逢卿却让林筝关了所有的灯,然后去除保护措施,揭开防水罩布。
一霎那林筝又重温了当年那种感觉——惊鸿一瞥,恍如隔世。她怔怔看着她,知道了这幅画出自顾震寒之手后,林筝此刻再看冯小屏,只觉她那漫不经心的眼底,爱意深藏。
戴逢卿的影子映在了屏风一角:“记得这首诗么?”她问林筝。
林筝不必看也记得清清楚楚:“应该是什么人写给冯小屏的祭诗吧。”她脑子一转,“莫非是顾震寒?”
戴逢卿拉起林筝的手:“你过来,站到我的位置来。”
林筝依言而动,站定后戴逢卿说:“再看。”
她便抬眼看去,奇怪的是,诗言变了。
那八句原诗林筝烂熟于心,明明应为“岭春融冰尽,唁客践祭约。扬花新涧道,拂尘旧冢阶。恍惚终老去,忧伤度休歇。今夜月懂人,思君微如缺。”
什么时候换了样子?
林筝太过惊愕不能开口,眼前所见也是八句诗,却是另八句:
跹蝶应有情,何以花无情。
落花应有情,何以水无情。
流水应多情,安能动山岗?
青山谓无情,脉脉葬仃伶。”
她念了两遍,好似有所触动,却又说不上来那是什么滋味。
“这个秘密发现的人并不多。”戴逢卿柔声说。“你觉得这两首诗,如何?”
“……我,”林筝终于把自己那混乱感觉理出些头绪,喃喃说,“两首诗应是不同的人写的,前一首是悼祭,后一首,似乎是在安慰前一首的作者?”她深呼吸了几下,不可思议地说,“这技法简直神乎其神,我对着屏风那么久,从没发现内里乾坤。”
戴逢卿笑意略深,她站在林筝身后,把手放在她肩头说:“这样的技法,我曾在大英博物馆典藏的一件袍子上见到过一次,那是明朝某个后妃日常起居所穿的一件夏衣;此外,我在美国大都会游学时,结识一位考古学家,他对我说,有一本中国古文献提到了,在正德年间,有一座宁王献给皇帝的乌金沉楠寿屏,也用了同样的隐针法。”
林筝深为震撼,明代妃子的夏衣,正德皇帝的寿屏,假设这些皆出自同一人之手,这名绣娘一定不会是市井普通人物,有极大可能是一位宫廷绣师。
只是,直接服务于天子的手艺人,南北相隔千里,怎会去绣一个扬州妓女的像?她与顾震寒是何渊源?
而这种令人惊赞的技法,又是因何失传?绝迹于世?
林筝百思不得其解,她觉得自己非但没有解开这个谜团,反而越陷越深。
×××
戴逢卿说自己会在国内逗留盘桓数月,筹备一个大型展出,她向林筝要了联系方式,也留下了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