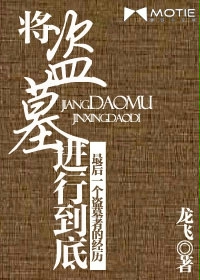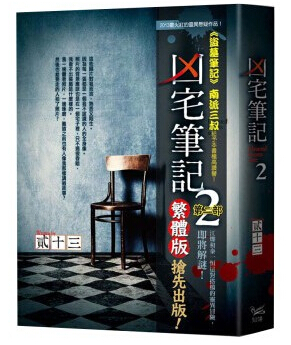盗墓笔记/瓶邪/世界.-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梦到那天后来我回了家,我爸才刮了我两下,爷爷就出声说算了。我爸说老爷子太宠我,爷爷说没关系阿邪知道错了,我爸就没说的了。
又后来,我跟他说对不起,爷爷说没事,其实修也用不着修,自行车这玩意总要坏的,坏了就扔掉好了,反正无论怎么修怎么补,都和原来的不一样了。
梦一直做到了这里,我就醒了。
醒了之后脑子混混的,呆了五秒才反应过来现在的状况,这里只剩我和胖子了。
第六天的时候黑眼镜和三叔其他的伙计都走了,带走了大半的食物和水,黑眼镜也叫我走,我没应。
胖子留了下来,这是一种出生入死后的默契,只可惜现在我没法矫情地去泪流满面这种默契,我固执地等在那里,每天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去那个孔洞下面去看上一眼,像一个疯子在演一场没有休止的荒诞剧。
第七天开始之后的日子里我脑子里不断地会回想起梦到的那件事情,会想起爷爷的话,像一种生理性的暗示,暗示我会失去一些已经习惯了的东西,只是我不知道这次一旦失去了什么东西,我能不能像我爷爷那样潇洒说,既然坏了,就扔掉好了。
第7+N天之后,我从混乱的睡梦中被人推醒,我挣扎着清醒过来,然后看到胖子一脸严肃的样子,脑子里就开始一阵一阵地抽疼。
胖子扳直了我的身体,脸朝着我,往我身后奴了奴嘴巴,说:“小哥回来了,但是他好像有点疯了。”
我心一疼,眼一闭,世界就是一场天旋地转。
老天,这一把,你赢了,我输了。
二十四 挣扎。
张起灵又失忆了。
这几乎是一秒就能得到的答案。
我爬起来,走过去,轻轻拉开他卷在身上的毯子,看到他睁得老大的眼睛和抖动着的嘴,我凑过去,凑到他的嘴边听他说什么,然后听到一句,没有时间了,再一句,没有时间了,还是一句,没有时间了。
我叫他,小哥,小哥。
没反应。
于是我只能很轻很轻地扶起他的头拉到自己脸前,让他的视线里看得到我,我轻拍他的脸,压低了声音,用只有我和他听得到的音量问。
“起……起灵,认得我吗?”
他没有回答,只有始终墨黑的眼睛里空洞茫然的眼神无声地飘散着,像谁也搅不起波澜的死水,别人不能,我也不能。
我深吸一口气,再慢慢地把他的身体放地上,落下的毯子再帮他盖回去,我起身朝胖子撇了撇头说,“给他打镇定剂。”
一针下去,不到三分钟闷油瓶就睡了。
这是吴邪我这辈子唯一的一次直接叫他双字,不过既然他没应,那就算了。
胖子守着闷油瓶入睡之后走过来问我咋办,我头也没抬,忙着在装备堆里找东西,我翻出一截绳子,比划了一下长度还OK,就往身上裹,胖子一看急了,忙问我干啥,我一边忙活着一边凉凉地说了句,“上去看看。”
胖子抓住我说小邪你疯啦,小哥都这样了你上去能干嘛,我懒得跟他辩,直接叫他放手。他不肯,我就冷冷地看着他。他倒也聪明,笑说我不托你上去我看你怎么爬,我冷哼一声说就算我把那边西王母的尸体搬到洞下面踩着我也要爬上去看看。
胖子一脸震惊地看着我说,“小邪,你也疯了么。”
“……”
“冷静点,现在就我们俩了,我们不能乱。”
“我要上去。”
“吴邪!”
“让。我。上。去。”
最终胖子还是拗不过我,在我帮好绳子之后把我托到
了洞口,我一个挺身攀住了洞口的岩壁,使出了吃奶的劲提上了一条腿,刚想再接再厉把另一只脚也卡进来,却没了劲,我手一滑整个人就摔了下来。
“操。”我又四仰八叉地倒在了胖子身上忍不住骂了一句,“妈的老子就不信这个邪,胖子,再来。”我从胖子身上跳起来就嚷着让他继续。
胖子也低骂了一句,还是无奈地又把我送了上去,我再一次憋了口气准备抬脚,啪嗒一声又掉了下来。
“操。”我机械式地骂着,机械式地爬起来,整了整衣服又向胖子甩头,这个时候胖子已经根本不想说话了,直接破罐破摔地过来把我往上一甩,我第三次攀住,可是不到五秒,第三次落下。
我坐起身,擦了擦手上的手汗,再抹了抹脸,又站了起来。
“够了够了。”胖子终于爆发了,“你他妈的别疯了,就你那身板根本就上不去,趁早给爷我死了这条心。”
我没有搭理他,只是淡淡地说,“再来。”
“来你个头!”胖子骂道,“胖爷我才不陪你疯,你爱踩谁踩谁去。”说完他就骂骂咧咧地走开了摆明了不再帮忙。
我叹了一口气,接着抬头掂量了一下天石离开我头顶的高度,又试着跳了两下,决定试试看自己跳不跳的上去。
我跑过去把我们带来的折叠帐篷挖了出来,整整齐齐的叠好叠成一块方的,垫在脚下面,踩上去,深吸一口气就往孔洞里猛的一跳,居然还被我跳上去了,不过只有短短两秒,我又滑下来了。
这一次没有胖子在下面接着我直接摔了个狗□,摔得我脑子一震晕,连习惯性的骂娘都说不出来。结果胖子在十步以外的地方哈哈大笑,我默默地听着,过了半响,我又爬了起来。
我再去找了些东西垫脚,又跳了一次,又摔了一次。然后再晕,再起来,再垫脚,再跳,再摔……
周而复始。
一直到胖子在一边从大笑变成冷笑,再转为叹气,最后也没了声响。我一共跳了大概有8次多,衣服都已经被我摔得磨了口子,我感觉自己已经麻木了,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跳起摔下爬起再跳起这一件事情可以做,而且还不能停,感觉一停下来就会死,一定会死。
第九次,我站在我自己搭的危险物上面又一次使劲地往上跳,不过这个时候我已经真晕了,我连方向都没选对,直接“嘭”地一声脑壳撞顶,跟着整个人仰面朝天地重重地栽回地上。
这一声惊天动地的终于把胖子吓了过来,他大吼一声吴邪,一个箭步冲过来扶起我的头,而我自己已经彻底懵了。
胖子检查了一下我的头,半响之后他说。
“小邪,我们别傻了,成么。”
胖子拉着我的右手想让我坐起来,结果右胳膊传来一阵剧痛让我猛的一缩,胖子一看,撕开我已经裂了口子的衬衫袖子,一道巨大的口子划开了我大半个胳膊,还涓涓地往外冒着血。
胖子一瞅就嚷嚷上了,大叫道,“我操这怎么行,这血流的跟掉眼泪似地敢情不要钱啊。”于是他扔下我的胳膊就去找医疗箱,咋咋呼呼还地骂着我,骂我脑子发热精神错乱,骂我说以前的我可不是这样的,虽然天真是天真了一点,可是从来不逞强,说什么现在又没人拿枪逼着你你起劲个屁啊小哥又看不到也不会醒过来谢谢你……
我坐在原地,默默地听着他骂,愣愣地看着自个胳膊上的伤一股一股地往外流着血。
也好。我在心里跟自己说。
流点血,那至少我自己也就用不着哭了。
二十五 回程。
一天之后,我、胖子、张起灵收拾停当,开始回头往外走。
起初我还不答应,死也不同意丢下陈文锦一个人,胖子只是说你不能拉着小哥给你俩陪葬,我一听就歇菜了,立马就妥协了。
胖子说的很对,其实我应该早在七天以前就已经疯了,疯得左右不分云里雾里,疯得连我还剩什么,还能守住什么都不清不楚了。
我和胖子忙着埋头收拾装备,偶尔抬头瞥见闷油瓶一个人抓这个小包坐在五米开外的石阶上愣愣地发呆,虽然他以前也经常发呆,不过这一次不一样,如果以前他把发呆当生命,那么现在他的生命里应该就只剩下发呆了。
我忙把胖子拉到一边,我对他咬着耳朵说,“胖子,你这一路上别再嘴巴没遮没拦的啊。”
胖子不乐意了,呛了我一句说,“胖爷我哪次说错过话了!”
我指了指闷油瓶说,“我是说别抓着他问东问西,他不问我们就什么都别说,哪怕是张起灵这三个字都给我咽下去别吐出来。”
胖子不解,问这是为毛。
我摇了摇头,无奈地说,“经验。”
的确是经验,失忆人士特有经验。
其实失忆的人本身比谁都痛苦,比谁都着急,比谁都想知道自己是谁,看着别人总是眼巴巴地望着自己总是压力特大,别人如果硬是给自己灌输东西,自己一旦消化不了接受不能,反而会一阵阵的挫败,结果是对那些未知的过去更加的抵触。
我只知道我不是专业的医生,失忆说到底是个病,在有把握治疗之前我不想给张起灵任何的压力,万一不小心压垮了,我找谁讨去?
我三言两语地跟胖子解释了一下,他虽然粗线条但也算能明白其中微妙,叹了口气说他知道了知道了,不追着问就成了,等到了北京给他找家大医院治治。
我看了他一眼,拍着他的肩说,“谢了。”
胖子古古怪怪地瞅了我一眼说,“谢啥?”
我答不上来。
眼前这个是失了忆的闷油瓶,保护他人人有责,我谢个啥。
那我那个呢?那个我一个人的小哥,哪去了?
之后是整整六天六夜的奔波,一路上的经历乏善可陈。起初闷油瓶还需要我们搀扶,后来他渐渐能跟得上我们的步子就开始自己走,他一直没有起色,恍恍惚惚的什么都没有记起来过。我和胖子很有默契地什么都没说,什么都绕开了说,我本不想去跟闷油瓶搭话怕多说多错,胖子却说不能晾他一个人在一旁万一胡思乱想地钻了牛角尖就完了,于是我和他开始轮流抓着闷油瓶念叨一些有的没的,比如说这雨林里的草蜱子太他妈可恶了,比如说那蛇褪下来的蛇皮可是好东西不如带走拿去卖之类的,再不然就问他小哥累么,小哥饿么,搞得像我们这一路是来野炊的不是倒斗来着的。
我没有告诉他他叫张起灵,我也没有告诉他我叫吴邪。
最后我们回到了戈壁上,意外地发现定主卓玛在等我们,更意外的是潘子被扎西救了回来,他虽然时而还有些糊涂但起码性命是保住了,我们在原地跟着他们休息了三天,终于有一种如获新生的感觉。
三天以后我们重新上路,扔掉了帐篷,食物减半,带足了要喝的水开始往回走,四天后走出了魔鬼城的范围,一个礼拜之后到达了公路,联系上了裘德考的人,三十小时之后他们来人将我们救起。
我坐在回程的越野车上,头靠在玻璃上,副驾驶的胖子唱起了歌,用他的破落嗓子唱了一首又一首,一首感慨一首悲凉。
车窗外是滚滚黄沙,跟我来时的黄沙一样豪气冲天,我坐在那里,身旁是蜷缩着的张起灵,我看看他,看看窗外,无话可说。
我挠了挠脑袋,无意间碰到自己左脸这边疯长的鬓发,我愣了一愣,于是慢慢地,慢慢地,用自己的左手把他们全都捋到耳朵后面去,最后压了一压。
“攀登高峰望故乡,黄沙万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