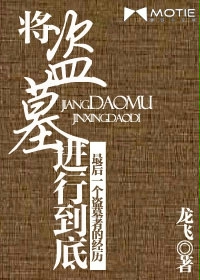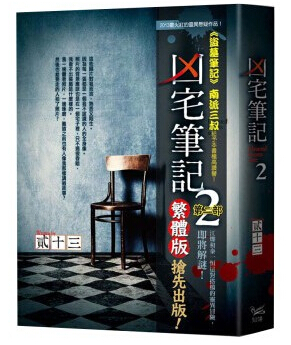��Ĺ�ʼǣ�ƿа������.-��2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ҵ��ڵ��ϣ�����ǰ��������治�ϵ�Ť������ͼ�˲�������ȴ��ôҲ���Ѳ���β���ϵļ�������������£�ʼ�ղ�����Ϊʲô�������������ô�����ʵ������ˣ�������Ľ����ƿ�����ӳ���˧ô��
�����������Ҳ١���������һ�룬��������������֪������Ϊ�Ǹ�ʲô��ƨ���ʻ�����������������ʲô��ʲô�ͳ���Ļ��������������ɻ�Ʊ������ȥ������������
������������ƿû�ӻ�����ȥװ������������ˮ�Ϳ����أ�����������������������ˣ������������������ﱻ����ҧ�ò�����ˣ�����ȥ�����������ϵĶ�����Ҫ����ֹѪ������Լ����֪�������ã�Ҳ�����Ұڲ���ȴһ��δ�ߣ��Ҷ������ۣ�������������ɧ��м�������������
��������������û֨����ȴ�������۾������Dz���һ�ᣬ��ͻȻ��ɫһ�䣬�۾�ٿȻ�ɴ������ң�����а����������ʲô�����𣿡�
������������֪���죬����һ������ֱ�˶�������ʯ̨�DZ�������������������Ū�ö��������ò����ˣ�����ϸ��֮�£���Ҳ������ʯ̨�ĸ����棬�ѹȵ�Զ������һЩϤϤ��������������������Խ��Խ�졣
������������ƿ�ͺ�һ���������ã�����Ⱥ����
������������һ����������һ����ë�������Ҳ٣��������Ȼ���˻�����Ⱥ�����ӣ�����ȥ�����ѻᾪ��������ͬ����������������ɽ�Ǹ���ɽ�ȣ��ж�������ɽ���Ѹ������ɹ��ƣ����Ǹող�Ӧ��ɱ�����ǵģ�ֻ��ϧ����Σ�ڵ�Ϧ˭���軹�ǵ�������¡�
�����������ܡ�������ƿץ����Ťͷ���ܡ������������ˣ��������ֶ���������Ŷ࣬���������ٶȼ��죬�̶̵�ʱ���Ѿ��۽���ʯ̨�����������ӿ��������Ⱥ����СС�������ӣ��е�С��ֻ�ܿ���Ӱ�ӣ��е�ȴ���������׳������ǻ���һ���������࣬����һ�ɺ�ɫ���ˣ�����ǵصġ�
�����������ǻ�ͷһ����֪���������ӵõ�������ɽ���������ѵļң���ȻС����Щѩë��Ӧ�û����Һ�����ƿ��Ѫ������Щ���˾�������һ����������ǿ������������ͷ�����Ǿ������ܿ���סֱ���ܳ��ѹȵķ�Χ�⣬��̼䣬���¾����������ľ���֮�С�
���������������Կ�һ�ۣ������˴��۵�ӳ�����Լ����Һ�Ȼ���һ������Ц�˸�������а��
���������������
�������������������顣��
������������һ˲��������ȼ������
����������Ȼ�����ܵĵ���ƾ��һ�������������վ�����ˣ�����ʱ�����ǵ�����������һ��¹�Ǻ����������ޱȣ����ѹ��л��ơ�
���������Ѿ�������ǰ������Ⱥ��Ȼ�����ת�˷����Լ�����ٶ���Զ����ȥ����ʯ̨�ϵ���ֻҲ���������������صײ���
���������һ���һ�������Ƶľ��������и��֣�����Ȼ��ͷ����Ȼ������ͭ���Ѿ�������Ϣ���ѿ�һ���죬����ɫ�ı�����ʼ���ϵش��ŵ�����ӿ��������ɢ����һ�������IJ����ƹ
������������ƿ����Ҳ���ˣ������������ȴ��������ղ��õ��Ĺ��������ó�һ��ֽһ��ݸ��ң���Ī���ؽӹ�һ���������Ȼд���ĸ��֣������ϣ����š���
������������ƿ˵�����Ǹղ�ѹ�ڹ��������ֽ�������棬�Ǻ��۾��ıʼ���
������������Ҫ��ȥ����˼�𣿡�����ƿ�ʡ�
����������������������һ���ˣ�����ʲô���µġ�����Ц�������ߡ���
����������ץ���ҡ���
�����������š���
����������ʱ���������������������ӣ���ȴץ�������������������һ����ǰ�ܣ��������Ǹ�������һ���������յ���ͭ���ţ�Ȼ�������ԥ�س��˽�ȥ��
�����������ŵ���һɲ�ǣ�ӭ���ҵ���û���ĺڰ�����Ȼ���ϵ����������ˣ���ʧȥ����ʶ��
��������
����ʮ�塡������
����������ʮ��������
�����������Ѿ��ܾã�û���������������ˡ�
���������ҴӺڰ�������������ȴ���ȵط����Ҿ�Ȼ���Լ�����ӡ��������
��������ǽ�ϵ�ʱ����ʾ�������������㲻�����������ҵ��������ϣ�������С���ڹ�̨��ƫ��ͷ���˯���������һ�˰����úܣ�ֻ��ͷ���ĵ����������ת�ţ�����֨��֨�µ�������
���������ҳ��״����������֮��Żع����������Լ�һ�ѣ��۵��Ҳ����ᣬ����Ѹ�ٺ���һ�飬�Ҿ���ˣ������ⲻ���ΰ�����
�������������������������ҵ�Ѳ�����������棬�ҵ����������֮�����Ҳû�иĹ�װ�ޣ�����ĸ�ֶ����������һʱ���濴�������ߡ�������ͣͣ����ȻƳ������ļ����Ϸ���һ�������Ĵ������Ҵ����ȥץ������ϸһ������һ��������������
�����������������ʵ�Ǹ���Ʒ�����������˷���ģ������ֹ����ɣ�������ǰ���Ŷ�����ǰ�и��ͷ������������200��ָ��ҵġ������ҷ����ǵã��ⶫ����05���ʱ�������һ������ˣ�������˱��ͷ�Ҫ�����һ�û������������Ϊ���У��϶����ⶫ���Ǻ���ԭƷ������������������������֣�ȴװ�������⣬�������ĵأ����������ɽ���
����������һ�����������ü��춼����Ц�ѣ�������ô���������ģ���������������ھ�Ȼ�ö˶˵ذ��������ͷһ�Σ���������������ȥ�ˡ�
�����������ܹ�ȥ����ҡ�����ˣ��������켸�¼��ţ���˯�����ʵش��4��18������ô�ˡ������һ�飬�����������ʣ�����05�ꣿ�����ɻ������Dz��Ƿ����ˣ��Ҵ�У���˵����������һ�£�˵��05��û����
����������һ���Դ����������ˣ����Ӵ�Խ�����ˡ�������26������Ĵ��죬����ĺ��ݣ�������ƿ�������Ǽ�����ݡ�
��������ȥ�����̵ģ�ʲô���ռ���ȫ������һȺ����ѭ��ѧ���ɵĻ쵰��
���������Ҵ��ţ������������գ��������µ���Ҫô�ȳɹ���Ҫô��ɱ��������仯����С���ӱ�����Ҫ��ҪЦ����һ˲�䡣�ҿ������泵ˮ������ͷ�ܶ��������¥��¥���ұ���������һ�ж��Ͻ����������·�ֻ����һ���ˣ���һ��ͻأ��ƴͼ����ô�������ڻ���֮�⣬��ʱ���ÿ�Ц���á�
���������������ӣ����ִ����߽����ã�������ؿ���һ����ɫ�̷������������ҵ�ɳ�������컨�壬������һ����̾�˿������߹�ȥ���������ߣ����������������ҡ�
������������̾��һ������ʲô����˵��������
�������������������������ҵ�������������������ߵ�����һ���������۵��������ȥ�����������Լ����������������һ��������ȱ�Ķ��䣬��Ȼ���ﷸ����һ�������������������ͭ�ű�����ʲô����
��������������һ�٣���������ռ�����
�����������ռ���ʲô����
����������������
�������������ˡ������˿�һ��������輸�ϵ�ң�������������Ӱɡ���
�����������ţ��ҹ�������Щ���ӣ���������Щ������������������ӣ��ҿ�ʼ���ϵؿ����Ӵ�ʱ�䣬�����˾ͷԸ����˹ص꣬Ȼ���ȥ��ˣ������պ�Ū�ã��к�ɳ���ϵ��˳Է������˷������˻����ϴ�����ֿ�ʼ�����ӣ�����ϴ�裬Ȼ��˯����
���������ڶ���������ʱ�������������Ҵ��ţ����˲������٣��ҹ�Ѫ��ͷ�ذ�������һ�٣���ʼ�����ĹŶ����ң��ҿ����ܶ��Ѿ����������Ķ����ֶ������ˣ���Ѱ˼���Ժ���ô�л�����������������ߵļ�Ǯ��
�����������Ӿ�����ƽ������ع������죬�����죬���������˻�˯��ɳ���ϣ�������Ѷ�¥�ķ���IJֿⷿ����ʰ���������߽�ȥ����ʼ���䵹��������������˺�һ���ӣ������һ��ֽ����淭��һ�������������ģ��ò�����������ʵʵ�������ܴ���Ҫ��˫�ֲ���ǿ�������Ҵ�����վ���������������ȴǰ��δ�е�������������
���������Ҵ�Ż���һ��������а��С���ӣ��ڴ���һ���ǹ��ܾã�����һ��Ե�������ʱ�ŷ��֣��Dz������Լ�ϲ����ζ����
�������������ų����IJ�����ߵ�������ںڷ����ӵ����ߣ���������һ��û˵�����ұ㿿��ȥ��������һ�������������ҵ�ͷ����
�����������ǣ���һ��ץס�������֣�����˵��������֪��֪����2���Ժ�2007���ʱ������һ����Ĺ�����˵�����һ�����յİ���������С������䡣��
��������������������Ĭ�������ҡ�
������������֪��֪�������Ѿ��ܾã�û������������ˡ����ҿ���������������Ҳ�������ɳ���϶���һ����˵��������ɡ���Ȼ�������ˣ���Ҳ�������ˣ�����ȥ��ɳĮ����Ȼ�������ﶪ�˼��䣬����֪��֪���Һ��������ҵ�ʱ���������ˣ�û������������������¡���үү��˵������ʧ����֪�Ǹ�����ʧȥ�����꣬������û�к�ڹ�����
��������������˻���û��˵�������Թ��Ե�������֪���������������ͭ�����棬��Ȼ��֪���������ô���£������Ҿ͵��ǻþ�һ��������æ�����뿪����Ȼ�Ҿ����������ӣ�����������ƣ��������ܲ�������ڸ����ˡ���
����������ǰ�������ɰ���һ����̱������ȴаа��Ц���ĵ�û�����Ĵ���һ�����ţ������Լ��ⷬ��������˧���ˣ���һ�п϶������dz�ƭ�֣���ڲСү�ң�������˭���㶼����������ΪСү�Ҹ���ǰһ������Щ��������ô����OUT�ˡ�
�����������ã�״��������������ڿ��ڣ�������һ�䣬����ô���ֵģ���
������������4��12���������ϵģ�֮��ȷʵ��������ݣ�����18�����죬����ȥ�ˣ���֪ȥ�İ����ĵ���ʰ�����ˣ�3���ʱ���Ҽǵ�����û�����ء���
��������
����ʮ������졮��
����������ʮ����졮��
��������Ԓ���䣬���������Ц��һ�£�����ǰһ������ʮ�ֱ��ߵ�ʧȥ�����R��
����������֪�^�˶�ã����������V�V���с����ұ��_�ۣ��sɶҲ����Ҋ���һ��ˣ��������l��һ����Ͱ��ҽo��Ϲ�ˣ����͵���������������ˣ��ͱ���һ��ץס�����֡�
�����������e�ӡ���
����������һ ������Iӯ�������ɷ��f��������ס���ĸ첲����������fɶҲ����Ҋ�������N���N�ڣ���
�����������@�Y����й⣬ֻ��졮Ϭ֮�������������
���������������N�k����
��������������лش𣬵����^�N���Ҷ�߅��������а�� ���f����
�������������������ˣ�ȫ�������������ˡ���
��������Ȼ�Ꮘ��졮�^һ�ͣ���Ѹ�ײ����ڶ�֮�ݣ����ı���ײ�����ұ��ӣ��촽�N�����ҵ��촽�����X�ĵ����ҵ����X���ĵ����������۵ģ��۵������R����ҵĵ�һ�����s�ǣ��ۿ��@������������N�ҵ�����͵ģ����氡��
������������犣������қ���п����²��ˣ���Խ��Խ�Խ���Ҿ�Խ�Ժ���Խ�Ժ��Ҿ�Խ���R�
����������������R�
�����������������^̫��Σ��������֏�ӛ���ˣ���Ҫ�����fЩʲ�N���������������꣬ÿһ��Ĵ𰸶���һ�ӣ��Y���µ��R�^�ˣ��Ұl�F�Ҿ�Ȼֻ���R�
�����������ǐ���ƿ�����ҵ���ͣ����B�����Ěⶼ������һ�ڣ����f��Ԓ�f���������Ҿ����������R��������ҷ�ҧ����ҧ�������^�����촽����ҧ��Ѫ����߀���˿s�������Ǿ���������һ�ӣ���������Y��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