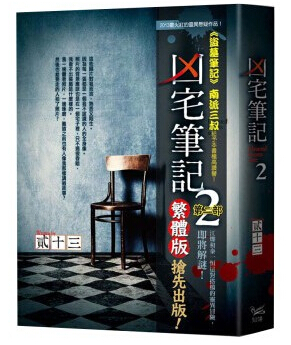狱中笔记-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见过车祸现场吗?”他说,“那么你会明白,横死的陌生人也足以让你发自肺腑地难受。”
“但也许不会让你痛哭?”
“你为民主德国死于饥荒的人哭过吗,他们可也是德国人。”
和一个比我年长一辈,又亲身陷入过世界的复杂性的人辩论是不明智的。但我还有另一个办法。我把一饼磁带放进录音机,一段小语种的新闻播报匀速播放出来。它的声调在句末总是滑行向上,句子很长而单词紧凑,每念一句都要深吸一口气。
“你觉得这是哪种语言?”
“难道不是德国的某个方言?”他皱起眉头仔细分辨着,“有一些单词是德语的,每句都有。”
“意第绪语。”我看着他惊愕的样子,击败父亲总是一件快乐的事,“你在利奥波德城听到的也是这种语言。你当时没留意?”
他沉默了下来,把磁带又听了一遍,然后承认道,“它确实非常像德语,而不是像别的语言。”
“据说一般德国人只要连续听三个月,就能听懂意第绪语。这段时间还不够学会法语呢。”
他陷入更长的沉默当中,而我简直得意忘形。
我不知道他后来有否重新思考犹太人和德意志人的族源关系,不过所有主流的语言学家都倾力否认意第绪语和德语是近亲,反而将之与斯拉夫语联系在一起。不料,一位前党卫队成员撕破了这件皇帝的新衣。
、心理医生
【原文】
被宣判死刑后的某一天,两位黑头发的心理医生造访了我。他们自称是纽伦堡特遣的,这个来头让我受宠若惊。
“您看起来消瘦,您有哪里不舒服吗?”他们之中较为温和的那个先开了口,用的是英语。
据闻纽伦堡的战犯享有与心理医生谈心的待遇,作为不得获取报刊杂志、不得与辩护律师充分沟通的补偿,以防止他们因为与世隔绝而丧失等待被处死的勇气。作为一个只能由美国单方面判刑的小人物,我的待遇是否越了级?
但心理医生是一种古怪的生物,他们说人话,却从不听人说话。我确实掉了一点肉,但还不至于向他们哭诉什么。
“我的不适并没有超过兰斯贝格的平均值。”
“您或许会发现,必要的宣泄对健康更有利。”另一个方脑袋的家伙开了腔,令我惊讶,他说一口奥地利音的德语。
我诚恐于刚才的对话是否足以让他们确诊“叛逆人格”或“自我封闭”之类的病症。但为了阻止这一点而努力辩解,又会获得“受迫幻想”和“自我意识过盛”的殊荣。我只好请他们随意坐下。也许真正患有臆病的是这两个想象力超群的生物,出于人道考虑,我不能主动刺激他们。
“您在法庭上承认了罪名,但也许那不是您要说的全部。”方脑袋用尽量平和的语气说道,同情是使人打开话匣的手法之一,“您对利奥波德城一案的处分最为不平,我猜得不错?”
激将是手法之二。
达豪审判赠我几项罪名,其中反人道罪得自1938年德奥合并时在维也纳猎杀犹太老幼。他们用当时的报纸作为杀人证据,报纸将英国间谍也笼统地报道为犹太人,达豪因而起诉我迫害犹太教会人员和民间组织。我的辩护律师仅仅给出“没有犯案动机”的无力辩驳。
我真的迫害犹太人了吗?
“贵国的主要报纸无一不刊载此事,您还有什么辩解?”
看来德国是个没有书报审查的自由国家。
然而海洋法系对证词的依赖超过了客观凭据,只是辩解同样无效,我还是被判了死刑。并非每个站在你对面的人都可以交谈,在冥顽的心灵面前,语言的障碍都退居其次。
我沉默的时间有点长,只好打破尴尬,“您猜得不错。您是来猜谜的?”
换成他摆出一副抱臂的自闭作派了。
在那个讲美式英语的医生打圆场时,我发现这场景颇类于刑警办案: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犯案人总会被其中一个激怒,继而错误地向另一个人寻求庇护,结果透露了罪行的细节。可我对罪名“没有丝毫的追悔”,也许他们是来考察我的油盐不进是否来自纳粹精神?
“坦言自己的身份是沟通的开端。”医生大都以法官自居,但情报人员尚未遗忘与人交往的基本礼仪,“我想您是德国人,尽管您努力把奥地利音说得更像美语,但是只从神态也能看出您的祖国。我来自法兰克福,名字您已经知道了。”
他的偏见带有德国式的固执。
而他开始变得更不乐意。
“您是来自德国的犹太人。”我补了一句。
“好吧,”他无疑受过尚算合格的高等教育,能模仿一点他以为然的上流礼仪,“我的确是犹太人,希望这不至使您蒙羞。”他深吸了一口气,“我的家族曾在奥地利生活,而我生于美利坚的纽约市。——古斯塔夫?吉尔伯特,我的同事,莱昂?戈登逊。”
“看,必要的宣泄对您的健康是有利的。”
“我也是纽约人。我和您是同龄人。我们是来帮助您的,如果您想倾吐一些什么的话。我们是中立的。”戈登逊体谅地用了简短的词句。
有时候憨厚的态度比精巧的语言更利于沟通,在这位友善的山姆面前,我不禁为两个同样说德语的人的隔阂感到悲凉。不过,伪装的善意倒是不如直白的恶意更具表达力,我能轻易捕捉吉尔伯特的想法——他是个有受迫幻想的犹太胜利者,想用纸上谈兵的心理学知识解释纳粹党人何以统治德国。但我难以猜出戈登逊的来意。
“我能否只与您交谈?两位医生同时在场会令我紧张。”我对吉尔伯特说。
他想了想,然后摇摇头,“我们司职不同。”
“您是这位先生的翻译?”我激将。
“我们都是心理医生。”
我陷入椅子的后部,决定沉默一阵子,直到他们妥协。
那天的谈话因为我“防御心理太强”而无法进行,他们提供了卫生院水准的体征测量之后就走了。在监狱里呆久了,即使是失去两位来历不明的对话者也会有些落寞,幸而我没有表现出来。
一个月后再次到访的只有吉尔伯特。
“作为纽伦堡审判的御用医师,您在这里是否屈才?”和他谈话是不会和睦的,但针锋相对倒也能让话题进行下去。
“配给达豪的医生不够,我来这里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他生硬地说。
他的确是德国人,奥地利籍贯和犹太血统也帮不了他。
“不对,您来这里是受戈登逊所托。您本人只对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感兴趣。您更憎恨大人物,这不失为一种勇敢。”
他略带吃惊地看着我。
“情报侦讯手段是否比心理访谈技巧要高明?”我看着这个比我大几岁的人。阅历和智力都将成为力量,书卷气则不能。他对纳粹的恨使他试图剖析纳粹要人的心理,但他本人的倾诉欲超过他的访谈对象。
我拿情报侦讯和心理访谈作比较时,他更不自在了。
这次我让他坐椅子,自己则坐在床上,“您或许不爱听,但戈登逊的职业素养比您高明,他更善于让受访者自己说话。不过塞翁失马,我更愿意与您交谈。——我们聊点什么?”
我们从利奥波德城枪击案谈起。我试图使他明白种族歧视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全部,失败了,他认为二战是德意志人民反犹太战争。试图使他明白宣传指导和新闻事实的矛盾关联?取得片面成功。
“您在暗示,这些思想毒瘤并非德国特有?”他警惕地说道,好像我冲犯了他的基本观点。
“我在明言,这些体制弊端——无关于思想,世界各国都存在。”我对自己鲜于实践的说服术毫无把握,那是我旧日的上司和前辈、瓦尔特?施伦堡的特长。
“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德意志人,您是怎样看待犹太人的?”
我有一位在纳粹时代仍然坚守社会民主党纲领的自由派的父亲,我本人则在今天也宣称是一名纳粹,我才不是什么普通的德意志人。但吉尔伯特坚持把我当成德国人的代表。
他认为大屠杀来自种族仇恨,而仇恨在方方面面都迫害着犹太人。我问他,坚信这种恨意是否让他更坚强。他迟疑地承认了。
“难怪您坚信我也心怀仇恨。”我感到好笑。
“难道您不是?”
愧不敢当。
“您对族人的恻隐是否超过了对其他人,尤其是对德意志人?”
“在面见这么多的罪行之后,我在心情上很难接受作恶者的善心。”
“我能否记录您的原话?”
他的脸色猝然起变,随即才发现眼前的囚徒无缘去出版些什么。
“您现在明白了,带着敌意的谈话无法正确地交换见解。”我欣赏着他在椅子上不自在地挪动的样子,“您从前遇到的政界要人大概不在乎这一点,他们乐于宣传,而您乐于冷眼旁观。您太习惯在这种彼此不沟通的情况下寻找异见和敌对的原因了。”
他沉默了片刻,笑着说情报侦讯真的比心理访谈要厉害。
使之厉害的是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履历长短,我这样说道。他用一副圆边眼镜强调自己犹太裔知识分子的身份,却匮乏于这个民族常见的狡黠,“怎么,您真的是一名情报人员?”
令我意外的是他承认了。
难怪我拿侦讯术和心理访谈术作比较时他会不自在。
他大概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求而加入这一行的。他来找我,不单是受那个更为学究气的戈登逊所托,还肩负美军派给他的任务。但是急于表达自我观点使他成为不了优秀的情报员,他的稚嫩也使他更像个出卖情报者。
“您的确更适合当一名左翼学者,用学识来资佐您先验的政治主张。而情报员是生存在没有立场的灰色地带的,唯此才能搜集更多的信息,这一点不巧是您的软肋。”
余下的时间里气氛变得低沉而萎靡,我们像东线战壕里煲烟的士兵一样颓然,零零碎碎地各诉衷肠。他自陈是在纽约出生,直到战争末期才跟随美军到了德国,除了语言之外,与这个国家没有任何联系。我回报以简单的履历说明。
总算像是一场对等的交谈。
“我最初以为懂德语会让我比同僚们更能胜任情报搜集工作,但是经过这一年半的实际行动,我不得不承认,我对这个国家所知甚少,而且时时感到无法融入其中。”
感伤的知识分子是很难对付的。我告诉他情报工作和性格、价值观直接相关,它不关心工作者的灵魂,但是否接受这项工作却涉及灵魂深处。
“也许您是对的。我的确应该尽早回到美国,继续我本来的学术。我在这里每一天都在思念故乡。”他继续说道,完全沉入自己的世界,“——挺奇怪的吧?一个犹太人对新大陆有思乡之情。”
比向往《塔木德》上的抽象故乡要容易理解得多。
他随即涌起更多的情绪。
“我的良心不安。我在采访他们……你们时,没有声明采访记录会成为研究资料。这是否也是一种不诚实。”
这是一种欺骗。
那些政界的公众人物必然不介意自己的言行被后人褒贬,但是在一对一的交谈时未申明来意,这仍然是欺骗。我看着他不发一言,直到他露出忏悔的神情。
“但您还是要写您的书。记住欺骗与品行无关,它只是懦夫的座右铭。”
这是今年8月间的事了。又过了一个月,吉尔伯特寄给我一封信。
加兰中校,
也许您已经通过别的途径知道,纽伦堡审判接近尾声,接下来我会回到美国,投入学术研究当中。
接受您的批评。我是在彼此并未沟通的情况下,以我个人的左翼立场去审视纳粹政要的。但如果仅从学术角度考察这个令几千万人卷入灾难的政体,未免有失责任。它不单涉及抽象概念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