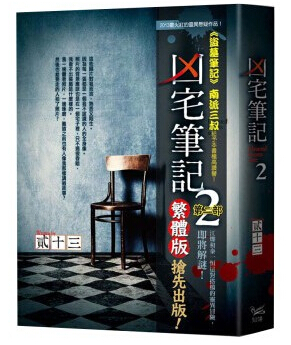狱中笔记-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从没见过这样简洁的布置,情报搜集科和情报分析科!”他和我一样擅长抽象思维,拙于四处打探消息。这种截然的工作划分很适合他,而他的本职又具有更核心的地位。
“确实十分简洁,虽然不是长久之计。”
“如果您愿意视之为自己的单位……”他那时如是说。
他继而滔滔不绝地谈起东西两线,意图招兵买马。“西方是可以谈判的君子,套取西方的情报再多,也不过是在邻里吵架时占上风。东方则是必须抵抗到底的猛兽,东线情报涉及你死我活的争斗。”
当时外军处的情报有一半来自我所供职的六处,但劝诱一个人走进激昂的历史,总是比劝诱他坐揽既得的实利更奏效。
我受史诗的蛊惑有多深?
“如果您愿意视之为自己的单位……”三年后他为美国打工,我成为死囚,韦塞尔再次说起这句话,没有像从前那样口若悬河。
他能说什么呢。盖伦何以取得美军信任,成为其在德国的耳目,他的斡旋与交易、手段和奇谋?肯定是一段独出心裁的传奇,但缔造传奇的无非桌下交易。
我们是发过誓的军人,今天我们对誓言缄默不语。
“我只能选择合理性,不是吗。”我这样回答,“我一直在猜,我在狱中的两年里并未被绞死,或许是仰仗……”
“施奈德博士,他现在的名字。”
我们默契地对视,不发一言。
后来韦塞尔间或到狱中找我,交换各自的筹码,刺探对方的把戏。这是个不动刀枪的时代,施耐德只有一群军队出身的老部下,他们是否会在出外勤时操正步,吓跑一条街的鼹鼠?
他需要政情处的案官和线报网。
他和施伦堡互不相帮,因而找到我。
“可是政情处的档案已经被销毁。”我对韦塞尔虚晃一枪,“他派一个少尉和我一起办的。您也许认识这位荷尔施泰因人。他后来怎样了?”
韦塞尔顿了顿,没有讲出少尉的名字,他在躲闪,“他死于柏林保卫战……兵荒马乱,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我在狱中,也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他没有去报告?”
“但博士不相信。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相信,您会把这份厚重的筹码扔进火堆?”
他和我都笑了起来。
我想告诉韦塞尔,人和胆小鬼分属在字母表的M和F,不太容易混淆。六处的档案记载了它的工作方式、重要人物、可供要挟的弱点。掌握它就能掌握德国乃至国外的政治情报工作。我烧了它,但他们相信我另有底本,我就凭空多得一份筹码。
“那么,用这些内情能交换什么?”
韦塞尔的眼睛直了。
盖伦希望与我交易,或是他的亲信韦塞尔想拉拢我。这两条路有着细微的差异,现在还不清楚。直到我走出监狱,成为他们的一员,了解其内情并成为同谋,才能知道今天的应许意味着什么。
可以确定的是,我用国家机密与美国合作。
有几成把握不当卖国贼?
这段时间我过得平稳。时间仿佛回到从前,情报工作新鲜刺激,挑战思维和耐力的极限。我在窄小的囚室里,接收更多的外界信息,思考一些不符合死囚身份的事。
迷索逻格斯给我寄信:古德里安成为美军顾问,盖伦主持了CIA派属不明的地下机构。斯科尔兹内从西班牙前往阿拉伯。
我试图在零丁的拼图碎片上窥见全图。它们暗示什么?国防军高层幸存的关键人物已是美国附庸。阿拉伯是一次大战时德国的势力范围,此后归英国统辖,又在45年后易手美国,再往东就是苏联的控制区。——德国分为东西两半,各为美苏的桥头堡。我再也坐不住,立刻找到那位CIA菜鸟,“请帮我把这管牙膏放进信箱。”
三天后,韦塞尔气急败坏地找到我,“害我找错了接头对象!”他把牙膏扔在桌上。
他曾经说过如果我要找他,就把一件能说明我是谁的东西交给菜鸟,让他放进死信箱。我猜他的重要人物里,使用美军监狱的牙膏而又用漱口杯把它轧扁后再折起来的人只有一个。
但他没有注意牙膏厂牌。
不知道他找错了谁,看来没少吃瘪。
“……很高兴您能全身而退。”我们瞪着对方,同时笑了起来。
这次乌龙说明了两点:一、韦塞尔和此类正规军人真的不擅长跑外勤(我也蹩脚于此道);二、韦塞尔与我的联系并未让盖伦知道全情。
“我想起来了,六处另有一批档案备份。”我坐在秘密谈话室里,语速缓慢,韦塞尔的眼睛像鼬鼠那样亮起来。
“你也许知道,它们涉及六处使用过的案官和线人,如何联系他们,采用何种诱饵或手段能与之合作。还有各国政界要人的丑闻、文化界人士的思想倾向。以及欧洲各城市的哪些咖啡厅、酒吧、下级旅馆可供接头——你也许不知道,六处还有许多尚未动用的鼹鼠,他们捱过了战后搜捕,现在仍在潜伏。”
我说这番话并无把握,但韦塞尔比我知道得更少。
“您开个价吧。”
我已厘清了道路。盖伦组织的格局已经改变,战争时代由军人主导的东线外军处变为和平时代的情报机构,分析科科长韦塞尔希望进入情报搜集的领域,与盖伦的其他几张王牌相抗:这些人对苏联以及东欧的军事情报了如指掌,但并未涉及德国境内或西方。韦塞尔想与我联手取得这片空地,成为盖伦手下的一号人物。
我看着这个荷尔施泰因人。他与我年纪相仿,有着相似的思维方式,逻辑上我胜一筹,交际是他的强项。曾经我们一起设计外军处二科的编制,互知底细,棋逢敌手,与这种人合作势在必然。
他现在的棋谱是借由我所掌握的六处档案,组建德国境内的情报网,而我的身价,是介入他此后将无暇顾及的情报分析工作。
这是盖伦组织的核心,我要成为盖伦拔不掉的一颗眼中钉。
我坐在秘密谈话室里,墙外的世界在思维里呈现出来。经历威廉时代和第三帝国,两次覆灭,德意志兰又回到三十年战争。为何一个死囚想到即将与己无关的事情,会死而不宁。
这让我走上逃亡之路。
三年前我带着必死的信念穿过美军的封锁线,成为战俘,现在为世变后的“合理性”愧对誓言。我变了节,再也不是那个旗帜下庄严宣誓的少年。
与任何主义无关,背弃内心本身是一种责罚。但后悔是推卸责任的表现,我别无遗憾。
1948年6月19日—6月21日
(下篇完)
、豚鼠
【原文】
午后的阳光斜射进来,我把瞳孔对准太阳的方向。这种消磨时光的方法让我想起埃尔文。大学时他总是把自己镶嵌在一堆抱枕里,说要在黄金般的午后享受字面义的“度日如年”。
我在大三那年认识了他。他是慕尼黑来的交换生,比我低一级。欢迎会后他抓着我抱头痛吻,用浓重的巴伐利亚口音打着响鼻,说重感冒在身不便行大礼。谢谢感冒病毒,让他简化了礼仪。
那年的交换生里有不少青年团员,组织让本地生一帮一的接待他们。由于他那极其特殊的打招呼方式,当支队长问我对谁最有印象时,我就脱口而出了这小子的全名。
他第二天就跑到我租的公寓里安了窝。
那天他提着“反应颠沛流离的波西米亚人的生活”的花布袋出现在我家门口,大喊“这里怎么干净得像停尸间”,我从不知道寄人篱下也可以这么趾高气扬。
他真的把这里当成自己家,试图用随处乱扔的衣服和鞋袜来对床和桌椅让它“变得更有人味儿”,虽然在我的威逼之下没有得逞。
但某天当我从实验室回来时,却看见屋顶的吊扇赫然变成了火红色。
“被这种颜色的风扇吹着,是多么的温暖啊!”
我真想拧开消防水栓把他冲出去。但我们居然这样住下去了,除了他间断性发作但终告流产的“创造”之外,也算安平无事。
他学艺术史,文科生的课程少,他进而把十点以前的课全画了删除号,取而代之的是通宵不知所踪。自然界的智慧永远超过那些高喊“为德意志的犁取得土地”的人类,在这个仅有一张卧榻的小房间里,只需调配生物的作息习性就能解决生存空间的问题。
说到艺术史,海德堡在个学科没有太出名的教授,那反而是慕尼黑的传统强项。对此这家伙笑出整排牙齿,“如果教授太牛,学生就无处开荒啦。”
“教授不就是教你的人么。”
“是谁教会莫奈画画?谁教会兰克书写历史?”
“没有第谷,就不会有开普勒和他的三大定律。”
“那就给我一个第谷!让他去搜集堆垛成山的资料,由我来当那个从资料中提炼出宇宙真理的开普勒。”
我想告诉他,没有玻尔就没有哥本哈根学派,但这个文科生不懂物理。他倒是说对了一点,那些认为学生非得在自己的牵引下才能够行走的人,其实也没有懂得取得智慧的正确方式。
他还用怪诞装束来证明自己和艺术的关系,并给出一个地理名词以蔽之,“波西米亚”。我不明白为何他要用法文来念这个词,这个地方位处苏台德东南,讲捷克语。
我的公寓是一座两层小楼的二楼,格局并不规整。我用尽办法使它看起来像一个立方体,埃尔文则致力于破坏这个立方体的空间结构。宇宙定律每时每刻都在这里横生,他制造熵,而我和一切终归徒劳的人类文明一样,试图把熵灭绝。
这让我想起玻尔的“互补性”。不单微观世界如此,宏观世界也是由彻底相反、但并非二分对偶的物质组成的,它们互斥又互补,却绝不构成一个整体。
“就像A小调和C大调,”他歪歪扭扭地哼着曲子,“两种基本的韵律,永远不可能同时演奏。”
“听不懂。”
“就像语言和……”我不太记得他使用的术语,他指的是语言无法到达的领域。因为一切能用语言表达的认知都是语言本身,而在这之外的东西是人们无法涉足的。
我表示仍然听不懂,他变得非常高兴,声称要是听懂了则我们之中必有一个是疯子,然后他又换了一个比喻。
“就像我和你。”
“这是循环论证。”
我用“互补性”来概括我们的关系,而他用音乐调式和语言学。我诚然是那个“语言无法到达的领域”,我们相处时多半是我在听,一知半解,哑口无言,虽然鲜少赞同。
但我用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态度,这些行动也时常遭到他的猛烈抨击。最激烈的一次是我决定加入警卫旗时。我们本来应该告别,但我看见的是他咆哮而后负气逃跑,他则看见我无法推翻他的论证,却固执己见。
后来我们各自发现,行动何尝不是一种语言,而信任自我正是信任彼此。
而在这之前更为漫长的时间里,我们一同享有年少气盛。
那些年少的日子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王座山的背面蒿草丛生,那里没有俯瞰巴符公国旧土的城堡,自弃于尘世之人却一再踏访。“而历史恰恰是在这些超脱之人的脚下延伸的。当格尼斯堡的七座桥梁没有因为欧拉和康德而不朽,海德堡的哲人路没有得名于黑格尔的智慧,慕尼黑仍然是王师兰克到来前的样子,历史就留在了旧章。”他肩上椴树的影子边界分明,晾着五月的阳光。
我们一同走过海德堡高低错落的巷道,像一双兄弟。并无相对性可言,不是像光与暗、正与反、阴与阳、过去与未来,而是像美与正义、科学与艺术、逻各斯与迷索斯。并驾齐驱的车辙把世界裂分为二,并无非此即彼的对立,不是不可或缺,而是必然。
“那些披荆斩棘的人在脱离于凡世之时也否定了它们。”
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