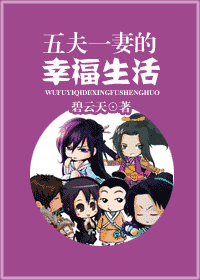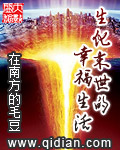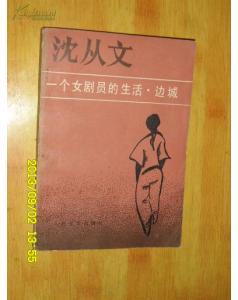生活的艺术 作者:林语堂-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今日的美国是机械文明的先导者,大家都以为世界在未来的机械控制下,一定倾向于美国那种生活形态。这种理论我却抱着怀疑,谁也不会知道未来的美国人又将是怎样的一种气质,勃鲁克(Van Wych Brook)在新著《新英格兰文化时代》一书中所描写的也许会重现于今日,我以为这是可能的。没有人敢说新英格兰文化的产物不是典型的美国文化,也没有人敢说惠特曼在他的民主主义的憧憬里所预测的理想——自由人类和完美母亲的产生——不是民主主义进步中的理想。假如美国能有短期的休息,我相信它或许会产生新的惠特曼,新的梭罗与新的罗威尔(Lewell)。到那时候,那种采金狂热所弄糟了的美国旧文化,也许会再开花结果。这样说来,美国将来的气质,不是又要跟今日的两样了吗?不是将接近于爱默生和梭罗的气质吗?我认为文化本来就是空闲的产物。所以文化的艺术就是悠闲的艺术。在中国人心目中,凡是用他的智慧来享受悠闲的人,也便是受教化最深的人。在哲学的观点上看来,劳碌和智慧似乎是根本相左的。智慧的人绝不劳碌,过于劳碌的人绝不是智慧的,善于优游岁月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在此我不想讲些中国人的悠闲过活技巧和分类,只是想说明那种养成他们喜闲散,优游岁月,乐天知命的性情——常常也就是诗人的性惰——的哲学背景。中国人那种对成就和成功的发生怀疑,和对这种生活本身如此深爱的脾性研究是怎样生出来的呢?
中国人的悠闲哲学,可以在十八世纪的一个不大出名的作家舒白香所说的话里看出来,他以为时间之所以宝贵,乃在时间之不被利用:“闲暇之时间如室中之空隙。”做女工的女人租不了小小的一个房间住着,房里满是东西,一无旋转的余地,因而感到不舒服;如果一旦她的薪水略为增加,她便要搬到一间较宽敞的房子里,在那里除了放置床桌和煤气炉子外,还有一些回旋的地方,这就是她感到舒适。同样理由,我们有了闲暇,才能感到生活的兴趣。我曾听说纽约公园街(Park Avenue)有一位富婆,她把住宅旁边的无用地皮都买了下来,原因是恐防有人在她的住宅旁造摩天大厦,她仅仅是为了要得一些弃置不用的空地,不惜花费大量金钱;但我以为她花的钱,再没有比花在这种地方更精明的了。
关于这点,我可以报告一些我个人的经验。原先我看不出纽约市中摩天大厦的美点,后来到了芝加哥,才觉得只要在摩天大厦的前边有相当的地面,而四周又有半里多的空地,倒可成为庄严美丽的。芝加哥在这方面比较幸运,空地较纽约曼哈顿市区多一些。如果那些大建筑物间的距离比较宽阔,则在远处看起来,就似乎没有什么东西阻碍了视线。这样比较起来,我们的生活太狭仄了,使我们对精神生活美点不能得到一个自由的视野。我们精神上的屋前空地太缺少了。
三、悠闲生活的崇尚
中国人之爱悠闲,有着很多交织着的原因。中国人的性情,是经过了文学的熏陶和哲学的认可的。这种爱悠闲的性情是由于酷爱人生而产生,并受了历代浪漫文学潜流的激荡,最后又由一种人生哲学——大体上可称它为道家哲学——承认它为合理近情的态度。中国人能囫囵地接受这种道家的人生观,可见他们的血液中原有着道家哲学的种子。
有一点我们须先行加以澄清,这种消闲的浪漫崇尚(我们已说过它是空闲的产物),绝不是我们一般想象中的那些有产阶级者的享受。那种观念是错误的。我们要明了,这种悠闲生活是穷愁潦倒的文士所崇尚的,他们中有的是生性喜爱悠闲的生活,有的是不得不如此,当我读中国的文学杰作时,或当我想到那些穷教师们拿了称颂悠闲生活的诗文去教穷弟子时,我不禁要想他们一定在这些著作中获得很大的满足和精神上的安慰。所谓“盛名多累,隐逸多适”,这种话对那些应试落第的人是很听得进的;还有什么“晚食可以当肉”这一类的俗语,在养不起家的人即可以解嘲。中国无产阶级的青年作家们指责苏东坡和陶渊明等为罪恶的有闲阶级的智识分子,这可说是文学批评史上的最大错误了。苏东坡的诗中不过写了一些“江上清风”及“山间明月”。陶渊明的诗中不过是说了一些“夕露沾我衣”及“鸡鸣桑树颠”。难道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和桑树颠的鸡鸣只有资产阶级者才能占有吗?这些古代的名人并不是空口白话地谈论着农村的情形,他们是躬亲过着穷苦的农夫生活,在农村生活中得到了和平与和谐的。
这样说来,这种消闲的浪漫崇尚,我以为根本是平民化的。我们只要想象英国大小说家斯顿(Laurence sterne)在他有感触的旅程上的情景,或是想象英国大诗人华兹华斯(Words Worth)和柯勒律治(Coleridge)他们徒步游欧洲,心胸中蕴着伟大的美的观念,而袋里不名一文。我们想象到这些,对于这些个浪漫主义就比较了解了。一个人不一定要有钱才可以旅行,就是在今日,旅行也不一定是富家的奢侈生活。总之,享受悠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要享受悠闲的生活只要有一种艺术家的性情,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正如梭罗在《瓦尔登湖》(Walden)里所说的,要享受悠闲的生活,所费是不多的。
笼统说来,中国的浪漫主义者都具有锐敏的感觉和爱好漂泊的天性,虽然在物质生活上露着穷苦的样子,但情感却很丰富。他们深切爱好人生,所以宁愿辞官弃禄,不愿心为形役,在中国,消闲生活并不是富有者、有权势者和成功者独有的权利(美国的成功者更显匆忙了!)而是那种高尚自负的心情的产物,这种高尚自负的心情极像那种西方的流浪者的尊严的观念,这种流浪者骄傲自负到又不肯去请教人家,自立到不愿意工作,聪明到不把周遭的世界看得太认真。这种样子的心情是一种超脱俗世的意识而产生,并和这种意识自然地联系着的;也可说是由那种看透人生的野心、愚蠢和名利的诱惑而产生出来的。那个把他的人格看得比事业的成就来得重大,把他的灵魂看得比名利更紧要的高尚自负的学者,大家都把他认为是中国文学上最崇高的理想。他显然是一个极简朴地去过生活,而且鄙视世欲功名的人。
这一类的大文学家——陶渊明、苏东坡、白居易、袁中郎、袁子才,都曾度过一个短期的官场生活,政绩都很优良,但都为了厌倦那种磕头的勾当,要求辞职,以便可以回家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另外的一位诗人白玉蟾,他把他的书斋题名“慵庵”,对悠闲的生活竭尽称赞的能事:
〖丹经慵读,道不在书;
藏教慵览,道之皮肤。
至道之要,贵乎清虚,
何谓清虚?终日如愚。
有诗慵吟,句外肠枯;
有琴慵弹,弦外韵孤;
有酒慵饮,醉外江湖;
有棋慵奕,意外干戈;
慵观溪山,内有画图;
慵对风月,内有蓬壶;
慵陪世事,内有田庐;
慵问寒暑,内有神都。
松枯石烂,我常如如。
谓之慵庵,不亦可乎?〗
从上面的题赞看来,这种悠闲的生活,也必须要有一个恬静的心地和乐天旷达的观念,以及一个能尽情玩赏大自然的胸怀方能享受。诗人及学者常常自题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别号,如江湖客(杜甫)、东坡居士(苏东坡)、烟湖散人、襟霞阁老人等等。
没有金钱也能享受悠闲的生活。有钱的人不一定能真真领略悠闲生活的乐趣,那些轻视钱财的人才真真懂得此中的乐趣。他须有丰富的心灵,有简朴生活的爱好,对于生财之道不大在心,这样的人,才有资格享受悠闲的生活。如果一个人真的要享受人生,人生是尽够他享受的。一般人不能领略这个尘世生活的乐趣,那是因为他们不深爱人生,把生活弄得平凡、刻板,而且无聊。有人说老子是嫉恶人生的,这话绝对不对,我认为老子所以要鄙弃俗世生活,正因为他太爱人生,不愿使生活变成“为生活而生活”。
有爱必有妒。一个热爱人生的人,对于他应享受的那些快乐的时光,一定爱惜非常。然而同时却又须保持流浪汉特有的那种尊严和傲慢。甚至他的垂钓时间也和他的办公时间一样神圣不可侵犯,而成为一种教规,好像英国人把游戏当做教规一样的郑重其事。他对于他在高尔夫球总会中同他人谈论股票的市况,一定会像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受到人家骚扰那样觉得厌恶。他一定时常计算着再有几个春天就要消逝了,为了不曾做几次遨游,而心中感到悲哀和懊丧,像一个市侩懊恼今天少卖出一些货物一样。
四、尘世是惟一的天堂
我们的生命总有一日会灭绝的,这种省悟,使那些深爱人生的人,在感觉上增添了悲哀的诗意情调。然而这种悲感却反使中国的学者更热切深刻地要去领略人生的乐趣。这看来是很奇怪的。我们的尘世人生因为只有一个,所以我们必须趁人生还未消逝的时候,尽情地把它享受。如果我们有了一种永生的渺茫希望,那么我们对于这尘世生活的乐趣便不能尽情地领略了。基士爵士(Sir Arthur Keith)曾说过一句和中国人的感想不谋而合的话:“如果人们的信念跟我的一样,认尘世是惟一的天堂,那么他们必将更竭尽全力把这个世界造成天堂。”苏东坡的诗中有“事如春梦了无痕”之句,因为如此,所以他那么深刻坚决地爱好人生。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人生不再”的感觉。中国的诗人和学者在欢娱宴乐的时候,常被这种“人生不再”“生命易逝”的悲哀感觉所烦扰,在花前月下,常有“花不常好,月不常圆”的伤悼。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园序》一篇赋里,有着两句名言:“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王羲之在和他的一些朋友欢宴的时候,曾写下《兰亭集序》这篇不朽的文章,它把“人生不再”的感觉表现得最为亲切: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我们都相信人总是要死的,相信生命像一支烛光,总有一日要熄灭的,我认为这种感觉是好的。它使我们清醒,使我们悲哀,它也使某些人感到一种诗意。此外还有一层最为重要:它使我们能够坚定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