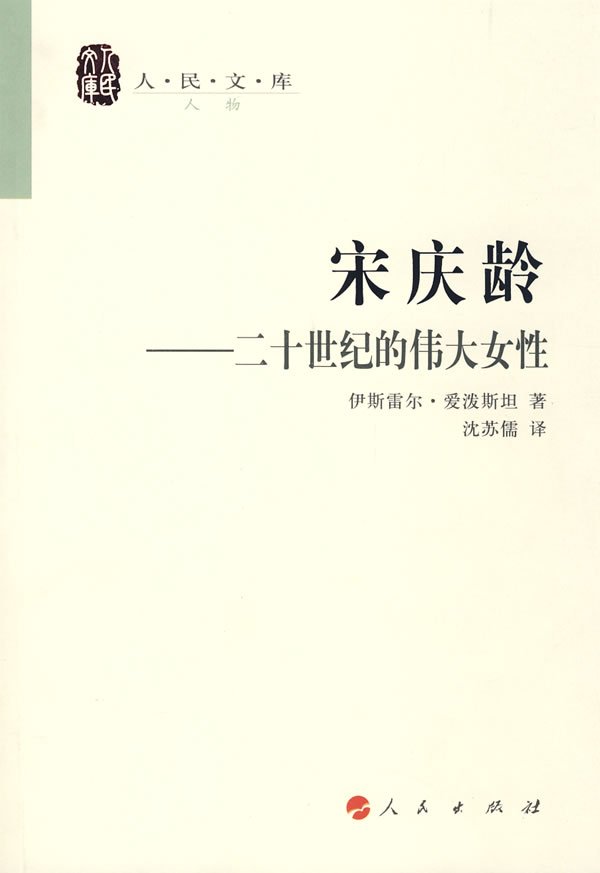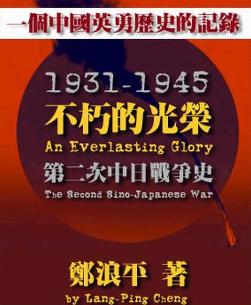黑铁时代--王小波-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假如可以和数盲们说理的话(其实和他们没法说理),我可以辩解道:星期四我只说了一句“开party”,此外什么都没干。这句话只是振动了一下空气而已——当然它和后来发生的事有一种极牵强的关系。数盲就顺着这种关系找到了我,让我挨鞭子。除此之外,蓝毛衣与保安打死小徐然后又偿命一事的关系也很可疑。假如保安该给小徐偿命,毙了他活该。假如不该偿命,把他放了也没什么不可以,这么胡搅蛮缠干什么。再说一遍,我知道说理是不许可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实在不讲理。刚进局子,警察就告诉我说,我的案子上面要直接抓,让我做最坏的准备。事实上没有那么坏。
我的案子数盲们很重视,所以警察一直劝我交待出个把别人来,但是我不肯。我倒不是皮肉痒痒想挨鞭子,而是身不由己——身为老大哥,如果让别人去挨鞭子,今后没法做人。这件事一连拖了半个多月,其间还被带到公安医院查了几次体。最后人家说,你年纪大了,心脏也不行,有生命危险——你可要本明白。我听了也有点犹豫,要知道我挺怕死。后来弄明白生存率有百分之七十(后来知道实际上是五十)就鼓起了勇气,签了认罪书,住进了公安医院。这里和活还蛮好的,睡单间,一流伙食,每天看病吃药。住医院有两个好处,一是先把我身上的病控制住,鞭刑后的生存率就能比50%高。二是假如让我信在家里,鞭刑前准会服止疼药,打吗啡针,这样鞭刑的意义就失掉了。
后来我知道,我是命里注定要挨鞭子的,公安局的同志问我那么多,是觉得两个人太少,想多拉几个。他们后来说,人多了热闹,也显得不疼。但我不这么想。他们又说,你这个案子上面动了真怒,多报几个人好,少了可能毙了你。这可让我够害怕的,但我挺住了。这样好,万一后来知道不招也能活就会后悔。宁可当场死,也不吃后悔药。
有关小徐,有必要补充几句。首先,他已经死了,我不说死人的坏话,所以本日记里一切他的坏话都取消。其次,虽然他死了,我还是不喜欢他;因为他什么都不肯干,和老左简直是一样,而且公开宣称他想得数盲症。最后,他已经死了,至死都没患数盲症,所以他是我的人;故此上面说的那句话也取消。而且这件事我也有责任,假如早发现他不见了,就可派出人去找他。发现他被保安逮走了,我可以率大队人马去救他——玻璃公司的哥们带来了铁棍,就是为这样的事预备的。荡平保安总部,冲到地下室把他救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肯定要出人命。假如我干了这样的事,等待我的就不是鞭刑——额头上要吃子弹了。
4
星期四我去参加那个party——现在我是从反面来说,坐的是技术部开最后一辆车。当时天已经黑了,但是我也能看出来,这车不是往东山上开——东山上有好多疗养院,现在也都空着,但西山是禁区。这里是中央的地方。自从海里满是柴油,人家就不来了,连警卫部队都撤走了,但别人还是不敢进去。最可怕的是它离市府小区极近,肯定会让数盲们发现。不过,我既然已经豁了出去,也就不问了。车进了西山的围墙,空气登时变得很好闻,因为这里有很多的树,甚至可以说,整个西山就是座大树林。现在树很少见,城里的树都被农民偷走了,所以有好多年没闻见这么好闻的松树味。出于一种朴素的敬畏之心,农民还没到这里来偷。连小偷都不敢来的地方,我们来了,这件事不怎么好。
等到车开到广场上,看到那里黑压压的人群,我脑子里又嗡的一声。整个北戴河,整个秦皇岛没得数盲症的人都在这里,甚至还有天津和北京来的人,开来了各种柴油车、烧焦炭的煤气车、电石车,以各种垃圾为燃料,这些是各单位的公务车,一个个千奇百怪;还有新式的日本车、德国车、美国车、瑞典车,烧高级燃料,还有用电池的无污染车,每年要到日本去充一次电,然后就可以开一年,都是首长专车。这两种车的区别在于前一种开起来地动山摇,后一种寂静无声;前一种跑得慢,后一种开得快;前一种车上没有玻璃,驾驶员暴露在外,跨在各种怪模怪样的机件上,一不小心就会摔出来,后一种很严密;前一种车上有各种管道、铸铁手柄、传动皮带等等,后一种同有这些东西,倒有录相机加彩电、小酒吧、电子游戏机、卫星天线、全球定位系统等等;前一种很难开,后一种是人就能开,除了数盲本人,但他也不是真不能开,只是觉得开车失了身份。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别的区别。前一种车是我的人开来的,后一种是傍肩们开来的。现在他们正在广场上换车开,三五十辆结成一个车队,浩浩荡荡开出去,到山道上赛车;剩下的人在广场上,有五六千人,有个骡马在集的气概。这么大的集会,假如我不是头儿就好了。但是我们这辆车开来时,所有的人都对我们鼓掌,并且有人在扩音器里说:老大哥王二来了,可以开始了。这就是说,这本烂账又记在我头上。我觉得有股要虚脱的感觉,但是挺住了,站在车头上,大声问道:吃的东西够吗?底下人就哄我:老大哥,闭嘴!俗气!车还没停稳,就有些女人叫我们车上的人:喂!陈犯!我在这里!刘犯,快滚过来!这是弟兄们的傍肩在打招呼,都是砸碱时傍上的。但是没有叫王犯的——我忘了通知她了。
在医院里我又见到了蓝毛衣,她和我一样穿上了白底蓝条的睡袍,跷着二郎腿,坐在走廊里的沙发上和小护士吹牛,说这一回她肯定上吉尼斯大全。假如先抽她,她就是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受鞭刑的人。假如先抽我,她就是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受鞭刑的女人。这孩子身材不高,有一点横宽,体质极佳,十之八九打不死。我们俩在医院里大吃大喝,鸡鸭鱼肉不在话下,还吃王八喝鹿血。原来定的是我八下,她六下。上级的指示有两条:1。一定要抽得狠,抽得疼,把歪风邪气打下去;2。一定不能把我们俩打死,以免国际上的人权组织起哄。说实在的,这两条指示自相矛盾,乱七八糟。可以想象有一条是首长的意图,还有一条是秘书加上去的。但是都要执行。所以就把我加到十二下,把她加到了八下,给我们俩吃王八,还请了些五迷三道的大气功师给我们发气。除了这些措施,别的医疗保障方案还很多,但是都怕负责任,让我们自己定夺。这些方案都是胡说八道——试举一例,让我练铁裆功健体,在睾丸上挂砖头——只有一条有道理,我们接纳了。那就是在受鞭刑前灌肠导尿。大庭广众下,被打出屎来可不好。
现在我知道这件事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国家花了宝贵的外汇从新加坡的历史博物馆买来了藤鞭,那种东西浸了药物,打一下疼得发疯,事后又不感染——只是对我来说,有没有“整后”大成问题;从外省调来了武警,以防那天出乱子;与此同时,海滨路正在搭台子。这些事和我没有关系,我应该在日记里多写点我的问题。
星期四晚上,有人运来了一台很大的音响设备,有他妈的逼好几十千瓦,对着话筒吹口气,山海关都能听到。先有人说,上星期是我们技术部老大哥生日!我们的老大哥王二,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乍听时几乎晕过去,一切不受惩罚的幻想都破灭了。到了这个地步,心里挺平静。在我看来,僭称万岁的事最严重,一有人提就死定了。但是居然就没人问。现在看来是有关心我的人把这事按下了。
有关万岁的事我要补充几句:我们部里有好几位浪漫诗人(我不能举出名字,以免他们也受鞭刑),但我认为,诗人的定义就是措辞不当的人。当然,数盲诗人不在此列。他们的问题不是措辞不当,而是诗写得太长而且永不分行。我个人的意见是措辞不当相对好一些。上星期有位数盲诗人在广播里朗诵诗篇,从早九点到晚八点,连题目都没念完,是否过分了一点?
那天晚上的餐桌上有各种好东西:香槟、茅台、鱼子酱,我们预备的东西全扔掉了。等到party散了以后,桌上还剩了大量的食品,全是特供。后来数盲让我招出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他们又让各特供点清点,仿佛我犯下了抢劫罪。我认为他们应当回家清点。但是局子里的人说,不能这样报上去,否则会说我偷到他们家里去了。
从正面来说,我已经体会到鱼子酱为什么是特供(危险品)了:这种东西太好吃,足以使人为之厮打起来。而在数盲那里就没有危险,他们好吃的东西多极了,犯不着为它打架。
后来大胖子要露一手美声唱法,不幸的是话筒有毛病,他嗓门又大,故而完全失都,满山满海都是驴鸣;别人就把他撵下台去。上来一个乐队,玩的又是重金属,好在我及时用棉花把耳朵塞住了。后来有人建议让砸过碱的大哥大姐们跳迪斯科,我就没有听见,糊里糊涂地被人放倒上了镣铐,这回可是铸铁的真家伙。爬起来以后看见大家跳,我也跳。别人是一对一对的,我是一个人瞎扭,自得其乐。忽然有人在我背上点了一指,回头一看,是我前妻。穿着套装,很合体,脸上浅笑着,妩媚之极。我赶紧把棉花掏出来,这会儿不是乐队吵,而是铁链子哗哗地吵。因为所有跳舞的男人都戴镣。我说:报告管教,忘了通知你。她说:没有关系。我说:又要劳动你送我去砸碱了。她说:大概吧。你是有意的吗?我想了本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事是有意,也没有什么事是无意。她凑过来,贴住我的脸说:你很诚实。这时候有人宣布说,各房间都有热水,可以洗澡,也可以喝。这就是说,早有人把深井启动了。深层地下水是特供的,它的危险性在于可以洗澡,洗澡很舒服,洗了还想洗,就会把水用光;我们用当然犯法,这是因为假如我们抽走了深层地下水,表层带有盐碱的水就会渗下去——数盲抽才没有问题,虽然他们抽了地下水,表层水也会渗下去。这件事我负完全责任——听到这条通知,她就带我去出操。进了房间才发现镣铐都打不开——后来是用手锯打开的——所以只好戴着干。那天晚上她没有发口令,我自己就行——事后她说:这样的情形是第一次吧。我说:是。她又说:这说明,你爱我?我说:大概吧。她一听,眼睛里全是泪,因为这回答不能让她满意。她又问道:那你可爱过别人?我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她就说:那我死了也不亏。后来又干了两三次,都是我主动。然后我们开着她的车回我的小屋,喝了很多酒,又干了很多回。后来就睡了,再以后我醒来,我前妻已经走了,到现在还没见着。
假如我在受鞭刑的时候死掉的话(这一段是我受刑前写的,现在知道我并没有死),希望领导上能把这个日记本交给我前妻。这个笔记本里有好几处说到我爱她,希望她看了能够满意。我一直不肯告诉她,是因为她是我的管教,我是她的“王犯”,这种关系比爱不爱的神圣得多。而那天晚上我告诉她,我大概爱她,情形和现在差不多,我觉得自己快完蛋了。当时我们那间屋里点着床头灯,挂着窗帘,但还是一会红、一会绿。这是因为有些混蛋带来了船上用的救生火箭,正在不停地燃放,而且火箭朝小区飞去。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