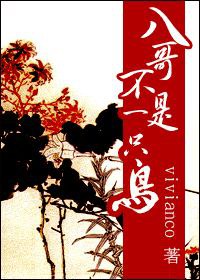藏獒不是狗-第5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电脑上查到了蓝岛所有挂牌营业的律师事务所,一个个打电话过去。当我把第十五个电话打给蛮睐律师事务所时,那边传来了我需要的声音:“袁最有啊,但已经辞职了。”
我又说:“我是他一个朋友,这会儿在西海,能告诉我他家的电话吗?”
他家的电话没人接。我寻思,家里人大概上班去了。我再次坐出租车返回黄海獒场,刚在公路边下车,就见袁最从土路上走来,赶紧又钻回出租车,告诉司机:“我有点头晕,想在车里坐会儿,你计时吧。”
袁最显然没什么急事,耐心地在公路边的车站等来了公共汽车。我让出租车跟着公共汽车,一个小时后来到了一座秀丽的山包前,看到山底石阶前赫然耸立着一个牌子:基督山#基督教堂。
袁最沿着石阶走上山去。山上唯一的建筑是有尖顶!带钟楼的基督教堂。我寻思他这种人也会去教堂?
又一想,教堂也许正是他这种人才会去的地方。
上大学时,我跟路多多探讨过宗教。我认为有罪孽才有宗教,他认为有宗教才有罪孽。两个人曾为此吵得面红耳赤。我说所有宗教的起源都是为了让灵魂得救,因为灵魂从一开始就是罪恶的痛苦的绝望的。神是灵魂的彼岸,我们对神的所有宣誓都是凭着自己的灵魂能不能永远得救的起誓。宗教的意义就在于,它用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把起誓变成了仪式,把解脱变成了宣示经典的过程,把神和彼岸变成了可以理解的语言。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罪孽一旦拥有,就必然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力量挣扎出全部的魅力,宗教就是被罪孽的魅力吸引过来的神的载体。
路多多对我的反驳非常有力,他说人本来既没有道德感也没有罪孽感,是宗教把痛苦和罪孽强加给了人。人一遇到宗教,才发现照透自己的镜子出现了,神让我们感到污秽不堪!罪恶累累。没有神,人类就没有比较,而宗教是比较后的神殿,是让人感知罪孽!拥有罪孽又容纳罪孽的蓝色天湖。宗教并不滋生罪孽,却可以描绘罪孽和夸大罪孽。当罪孽在神性光辉的照耀下被迫消失时,宗教会让你留下永恒的阴影,表明即便你烂漫如花,也是阳光下的黑暗。
不管是我认为的有罪孽才有宗教,还是路多多认为的有宗教才有罪孽,都能说明袁最此刻的行动:一个罪人走向了最容易释放罪恶的地方。这几乎是一种本能的选择。他出于习惯,来到了罪人之路上早已等候着他的骚站。
而我却来到基督山对面的一家菜馆里,坐在窗前,要了一盘辣炒蛤捌!一瓶啤酒,边享受蓝岛特有的口福,边等候袁最从石阶上下来。我不能上去,石阶只有一条,万一碰上就前功尽弃了。就在这时,一个年轻女人走进了菜馆,四下里一瞧,直接过来,坐在了我对面。菜馆的桌子很小,面对着她我都有点担心辣炒蛤咧的汁液会溅到她身上。她的气味也清晰可闻地飘悠在我眼前,有点淡淡的藏香的味道。我看看别的地方,到处都是空座位,她干吗要跟我坐在一起?
我审视着她,不客气地问道:“我认识你吗?”
年轻女人微笑着,把满脸的歉疚用女人特有的温婉妥帖地送给了我,语气柔柔地说:“可我是认识你的。”
一瞬间我便把傲慢置换成了谦卑。我凝视着她,敏锐地捕捉到了她的白哲!清秀以及牙齿的香洁,也许还有隐藏在美貌后面的疲倦和焦虑。我说:“认识我?我有点想不起来了。对不起,我一见女人就有点晕。我是个高原人,第一次来蓝岛,没见过大世面。你有什么事情赶快说,别让我提心吊胆的。我不习惯陌生人的热情,总觉得哪儿不对劲。”
女人望了望窗外说:“你在跟踪一个人,为什么?”
我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
女人小声说:“恰好我也在跟踪这个人。在你第一天躲在黄海獒场外面的树后探头探脑时,我就注意到你了。”
我几乎蹦起来:“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跟踪袁最?”
“你不知道我,我可知道你,你是作家。我家里有你的书,书前面有你的照片。”女人诡话而亲切地一笑。但我能感觉到她笑得相当勉强,似乎她努力想给我一个愉快美好的印象,但努力的背后却是苦涩和悲愁。
我站起来说:“如果你是私人侦探或者警察,那我就走人了,我不喜欢跟这种人打交道。”
她仰头望着我,眼睛里的恳求让我心软:能坐下吗?
我坐了下来:“你为什么不上基督山?怕他认出你来?看来你们是熟人。你知道他去教堂干什么?祈祷?忏悔?忏悔什么?难道他犯了罪?”
我的试探让她哆嗦了一下。她恳切地说:“色钦作家,我看过你的书,我相信你是个好人。你千里迢迢来蓝岛,天天监视袁最,肯定不是小事。袁最到底怎么了,能告诉我吗?”
我狡猾地笑笑:“当然可以,但至少我应该知道你的身份吧?”
她把眼睛闭上又睁开,神情黯然地说:“我是他妻子。”
我下意识地伸手抓起啤酒瓶,有点慌乱地说:
“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上午我给你家打过电话,我也是要找你的。”
“找我?你找我肯定有事。”她凄然一笑,突然喊起来,“小姐,小姐,再上一斤基围虾,一只大螃蟹,一盘海螺肉。我请客。你在蓝岛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但是你得告诉我袁最到底怎么了?对了,再来两瓶啤酒。我们蓝岛的男人,喝起啤酒来没个够。
小姐,虾!螃蟹!海螺快点上,别把死的搞上来,我是蓝岛人你们骗不了我。对了色钦作家,还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我叫姒苏。”
看来这个叫姒苏的女人打算豁出去了。就在酒菜纷纷上来的过程中,她把袁最如何为王故打官司,如何成为十一只大藏獒的主人,如何面对藏獒被偷,如何读了我的书去了青果阿妈草原,如何带着嘎朵觉悟和八只小藏獒回来,一股脑全告诉了我。说到最后,她拿出了袁最留给她的信和她始终没有签字的“离婚协议书”给我看。这封信里,袁最说他已经不是姆苏的丈夫,也不是飞飞的爸爸。因为他现在做的事已经不允许他有一个家!有妻子和女儿。虽然袁最声明他从来没爱过她们,他爱的只是藏獒,但字里行间透出的却是他难以割舍!发自肺腑的爱。是什么事情紧迫到会让一个挚爱妻女的男人,如此果决地放弃她们呢?不难想象是罪恶。一个深感自己有罪的人,如果他还爱着自己的家人,唯一要做的就是不连累她们,不让她们有一个罪行累累的丈夫和爸爸而一辈子低人一等。
“袁最虽然没告诉我他要去哪里,但我知道他带着嘎朵觉悟和八只小藏獒,就一定回到黄海美场去了。色钦作家,你说我们怎么办?我不是一个见异思迁的女人,就算天下所有的男人都比袁最好,我也只爱袁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他都是飞飞的爸爸!
我的丈夫。我不能跟他离婚,决不。不管他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是他最亲最亲的人。”她捂着眼睛硬咽起来,眼泪从指缝里渗出,落下来就成了砸在我心里的石头。
我心思沉沉地扭头不看她,突然发现袁最已经从基督山的石阶上下来,正朝着这边穿越着马路。我吓了一跳,他不会是也要来这家菜馆吃饭吧?如果他看到我跟他妻子一起监视他,会是什么举动?我站起来想拉着女人躲开,却见袁最脚步一弯拐到车站那边去了,显然他是要坐公共汽车回獒场的。我盯着袁最,直到他坐车离去。姒苏一直在低头硬咽。我又坐下,望着她不知怎么办好。她突然抬起湿热的泪眼想说什么。我赶紧说:“我们该走了,也许听忏悔的牧师会告诉我们,袁最到底做了些什么事?”又告诉她,“袁最已经离开了。”
姒苏赶紧站起来,生怕我抢了先,大步走向吧台去结账。我是一个向来不喜欢女人为我结账的男人,但这次我没有喝止她。她请客的用意是想让我告诉她我所知道的袁最,我不想让这样一个可怜的女人以为我在拒绝而失去希望。她为我点的菜,我一口也没吃。我们离开时,服务小姐问:“打包吗?”我看了一眼不知该怎么办的姒苏,赶紧说:“所有的菜,还有酒,都给我打上,我带回去晚上吃。”
4
今天不是礼拜日,也不是旅游旺季,教堂大厅里没有别人。当我们坐在第一排的长条椅上,面对着西装革履!清瘦矍拣的牧师时,我仿佛觉得这个天堂的守门人是从大街上招领的,而不是上帝派遣的。为什么不穿上黑色的道袍,为什么不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我立刻有了一种误人歧途的感觉:我虽然不是佛教徒,但仍然以我的出生地为自豪,那是佛灯照耀的藏区。我对红衣喇嘛!黄裳活佛的敬畏是与生俱来的。相比之下,我到了这里怎么一点敬畏心和神秘感都没有?我想佛教一定比基督教更接近神的灵界以及天堂!地狱!来世!灵魂什么的,首先他们的喇嘛是一些观照神灵修行念经的人,是即便脱得精光也会让人觉得并非凡胎俗骨的神职人员。不像面前这个牧师的形象。
还好,牧师虽然是个老人,说话的声音却比年轻人还要洪亮,神态平静样和,给人一种空廓无染的感觉。见面后没说几句,他就说:“对专门来找我的人,我首先要告诉他们我的名字,我叫欧阳约翰。这个名字意味着既然我是上帝虔诚的仆人,就应该是你们忠实的朋友。说吧,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说多久就说多久。如果觉得这里太空旷,我们也可以去后面的忏悔室。”
我说:“在哪儿都行。不过我们不是来找你忏悔的,我们是来打听个事,刚才离开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叫袁最的,他来干什么?”
“袁最?他叫袁最?我不知道。”约翰牧师若有所思地说。
“他一定是来忏悔的吧?告诉我们他忏悔了什么?”
约翰牧师吃惊地望着我们:怎么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而且口气是如此得理所当然。“忏悔者的声音只有上帝才能听取。”
“这个我们当然知道。但是,假如一个罪犯,面对你说出了他的罪行,而你却守口如瓶,知情不报,那会有什么结果呢?他会避开惩罚继续犯罪,灵魂和肉体将在越来越黑暗的堕落中得不到拯救。我的意思是说,你在对上帝的事业负责的同时,也必须为法律负责。该说的不说,替罪犯保密,那就是包庇纵容,他的罪就变成了你的罪,你和你的上帝怎么可以为人间担待那么多的罪恶呢?当然你会说,我不做出卖人的犹大,罪恶里头没有比犹大更大的罪,所以他只能在橄榄园里上吊自杀。但是我要说,自从有了耶稣基督,人类社会遍地都是犹大。犹大也可以是英雄好汉,是识时务之俊杰。”我的态度是如此的不恭不敬,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好像我是来挑战的,代表无神论挑战有神论:要说惩罚,上帝能耐,还是法律能耐?要说犯罪,在法律面前,上帝也会犯罪。
“当然,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很多事情是不辨自明的。”约翰牧师不怒不激,平和地点着头,让我感觉到他一下子就被我说服了,会立刻把袁最的忏悔说出来。他从朴素而神圣的讲坛上走过来,坐到长条椅的一边,和我们保持着距离,慢悠悠地说:“上帝听取忏悔时,我可以在场,也可以不在场。如果我意识到我将要听到的忏悔是不可以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