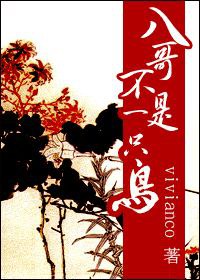藏獒不是狗-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明白了,一个犯罪嫌疑人是不能在拥有犯罪现场的光天化日里走来走去。虽然作为受害人的销售基地此前基本放弃了追究,但如果我把逍遥法外当作炫耀,大摇大摆地刺激人家,那就很难保证人家会继续放任不管了。还是小合一点吧,为了我的自由和我打算继续活着的信心。
我躲在车里,在麦玛镇转悠了半天,看到我不在的这几年里,到处都莫名其妙地盖起了楼房,就连我的母校麦玛一中和州立高中也都是三层五层的水泥教学楼了。突然想到拉姆玉珍,便让司机开向了贝囊家。贝囊家已经不存在了,那儿是一大片建筑工地,从工地前的彩绘广告牌上可以看出,正在建设的是一座广场和展览馆什么的。我问司机:“这里原来的居民呢?”司机说:“都拿着搬迁费走人啦,去哪儿说不上,反正离麦玛镇都不会很远。”我在沮丧中离开了那里,路过喜马拉雅藏獒销售基地时,让司机停下,从车窗里望了半天:红砖的围墙已经消失,代之以既不防贼也不防窥的矛头铁栅子,好看了许多。被我烧过的平房遗址上,盗立着一座四层的红色楼房。
楼房一侧是几排封闭的铁栅门的犬舍,几声硬邦邦的藏獒的叫声从那里传来。司机告诉我,销售基地这几年发了,他们的藏獒每天都有进有出,大部分是从边远草场低价搜罗来的,也有他们自己养育的。我说:“听声音这里的藏獒也不怎么样嘛。”司机说:“他们的好藏獒都在麦玛镇北边的台地草甸上,外地人旅游参观都去那边。”我知道那就是归并给销售基地的原珠穆朗玛藏獒保护基地了,便让司机开了过去。
我没有下车,看不见藏羹,但能隔着铁栅子听听藏獒此起彼伏的吼叫,也算是一种幸运了。我分辨着公獒和母獒!小美和成年獒的叫声,想在众多的叫声里捕捉到那个熟悉的轰鸣,那个因为老远就能闻出我的味道而激情澎湃!缠绵徘恻的轰鸣。然而我听了半天也没听出来,我确信我的斯巴真的已经不在这里了。
我说:“这里的藏獒真不错,它们的吼声能把人的心震烂。”
司机说:“其实青果阿妈草原最好的藏獒并没有搜罗到销售基地,有的獒主坚决不卖自家的藏羹,你出的价钱越高他越舍不得。”
“最好的藏獒在哪里?叫什么?”我希望司机说出“斯巴”这个名字来。
司机说:“嘎朵觉悟!各姿各雅,都是最好的。可惜我也没见过,不知道是谁家的。”
转完了麦玛镇,我再次被鹫娃接去吃饭,又是喝酒又是醉,又是第二天上午才醒来。这次是被鹫娃的司机叫醒的。司机带我来到车上。鹫娃已经在车里了。我以为他是来陪我的,便说:“你知道不知道拉姆玉珍在哪里?知道的话带我去看看。”鹫娃说:“别去啦。拉姆玉珍嫁给了一个牧人,你去了不是添乱吗?”
然后告诉我,他要去省会西海府开会,顺便把我带回去。我说我还不打算离开,还想待几天。鹫娃说:“不行,你待在这里我不放心,万一出了事我没办法给你父母亲交代。”
我知道我的安危关联着鹫娃副州长的安危,他是不会给我自由的。我跟着鹫娃离开了麦玛镇,一再叹息:“可惜死啦,我没有见到我的斯巴。拜托啦莺娃,你还是要继续打听,斯巴到底卖到了哪里。”
鹫娃笑道:“你放心,我对斯巴的感情一点不比你少。”
我又回到了西海府。在这个我不喜欢的城市里,我没有藏獒,没有女人,没有我所钟情的生活,只有寂寞和写作陪伴着我。我写出了关于藏獒的小说,把没有藏獒的日子变成了有藏獒的日子。其间我学会了开车,买了一辆二手货的北京吉普,污染着原本就浊气冲天的环境。好几次我都冲动地准备开到青果阿妈草原去,一想到鹫娃我又放弃了。我跟鹫娃又见过几面,都是在西海府,在他来开会时下榻的宾馆里。我把鹫娃介绍给了已经是省政府应急委员会副主任的路多多。他们两个似乎一见如故,很快就背着我交往起来。我理解他们,他们都是官场中人,属于那种没有利害冲突又可以互相利用的关系。不久,中国出现了藏獒热,都说是我的小说引发了这股前所未有的豢养并买卖宠物藏獒的潮流。但我有时并不这么认为,我的书可能会让许多人喜欢藏獒,却无法提供让他们如此喜欢的更深层的理由——那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精神的不期而至的需求。鹫娃适时制定了“把藏獒经济当作青果阿妈州龙头经济”的方针,还提出了“以獒富州”的口号。不知这突然爆发的藏獒经济到底起没起到让该州富裕起来的作用,反正过了不久,鹫娃就由青果阿妈州的副州长变成州长了。又是藏獒,我说过,鹫娃的每一次升迁都跟藏獒有关。这就是宿命吧,是鹫娃跟藏獒的因缘吧。
又是一次“藏獒兴,鹫娃升”。而我却恶毒地想:说不定下来就是“藏獒衰,鸯娃败”呢。
第七章 袁最
1
袁最在机场雇了一辆小型的厢式货车,把嘎朵觉悟和八只小藏獒运到家后,就开始忙前忙后地安顿它们。他家在蓝岛后海的一片居民区里,一楼,靠着后面的阳台,是一块用冬青树围起来的草坪。这块草坪现在就成了嘎朵觉悟和八只小藏獒的领地。袁最把嘎朵觉悟的铁链子拴在一棵石榴树上,发现地上太潮,便从家里拿出一块地毯铺在了草坪上。从下飞机到现在差不多两个小时了,小藏獒们已经从眩晕中恢复过来,虽然团团卧在一起,精神却是饱满的,抬头好奇而忐忑地望着四周。嘎朵觉悟只比刚下飞机时好了一点点,无精打采地卧在地毯上,滴流着满嘴的口涎,眼睛一会儿睁一会儿闭,似乎想睡又不敢睡。袁最放了一盆水在草坪上,坐在嘎朵觉悟身边,把手插进它浓密的截毛,不停地抓挠着:“这就是家了,我的家,也是你们的家。”
他想自己离家已经快两个月了。两个月中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他无从知晓,唯一的知晓便是地展。现在连地震他也要忘记了,忘记青果阿妈草原以及麦玛镇,忘记一个叫袁最的人在地震发生后前赴后继所做的一切。他没有去过地震现场,甚至都没有去过西海府。这两个月中他在河北省的某个地方给朋友帮忙,当然朋友是办獒场的。某一天,他在大街上闲逛,无意中买了几张彩票,竟然中了。他用中獒的一百万,不,两百万,不,三百万,从朋友的獒场优惠买到了这只大藏獒和八只小藏獒。现在他回来了,回到了妻子和女儿身边,仍然和过去一样,是妻子的好丈夫,是女儿的好爸爸,而且会更好,越来越好。他已经脱胎换骨,成了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他不知道什么叫无耻!自私!残忍!贪婪,关于罪恶的一切都将成为生活的空白而跟他毫无关系。他是多么的幸运和幸福啊,心满意足地守护在自己的藏獒身边,等待着妻子下班归来!女儿放学回家。
袁最当然不是第一次拥有藏獒。两年前他从律师事务所辞职,前往黄海獒场上班时,凭借的就是十一只藏獒差不多半个獒场的股份。十一只藏獒是当事人送给他的,这天外来福改变了他的人生,让他从此成了一个爱藏獒胜过爱一切(也许要除掉妻子和女儿吧)的人。
当事人叫王故,台湾人,来蓝岛和朋友合伙办獒场,结果就有了那起令王故心惊胆寒的獒场强奸案。
心惊胆寒的原因是作为合伙人的朋友李简尘状告王故用匪夷所思的手段强奸了他的未婚妻獒场驯狗师花馨子,致使花馨子因惊吓过度而大病住院。王故没有请律师,因为他觉得根本用不着。他在法庭的自我辩护是:不是强奸是两厢情愿,充其量不过是一夜情,不,是半夜情,而且是没有搞成的半夜情。花馨子说她突然不舒服了,就没有搞成。要是这也算犯罪,中国人从官员到百姓是不是有一半都得受审了?你们为什么不去问问花馨子呢?他的辩护刚刚结束,失踪半个月的花馨子就出现在法庭上,指着王故大骂他是没有人性的畜生,并详细讲述了被强奸的经过:王故借口制定驯狗计划把花馨子带进了他的宿舍。
她没想到宿舍里有三只王故刚从河曲草原收购来的大藏獒。当三只大藏獒扑向她而她本能地贴近王故寻求保护时,王故抱住了她。之后他威胁道:“要么让藏獒咬死你,要么你在我怀里老老实实待着。”他把她压倒在地上,扒光了她,也扒光了自己。她本来是可以反抗的,但三只大藏羹一只咬住了她的脚,一只用有力的前爪踩住了她的胳膊,一只在头顶吼叫,口水都流进她眼睛里了,她被吓得昏死过去。她当庭亮出了被藏羹咬伤的脚和被爪子抓破的胳膊以及医院确认被动物咬伤!抓伤的证明,悲痛地号哭起来。信奉基督的王故傻了,极度惊讶之中只说了一句软弱无力的话:“上帝啊,她她她,她是个骗子。”主审法官很快做出了宣判:事实确凿,情节严重,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案件还在审理。王故上诉之后,袁最出现在法庭上。他说他是主动要求为王故辩护的,因为他了解藏獒,藏獒有可能帮助人做坏事,但不可能为虎作怅到这种程度。在一个男人强行压倒一个女人时,藏羹本能的反应一定是撕咬男人,解救女人,而不是相反。
何况在花馨子的陈述里,对她形成威胁的三只大藏獒是王故刚从河曲草原收购来的,它们跟王故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应该不超过一个星期,并没有形成主仆关系,就更不可能做他的帮凶了。既然藏獒助人强奸不可信,强奸本身也就更不可信了。王故长得又瘦又小,根本不是大个子姑娘花馨子的对手。袁最说,为了证明他的辩护所言不虚,他愿意当着那三只大藏獒的面,在同样的环境里,做一次模拟实验,看藏獒到底会助男成奸,还是会保护女人。为了使模拟更加逼真,他希望配合他完成实验的是花馨子本人而不是随便找个替身。袁最说:“我一定要还藏獒一个清白,还被冤枉的王故一个清白。”这样的辩护有点离奇,但谁又能说它背离了一个律师的辩护原则呢?尤其是模拟实验,它勾起了法庭上许多人的好奇和喜欢恶作剧的心理,让人充满了邪恶的期待。主审法官跟其他法官协商之后,做了这样的答复:本法庭没有义务主持这样一种模拟实验,但如果辩护律师愿意冒险,并能说服原告同意,我们可以把它当作辩护证据给予足够的重视。现在就看原告李简尘和受害人花馨子的态度了。他们在沉默了一个星期后,通过法庭转告袁最,他们同意模拟实验,随时可以进行。
模拟实验的这天,袁最请来了公证员,架起了摄像机,穿上了家中最厚的衣服,戴上了皮帽子,还去医疗器械商店买了一个用于治疗颈椎病的坚固的钢质颈箍,免得野性的藏獒一口咬断自己的喉咙。他是一副稳操胜券的样子,但结果却使他大失所望,恨不得一头撞死。在王故的宿舍,当他压倒花馨子之后,三只大藏獒就像训练有素的黑帮成员,一只咬住了花馨子的脚,一只用前爪踩住了她的手,一只在前面用爪子蹂蹭着她的头发仰头吼叫。她吓得再次昏死过去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又是一次助男成奸。这样的结果显然说明花馨子没有撒谎,即使一个男人根本不认识这三只大藏獒,无从谈起主仆关系,它们也有可能成为他恃强凌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