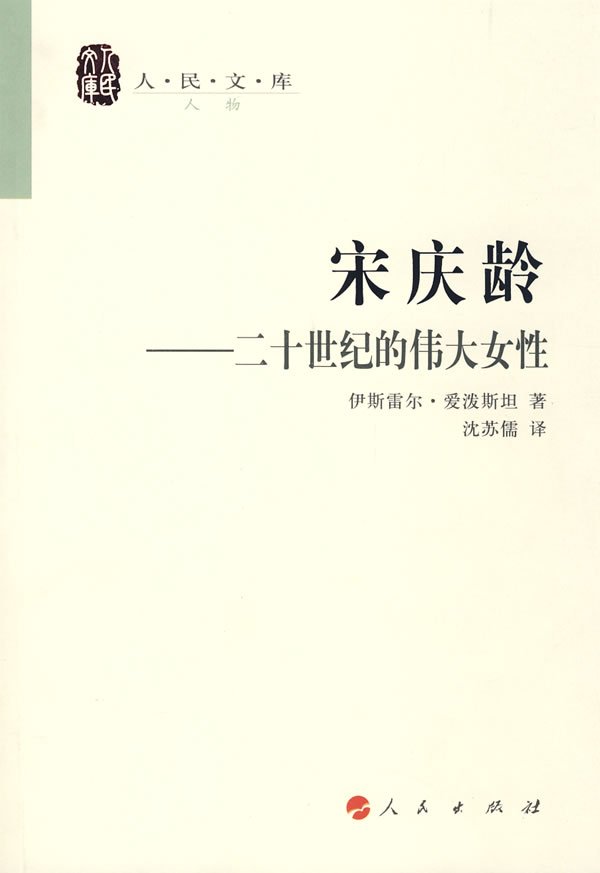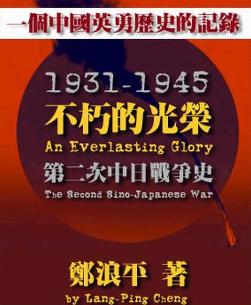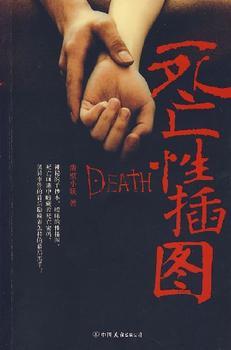第二性-第8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胎,她也会觉得这是她女性气质的一种牺牲:
她被迫在她的性别里看到一种祸根,一种虚弱,一种危险。有些女人把这种否定推向极端,在经历堕胎的精神创伤之后,变成了同性恋者。
此外,如果男人为更成功地实现他的男人命运而要求女人牺牲生殖潜能,那么他就会暴露出男性道德规范的虚伪性。男人普遍阻止堕胎,但一旦涉及到个人,他们又会把堕胎作为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予以接受;他们可能会采取一种无所顾忌的玩世不恭态度,自己反对自己。但女人通过自己受伤的肉体,可以感受到这种矛盾;就公开反抗男性的不诚实来说,她通常是太怯懦了;她认为自己是不公正的受害者,这种不公正使她违背自己的意愿成为罪人,同时她觉得自己受到玷污和羞辱。她以具体的直接形式,以她自己的身体,体现了男人的错误,但他却总是摆脱错误,把它推到她身上;他不过是用乞求、威胁、通情达理或愤怒的口吻说上几句,但很快就会把这些话忘得一干二净;而她却要用痛苦和血泪来理解这些话。有时他什么话也不说,一走了之;但是他的沉默和出走,更明显地违反了男性所确立的全部道德规范。
“不道德的”女人是讨厌女人的人最热衷谈论的题目,但这个题目并没有什么玄妙之处;
对于男人公开加以颂扬而私下却加以蔑视的专横原则,她们心里怎么能不怀疑呢?她们学会了不再相信男人说的话,无论是赞扬女人的,还是赞扬男人的:她们唯一相信的就是被掠夺的流着血的子宫,撕成碎片的深红色的生命,就是这个已不复存在的孩子。正是第一次堕胎,让女人开始“懂得了”这一切。对许多女人来说,世界将绝不会和以前一样。然而,由于没有普遍实行有效的避孕,堕胎在今天的法国,仍是那些不愿意让注定面临悲惨和死亡命运的孩子出世的女人,所能够采取的唯一手段。如斯特克尔十分公正指出的:“不准许堕胎的法律是不道德的,因为每时每刻都必然有人违犯它。”
避孕与合法堕胎,使女人有可能自由地承担做母亲的义务。就目前而言,女人受孕部分取决于自愿,部分取决于偶然。鉴于目前人工授精尚未普遍采用,想做母亲的女人——因为缺乏同男人的接触,或因为她的丈夫无生育能力,或因为她本人无法怀孕,可能不会如愿以偿。另一方面,女人又往往发觉自己是被迫生育的,违背了她自己的意愿。对怀孕和做母亲的体验,依女人实际态度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别,这种态度可以是反抗的、听天由命的、心满意足的或是热情的。应当看到,年轻母亲的公开决定和声明并不总是与她内心的欲望相一致。
年轻的未婚母亲也许会被突如其来的、不得不承受的物质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从而万念俱灰;不过她也可能通过自己的孩子,去实现深藏于内心的梦想。另一方面,对怀孕采取欢迎态度并感到快活和骄傲的年轻已婚女人,也可能会由于受她不愿意公开承认的幼年魔念、幻想和回忆的影响,而在内心深处对怀孕感到恐惧和厌恶。这就是女人为什么保守这方面秘密的原因之一。她们之所以保持沉默,部分是由于她们喜欢让自己为神秘所笼罩,喜欢那种唯独她们才有的体验;然而她们也为她们所感受到的矛盾和冲突所困扰。如南希·黑尔所说:
“对怀孕的成见是梦,它和临产痛苦之梦一样会被完全忘却。”这些复杂的真相,当时她们都很清楚,后来又被忘得一干二净。
如我们看到的,从童年到青春期,女人对母性的态度经历了几个阶段。对于小女孩,做母亲是奇迹和游戏,布娃娃代表未来的孩子,她可以占有它,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它;对于少女,做母亲则似乎威胁了她所珍视的完整人身,有时会遭到蛮横的拒绝。有时她怀着对怀孕的幻觉和种种焦虑,既害怕又渴望做母亲。有些女孩子喜欢对她们所照料的孩子行使母亲的权威,却无意承担其各种责任。也有些女人一辈子都持这种态度,她们害怕自己怀孕,却去当助产主、护土、保姆和忠实的阿姨。还有些人并非讨厌做母亲,而是由于对爱情生活或事业的过分专注才没有去做母亲。或者她们担心孩子会成为她们本人或她们丈夫的一种负担。
女人常常有意努力不让自己怀孕,不论是通过回避一切性交,还是通过采取避孕措施;
但也有些不承认自己害怕生育以及心理的防御反应确实在阻止怀孕的实例;通过医学检查,经常可以发现源于神经系统的机能紊乱情况。是接受怀孕,还是回避怀孕,取决于和对怀孕的一般态度相同的因素。在怀孕期间,女人的生育梦想和青春期焦虑又开始出现了;其感受方式,依女人与她母亲、她丈夫及她本人的关系而极其多种多样。
女人在轮到自己做母亲时,在某种程度上,她便会取代她自己的母亲:这意味着她的彻底解放。她若真诚地希望做一个母亲,就会为自己怀孕感到喜悦,鼓起勇气独自走完怀孕的全过程;但她若仍在受着母亲的支配,并且很愿意接受这种支配,那么她就会相反,把自己置于母亲的掌握之中;这时她就会觉得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和兄弟姐妹没有什么两样,并不是她自己的后代。她若是既希望又不敢解放她自己,就会唯恐孩子不会解救她自己,重新把她自己给禁锢起来,这种焦虑甚至会引起流产。而那种对童年所仇恨的母亲的有罪感,也可能或多或少地给怀孕带来不利影响。
女人同孩子父亲的关系也同样重要。一个业已成熟并且独立的女人,可能想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孩子。我就知道一个人,她一见到英俊的男人,眼睛里就会放出快活的光辉,这并非出于性的欲望,而是因为她断定他是个好父亲;这类人是热衷做母亲的女英雄,她们对人工授精的奇妙前景十分热心;如果这种类型的女人嫁给孩子的父亲,她会拒绝让他拥有对他们后代的任何权利;她会极力像劳伦斯《耳子与情人》中的保尔的母亲那样,在她本人和他们共同后代之间,建立一种排他性的联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女人接受新责任时,需要得到男性的支持;只有男人对她专心致志,她才会愿意对刚出生的孩子专心致志。
妻子越是幼稚怯懦,这种需要就越是强烈。有时,十分年轻的妻子在有了一两个孩子之后,便会变得惊恐不安,她对丈夫的要求也会变得过分。她会一直处于焦虑状态,想让他经常呆在家里;她会干扰丈夫的工作,把偶尔发生的小事当成多么不得了的大事;她还会经常让他帮她做这做那,以至使他无法在家里呆下去。
如果妻子爱她的丈夫,她就会想丈夫之所想:她是否会愉快地接受怀孕和做母亲的义务,这要看丈夫对此是感到骄傲,还是感到烦恼。有时,想要孩子是为了加强私通或婚姻关系,而母亲依恋孩子的程度,则取决于她的计划是成功,还是失败。即使她对丈夫怀有敌意,其处境将仍然可以是不同的;她可能会给孩子以强烈的专注,不许丈夫插手孩子的事,或者相反,她会对孩子表示憎恶,认为他是她极其讨厌的男人的后代。新婚之夜的粗鲁行为,可能会让此时怀上的孩子在出生前后都受到憎恶。托尔斯泰的妻子在日记中写道,她第一次怀孕使她在身心上都处于病态,这反映了她对自己丈夫的矛盾情感。
但怀孕首先是女人本人身体里演出的一场戏剧。她觉得这既是一种丰富又是一种伤害;
胎儿是她身体的一部分,又是靠她的身体喂养的寄生物;她既占有它,又为它所占有;它象征未来,当怀上它时,她觉得自己和世界一样浩瀚;然而也正是这种富足消灭了她,她觉得自己现在什么也不是了。新的生命即将出现,并将证明它自己有权独立存在,她为此而自豪;
但她也觉得自已被抛来抛去,是被动的,成为黑暗力量的玩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孕妇身体处于超越状态时,她又感到这个身体是内在的:它呕吐、不适,对自身进行攻击;它不再为自己而存在,所以它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大。工匠和行动者的超越性含有主观性因素;但做母亲时主体客体的对立却不再存在;她和消耗她的孩子构成一体,形成为生命所摧垮的一对儿。孕妇成了大自然的俘虏,她是植物和动物,是储备着的胶质,是孵卵器,是卵子;她把为自己有年轻平直的身体而骄傲的儿童吓破了胆,也引起年轻人的轻蔑嘲笑,因为她虽是一个人,是一个有意识的自由人,却变成了生命的被动工具。
通常生命只是生存的一个条件;它在妊娠期仿佛是有创造性的;但那是一种奇怪的创造,因为它以偶然和被动的方式完成。有些女人会从怀孕和哺乳当中享受到极大快感,以至希望它们能够无限地重重下去;一旦婴儿断乳,这些母亲便会有一种受挫感。这种女人与其说是母亲,不如说是受孕体,和高产的家禽没有什么两样。为了发挥她们的肉体功能,她们迫切要求牺牲自己的行动自由:她们觉得,她们生存的正当性,通过自己身体的被动生育力,得到了稳固证明。如果肉体完全是被动的、惰性的,它便不能体现超越,哪怕是以退化的形式;
它将会是迟钝的、无生气的;但当生殖过程开始时,这个肉体就会变成根茎、源泉和盛开的花朵,显现出超越性,呈现出一种面向未来的骚动,尽管同时它仍是一种粗俗的和现在的现实。女人以前在幼年断乳时所经历的分离,现在得到了补偿;她重新投身于生命的主流,再度同事物的整体,同无限的世代之链中的一环,同借助于另一个肉体并为这个肉体而存在的肉体,结合起来。当母亲感到自己在怀着沉甸甸的孩子时,或者当她把他紧搂向自己隆起的乳房时,她实现了在男性怀抱中所追求的(又很快得而复失的)融合。她不再是一个屈从于主体的客体,也不再是一个受与自由相伴的焦虑折磨的主体,她与那种暧昧的现实(生命)
联为一体。她的身体终于属于她自己,因为它是为孩子存在的,而孩子是属于她的。社会承认她拥有占有权,而且赋予这种权利以神圣的性质。她的胸脯,以前只有性爱的特征,现在成为生命之源,可以自由地袒露;就是宗教图画,也在向我们展示圣母玛丽亚坦胸露乳地哀求她的儿子拯救人类。随着母亲对自我的放弃,被她的身体和她的社会尊严所异化,她产生了愉快的幻觉,觉得就地本身而言,就某种价值而言,她是一个人。
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幻觉。因为她没有真的创造婴儿,他在她的身体里自己创造自己;
她的肉体所产生的仅仅是一个肉体,她根本不能够确立一种生存,这种生存只能自己确立自己。源于自由的创造行动,把客体确立为价值,赋予它以主要者的特性;而母体中孩子的生存正当性,却未得到这样的证明;他始终只不过是细胞的一种自然增殖,是自然的一种残酷事实,和死亡一样是依环境而偶发的,并且在哲学上与死亡是对应的。母亲有自己想要孩子的种种理由,但她不可能给这个独立存在的人(他明天即将存在)以他自己的生存理由,给他以生存正当性的证明;她是把他作为她的一般化身体的产物,而不是作为她的个体化生存


![同性婚姻合法之后,我们离了[娱乐圈]封面](http://www.xxdzs2.com/cover/1/122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