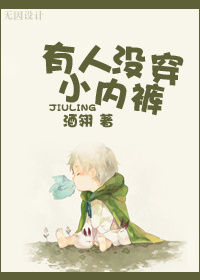有人骗你-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爷从地里做事回来,见一个乞丐裤子破得像渔网,人冻得全身发紫,缩在稻草堆里嗷嗷叫。爷爷回来,跟奶奶说了声,就给那乞丐送了条裤子去。其实,爷爷奶奶老两口儿总共才三条裤子,轮着换洗。不知爷爷奶奶又要节衣缩食多少日子,才能重新缝上一条裤子。
终于,爷爷身体渐渐虚弱了。先是腿弯儿发酸,后来脚发肿。于是一病不起,撒手西去了。他老人家只活了六十三岁。妈妈说,爷爷是累死的,穷死的。爷爷去世的时候,是否已穿上一条新裤子?
爷爷去得早,那会儿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上。爷爷在我脑子里的那些模糊印象,都是我根据爸爸妈妈断断续续的讲述,虚构出来的。爷爷的那些故事,我理不清时间先后,也弄不准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但却是真实的。不像那些线装书里记载的历史,看上去言之凿凿,实则大多是谎话。其实,不管二十四史何其洋洋,老百姓是另有一部史书的。他们更相信口碑相传的祖宗故事,时间长了,祖宗也许就在传说中封神登仙了。民间传说不理会正统,不讲究为尊者讳,也不为谁隐恶扬善,只认天地良心,便往往同正史相悖。
爷爷就葬在老屋对门的太平垴。上山的路很陡,顶上却平得像跑马场。满山千奇百怪的枞树,夜半风起,林涛凄厉,很吓人的。风清月朗的秋夜,山里的杜鹃叫得人们鼻腔儿忍不住发酸。那是我们王家祖祖辈辈的坟场。有年清明,爸爸带着全家老小上山扫墓。我们在枞树林里钻了好久,才找到爷爷的坟。坟不大,只是一个扁平的土堆,也没有墓碑。爸爸是凭着坟前的一块石头认准的。我顿时眼睛有些发涩。这就是我爷爷啊他老人家也算过了一辈子啊!我甚至怀疑爸爸是否真的认准了爷爷的坟墓,说不定我们祭奠的只是一堆没了后人的荒冢。
爆竹噼噼吧吧地响起来,我想爷爷是听不见这喧闹声的,他再也不会闷着头想什么大事情。老人家已经安安静静四十多个春秋了。
我的云南朋友
那年盛夏,昆明新知图书城邀请我签名售书,我立马想到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便欣然应允了。我很喜欢三联书店出版的书。再说昆明我还没去过,走走也好。长沙正热得要命。
下了飞机,远远地见位敦实的汉子,捧着束鲜花,小跑着过来了。寒喧间,知道他叫李勇,新知图书城的老总。我印象中的云南人正是这个样子,个子不高,能爬山,能吃苦。据
说当年身怀绝技,威震武林的龙云先生也是这种身材。
我平生头一次接受朋友的鲜花,居然有些拘谨。那是些百合花和黄玫瑰,清凉而芳香。上了车,听李勇一说,方知昆明新知并非三联新知,而是家规模颇大的民营书店。我向来对民营企业家多怀几分敬意,他们创业太不容易了。
我俩没聊上几句,就像是老朋友了。李勇说了个掌故,很好玩的。有次在飞机上,他巧遇一位著名笑星。这位笑星望见他,忍不住笑了起来,说:我演小品,就是您这套行头。原来,李勇穿着皱巴巴的西装,脚上居然还是波鞋。
李勇身上惟一显得豪华的,大概是他的肚子,腆得老高。我同他开玩笑,说中国人的皮带大抵上有三种系法:系在肚脐眼以上的是领导干部;系在肚脐眼以下的是企业家;正对着肚脐眼系着的是老百姓。李勇听罢,拊掌大笑。
那次我签售的是本旧作,小说集《没这回事》,不可能有火爆场面。李勇却总是说,昆明读者很喜欢您的小说,会排着长队的。我心里有底,笑而不语。
没想到签名售书那天,倒也来了不少人。一位老者说他步行几十里山路,大清早就等在书店外面了。老人想同我多聊几句,可后面还排着长长的队,我只好匆匆同他道了再见。心里歉歉的。
李勇一直站在我身后。我好几次回头,请他坐下,他总憨憨地笑,就是不坐下来。我正飞快地签着名,李勇低头轻声招呼道,王老师,您慢点儿签,喝口水吧,别太辛苦了。过会儿,他又低头说,王老师,人太多了,您就签个名字吧。后来我又见书店的营业员抱着大撂的书,站在读者队伍里。
其实,我早看明白了。李勇先是怕我很快就签完了,干坐着冷场,弄得我没面子。后来见排队的读者太多了,又怕真的辛苦了我,只让我签个名字了事。等我手脚快起来了,他又怕排队的人渐渐少了,场面不好看,就让营业员自己来排队签名。这个李勇,可真是个好人。
当时,我还有公职在身,签名活动完了,立即得返回长沙。李勇却太热情了,我只好在昆明勾留几日。他陪我去了抚仙湖。那湖里有种很好吃的鱼,可惜我记不得名儿了。抚仙湖正如它的名字,果然是沾着仙气的。比方说,抚仙湖同另一个湖毗连,由一河沟通着。可两个湖里的鱼不相往来,总是游到河中有个叫猫鱼石的地方,各自掉头回去。我不曾去猫鱼石看过,可我相信李勇是不会哄人的。后来从电视里知道,抚仙湖底居然还有座神秘的古城。
那次同行的还有贾平凹先生。平凹先生很有意思,哪里只要有他在,似乎就有了神秘的气场,况味就格外不同。抚仙湖边有座笔架山,平凹说,既然叫笔架山,我辈是要上去的。众人应和,拾级而上。快上极顶了,平凹从路旁树丛里捡起个瓦当,瞧了瞧,仍放回原处。我问,算个文物吗?平凹说,有些年代了。
下了山,平凹突然驻足,回望古寺,道,拿着就好了。原来,他还惦记着那个瓦当。我说,再上去一趟?平凹说,都是缘份,算了吧。
次日,我不能再耽搁,匆匆返回长沙。李勇又陪着平凹往大理去了。大理也是我神往已久的地方,好生遗憾。
从那以后,李勇会常打电话给我,邀我有空就去昆明玩玩。可我身不由已,总是走不开。我想念他了,就打电话过去聊几句。今年正月初,突然接到李勇电话,邀我去云南走走。我不好再推辞了,马上买了机票,飞抵昆明。李勇见面就说,这次没有活动安排,只是玩,一定要尽兴。
我已是自由写作者了,了无牵挂,正可担风袖月,云游天下。我们一道去了大理、丽江、建水。可我到底有些过意不去,怕误了李勇的正事。他却说,您来了,陪您就是正事。
大理的风花雪月,丽江的纳西风情,我是卧游已久的。没想到我从未听说过的建水,竟也别有情致。那里有保存完好的明清民居朱家花园、张家花园,有雄镇西南的古城楼,有土司衙门,有亚洲第一大溶洞燕子洞。最叫我难忘的是建水的哈尼族。李勇和建水的朋友陪我在哈尼山寨过了一天。正逢哈尼族最隆重的节日铓鼓节。家家户户都把酒席端出来,沿巷子摆成长龙,叫长街宴。头人举杯祭祀,祷告如仪,宣布宴会开始,全寨人齐声高喊阿毛坳姆!意思是过年好。席间,土坪里青年男女身着节日盛装,欢快地跳着铓鼓舞。男女老少兴致来了,随时站起来,抢过话筒唱山歌。可惜我不会记谱,那歌真好听。
我不善饮,平时在兄弟民族家做客,都不敢端酒杯。哈尼族人却是最善解人意的,你不喝可以,只是不要拒绝他们给你斟酒。你的碗本是满满的,仍不断有人过来斟酒,一轮又一轮。白酒、红酒、啤酒、饮料全往你碗里倒。我开玩笑说,这是哈尼鸡尾酒。多喝少喝随你,他们甚至可以替你喝掉大半碗,再同你碰杯,决不为难你。
我们要走了,全村人都放下碗筷,载歌载舞,夹道相送,一直送到村外的公路上。我们上了车,哈尼人扶老携幼,还在那里唱着祝福的歌。我眼窝子浅,忍不住潸然泪下。
可我没能登上玉龙雪山,终究是个遗事。去丽江那天,正好大风,上雪山的索道停开了。我们只好站在云杉坪,遥盼雪山云雾呼啸。那是座神山,想必是人们生来死去灵魂必经的通道吧。
有天,李勇专门打电话告诉我,他已登上玉龙雪山了。他知道我一直惦记着那座神圣的雪山,就说下次您来,我再陪您上去。
朋友和啤酒
那时,我还在湘西某市做小公务员。一日,《湖南文学》编辑黄斌先生突然去了我那里。于是呼朋唤友,举杯豪饮。敝乡酒风甚悍,非醉不能解瘾。自然要喝白酒。通常先是连喝三杯,热热肚子。酒桌上总要说些好话的,并无规矩,随意道来。就说这三杯酒,有人会说三生万物,有人会说三生有幸。那回相聚的都是些文人,就说文章总得三段才是回事儿,无三不成文,先干了三杯罢。接着就是各自举杯,囫囵敬一圈。一一碰过,这叫见面酒。再就是各自找人喝了。酒桌上没有道理,却尽是道理。比方我小你三岁,敬兄长三杯;比方你我
两年没见面了,至少要同饮两杯。席间不是七八人,就是上十人。喝到这会儿,每人多少也是十来杯酒下肚了。吓人的却是那酒杯,不是那种剔透玲珑的高脚玻璃杯,而是白瓷茶缸。酒量小些的,没干几杯,就天转地转眼珠子不转了。
我们都喝得差不多了,又嘻嘻哈哈,朝歌厅呼啸而去。侍应生过来,问喝什么茶。有朋友大手一摇:喝什么茶?啤酒!喝什么啤酒呢?我问黄斌,他是客人。黄斌说,金威吧。侍应生愣了愣说,金威?没有。我也没听说过金威啤酒,调侃道,我们这里是山区,好啤酒进不来。黄斌说,金威是新品牌,上市不久,估计你们这里还没见过。
我们只好喝青岛。我酒量本不大,只是年轻,什么酒都能喝上几杯。黄斌却说我海量,事后还写了篇印象记,说我喝酒是三不主义:酒杯不论大小,度数不论高低,颜色不论深浅。此文流毒甚广,贻害无穷,可把我整苦了。每逢酒席,我都推辞不喝。可不管是否见过面的朋友,都会引经据典,黄斌如何如何说,指认我本有喝酒前科,而且酒量不小。
当时我写小说只是业余爱好,并不知道自己将走怎样的路。多喝了几杯白酒,又来喝啤酒,我很快就醉眼朦胧了。包厢装修得有些像湘西吊脚楼,极有情致。我坐在吊脚楼里,望着朋友们在舞池里飘飘欲仙。我没下去,只是枯坐发呆。黄斌陪着我聊天,啤酒杯没有离开过我们手。迪士科舞曲响起来,黄斌招呼我下去蹦几下。我仍是不动身,黄斌自个儿出去了。舞曲激烈,震耳欲聋,灯光明灭很是眩目。一种幻灭感没来由地流过心头。我鼻腔有些发酸,便猛喝一口啤酒,把什么都咽下去了。
两年之后,我调到长沙。那是盛夏,热得难受。黄斌替我接风。我俩在临街的一家酒吧靠窗对坐着。酒吧里倒是清凉。这回喝的就是金威啤酒了。黄斌是个认牌子的人,抽烟多半抽三五,啤酒就认准了金威。我先闷了一大口,感觉真不错。黄斌话不多,总是低头喝酒,一副沉思状。我同黄斌交往很深,有话就说,没话就沉默着。我俩整个下午就呆在酒吧里,东扯西扯,不知说了些什么。只是身旁的空啤酒瓶慢慢多起来,足有十几个。黄斌突然笑道,好好干吧,看哪天混辆车子,混部大哥大。那会儿手机还很奢侈。我摇头笑笑,心里很茫然。
黄斌后来去了北京,仍是做编辑。有回我去北京签名售书,黄斌请我领略京城夜生活。我们去了家据说很有名的酒
![[鼠猫]叮!有人对你说谎by茶叶罐封面](http://www.xxdzs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