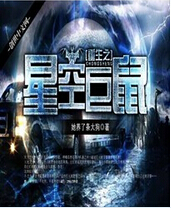在亚洲的星空下-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样好吗?”
“为什么要问我?”
“我想知道你的看法。”
虚荣的我,有种受重视、被放在心上的甜蜜感。
“不管你怎么决定,我一定站在你这边。”所以就心甘情愿了。
“你说的没错,我是不喜欢现在做的事。所以我想了又想,既然我又有了创作的欲望,那么不妨接受录音演奏邀请,可以躲远一点隐居起来。”
我不禁莞尔。“真要出了唱片,你能躲到哪里去?而且,你已经被后浪推开,被浪花淘去了的人物,谁还找你录音啊?”说到后头,我声音已止不住笑。
“说的也是,我已经江郎才尽,没有人会找我。”舒马兹杨也索性开起玩笑。
我们对望着笑,所有的烦恼好像都没了。望着望着,他靠过来我偎过去,手臂缠上他的脖子,他双手拢住了我的腰,顺势一斜,倒在地毯上。
身体跟身体就那么相叠。他的重量压在我的重量之上。
“今天我不回去了。”他说着,亲了我一下,又一下,再一下,密密且麻麻。
我双臂紧勾着他的脖子,这样被我缠着,他即使想回去也走不了。
“你想回去也走不掉。”我在他耳边轻声说。
他低笑出来,舔着我的耳朵。
暖气变得太强,一切彷佛都融化掉。
第十一章
真的,说舒马兹杨过气了,那实在太小看他。所以,尽管他心中是那样的打算,事情总没有那么美好简单。
录音演奏不仅是躲在幕后奏奏弹弹就可以。不管他愿不愿意,都以一种形式,暴露现身在公众之前。他当年初成名时,录制的唱片对他的名声绝对有宣传与推波助澜的加乘效应,甚且以极快的速度,用一种无形的方式,将他推介到大众之前。
如此,与他重新上舞台着实没什么差异。
还有,还要应付乐评家的批评,那更加令他烦厌。
舒马兹杨不是天生亲切友善友爱世人的人,我领教过。重新出发,乐评家不会轻易将他放过。
所以,他迟迟不想行动。
我想他根本不愿意。
“你觉得失望吗?”他问我。我们在餐厅吃饭,四周全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和工作人员。
舒马兹杨不只与我,也和别人这样一起吃过饭。所以,越是公开,越是平常,我们和其他在餐厅里吃饭的人没什么不一样。
“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我没回答,反问。老实说,私心里,我的确是觉得他“人在福中不知福”。他占尽一切有利的条件,却对之嗤之以鼻。就好像出身富贵的富家少爷,不屑自己的家世,口口声声要和平凡人一样。
“你问。”舒马兹杨只是喝着咖啡,似乎没胃口。
“你曾经无数次在舞台上,在无数观众面前展现了音乐的神奇,使人感动,明了音乐可以达到忘我的极致。我相信只要有过那种经验,一定很难忘怀。你难道一点都不怀念留恋那种在舞台上与自己的音乐结合为一体,激越、昂扬、热情的感觉,和乐迷感动热情的欢呼和掌声吗?”
舒马兹杨表情变沉肃,一口一口喝着咖啡。
“我的确是想过。”咖啡喝到尽,舒马兹杨终于承认。
“那么你为什么不愿意……复出?”他说他是累了,这时他的表情如此阴暗,我突然发现似乎触到了不该触的什么。
“我拿什么复出?”神态更阴晦。“理儿,我也不愿承认的,可是,事实是,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舒马兹杨’了。”
啊!这句话像雷击,我震栗一下。
“你为什么这么说?我才听了你的演奏,你把我父亲的曲子诠释得那么好!”我不相信他的话。
“那是不够的。”舒马兹杨一直不愿去谈去碰触的,我却残忍的让他拿刀去挖自己伤口的肉。“我自己知道,我顶多只是在原地打转。”
“这样就足够了!”
“不。”刀子利,挖得深,只怕见骨。“我有我的自尊。如果不能超越以前的我,只是停留在原地,我的姿态只怕会更难看。那些乐评家说我江郎才尽,某个方面来说,的确如此。”
我吃不下饭了。
“对不起,我……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样残忍逼他承认,又说出这一切,我难堪难过的抬不起头。
平凡的我,忘了他的骄傲。像舒马兹杨这般叱咤过的人,感触当然更多,只是他不让他的伤口暴露,不给人看见。
“没关系,你只要不对我失望就好。”他说:“以前我不相信的,但真是神奇,遇上你,我忽然又有创作的力量欲望。可是,这毕竟不是神话传奇,然后我就能一下子才情尽露,更胜从前,重新又扬名世界。”到最后他淡淡笑起来。
“那么,你说可以接受录音演奏是因为我,而与你母亲的妥协?”
舒马兹杨没回答。
沉默就是默认吧。所以我虚荣又一厢情愿的以为如此。我也愿意相信,的确是因为如此。
我承认我肤浅,我爱舒马兹杨这“为了我”的举动,知道自己被他收在心里重视着,天涯海角都愿意追随。
“舒马兹杨。”我唤他。如果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我大概会扑过去。
“你不觉得失望吗?我到底真的过气了。”舒马兹杨很认真,蓝眼珠更晦涩。
“请你不要这么说。”我吸口气,“曼因坦教授将我介绍来这里,表示他相信你,你一定有你的过人之处。不管你回不回舞台,能不能再次立足于乐坛中心,我一定都跟着你。其实,像我这种没天赋的学生才真是累赘;能跟着你学习,其实是我运气。”
我没有意思谄媚、讨好或安慰舒马兹杨。但他眨动眼,蓝眼睛变得温暖柔和。
我想,这种时候,无声胜有声。舒马兹杨只是看着我,伸手过来握我的手,再没有其它太多的言语。
王净打工回家带了一瓶红酒,冰箱有昨天吃剩的炒面,红酒配炒面,我们就那么吃喝起来。
“这个要庆祝什么?”我举举红酒瓶。
“我领薪水。”
“还有呢?”
王净呷一口炒面丝,配饮一口酒。
“他说他要过来柏林,要跟我重新开始。”
“他?那个黑龙江?”我大口吞酒,呛到了。“那你怎么说?”
“不要。他来我也不见。”
呵,我喜欢她的直截了当和干脆,虽然这样的决绝大概纯粹只是理论上。
“他要求你呢?你狠得下心?”
“你再瞧我狠不狠得下心。”王净横我一眼,神态和声音里的那娇狠样我怎么学也学不来。
“最好是这样。”我是甘拜下风。她性格里的精采丰富有时教人艳羡。看王净,偶尔我会有“李世民十八岁出来打天下”的联想。我读长诗,除了那长城玉门关,就想看汉唐盛世的长安。
“你这个人真怪,”王净放下酒打量我。“你在劝我跟他彻底分是不?人家不都是劝和不劝分?”
“我什么都不劝,对那种劝慰排解的角色没兴趣。”是的,我一直忘了承认,我其实不是那种纯洁善良的族类。
不过,即便如此,也请不要理当如此的就用类推法将我想成狡猾邪恶的女子。我承认,我的思考里有着世故的污秽,我的性格里也染了一点现实的机巧势利,不尽然的全是风花雪月,但这也只是顺应进化的趋势与因应阶级社会的形势,毕竟,一个人要在欧罗巴这块大陆顺利过活并不容易。
我明白自己是不完美的,有太多的缺陷,我也不想掩饰。我想,我大概也只能这样了,所以心安理得:何况,我并没有要求别人来欣赏喜欢我。
“你跟‘朋驰’的事都解决了吗?”红酒香醇,炒面可口,想想好像没什么好不满足了。
“我跟罗蓝德有什么好解决的?他离婚是他的事,可不关我的事。倒是你跟你那个舒马兹杨的事解决了没有?”
好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摇晃酒杯,灯光下,脸庞映上美丽的玫瑰红。笑吟吟说:“解决不了。我也不想解决。”
“什么意思?”
“就这样下去的意思。”
奇怪,我竟与王净说那么多。但想想,她在我肩膀流鼻水口水哭累过,我的喜怒哀乐情绪在她面前搬演过,心内的事如此好像就比较容易开口说了。
一杯葡萄酒喝到干。有一天,我真怕我会因此酒精中毒或者更不济,上了一种不该的瘾。
然后,我遇到杜介廷。
很偶然,也不恰巧。这天我有事到了自由大学附近,经过我跟他分手的咖啡馆时,还未来得及触景伤情便那么撞上了。
是杜介廷瞧见我,先喊我的。不用说,我很意外。更意外的是,他身旁居然没有跟着那个章芷蕙。
“好巧,一来就遇见。”我先开口。
杜介廷低下头,两眼看向我。“好久不见了,理儿。你好不好?”
哦,杜介廷问我好不好。
“很好。”我给一个制式的答案。
“理儿!”他衍出以前的习惯伸手抚拨我的头发,旧情绵绵。“要不要进去?我请你喝杯咖啡。”
“不了。我还有事。”
他低下脸,鼻息喷到我脸上。“你还在怪我?不原谅我?”
我退后一步,他换上一脸落寞,“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你生气是应该的。”
“我没有。反正都过去了。”
“可是我打电话过去,你也不肯回我。”
“我忙。”
“你知道的,理儿,”他抬头,两只眼罩着我,“即使和芷蕙交往在一起了,但是我一直没有忘记过你,心里一直惦记你。”
不,我不知道,压根儿也不知道。我不稀罕他施舍的惦念,因为我早已经不想他了。我不否认,我失魂落魄过一阵,也难过伤心好些时候,不过,档案都关了,而且已经被注销。
“你跟章芷蕙住在一起了,不必再说这些。”
“我只想跟你道歉,希望你明白,我一直是关心你的。”
那么,我是应该感谢喽。
可实在不必。那些不必要的关心。
柏林的冬天那么冷,我曾那么怀念他宽阔的胸膛和暖热的体温。但那样的缱绻都死伤破碎光了,我也不想再拼凑那些碎片。
“如果今天没碰到你,我也打算去找你。理儿,我们好好谈一谈好吗?”
“我没有时间。”还有什么好谈的?我差点怔愣。
“理儿!”杜介廷出手拉住我。
“我真的有事。”我挣开。
不是我心胸狭窄小家子气对他甩了我的事还耿耿于怀,只是这样拉拉扯扯不成体统,我又不是来这里找他叙旧情。
请不要说你听出什么语病,鸡蛋里挑我骨头,质疑我什么时候讲究在乎过体统。事情就是这样。既然不爱我了,把我像垃圾一样倾倒掉,就不要再碰我。
我不是那个善良美丽的白雪公主:我是那个每天问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丽女人的后母巫婆。
这一切,我都承认了。那么,就请不要说我没有气度兼加没有心肝。
我的心,被杜介廷倒垃圾倒掉,被舒马兹杨捡到了吃掉。因此,对于旁的人,我再也没有了心肝。
星期四,舒马兹杨的办公室又上演了一场争执的好戏,一串串盲流搞不清楚状况全又被吸引过去。
原因无它,伟大的舒马兹夫人又大驾光临了。
嘉芙莲秘书看到我,没什么表情,我也觉得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没有坚持到最后,等着给舒马兹杨也许一点的慰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