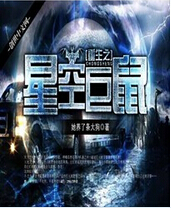在亚洲的星空下-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跟我说话时,她是不笑的。
我原以为那是她的习惯。毕竟,没有人规定跟人说话时一定要带笑。尴尬的是我,人家没必要陪我干干的傻笑。
开水滚了三分钟。我将面条捞起来。
“对了,你的朋友,他说他姓杜,有电话找你。”李红吞了几粒维他命,仰头喝了几口水。
“谢谢。”李红怕胖,饭都不多吃,身体又需要营养,所以柜子里全是瓶瓶罐罐的各式维他命。
到底也是药。我第一次遇到吃药吃得这么起劲的人。
我加了一些酱油和蒜头,和着面条拌一拌。才吃一口,李红闻到蒜头味,姣美的眉形又扭皱起来。
吃第二口,门铃响了。戏剧性的,李红打结的眉眼往鬓旁飞了起来,踩着光脚跑了出去。
我先听到开门的声音,然后是低低含糊的男声。跟着——一声“嗯”,打鼻腔哼出的,像撒娇,更像小狗要宠的叫声,不客气的穿进厨房。
我筷子一叉,一口面条鲠住喉咙噎着了。
就是这样,我才不习惯。
搬来一个星期,我就想搬家了。
“嗨,安德鲁。”男人跟着李红进厨房,我打声招呼。
安德鲁一头灰褐的金发,股票操作员,李红的男朋友。他几乎天天来,有时过夜。每次他来,李红都会发出那种像小狗惹怜的撒娇声,酷傲的表情全都不见,比我见过的任何小女人还要小女人。
一个人在男人面前身后,怎么能差那么多?
所以我不习惯。
当着我的面,安德鲁给李红一个辣辣的法式深吻。
安德鲁还没吃过午饭,李红立刻像个小主妇般忙碌起来。
我悄悄退出去,识趣地把厨房全让给他们。
柏林消费指数高,静子好心介绍我这个住处。我现在住的房间就是她以前待的。到维也纳之前,她和李红一起住了差不多一年。可是,她从没跟我提过李红特殊的习惯及性情。
我不是排斥,只是不习惯。
厨房传出咯咯的笑声,那种抽着气,可以显得出很娇俏的笑法。我曾试着学那种笑的方式,到底学不来。
那其实是很不自然的笑法,自觉性地控制鼻部与喉咙的发音位置,是有意识的、按照某种通路把笑声发出来。那是需要练习的,我学不来。
虽然不习惯,我还是镇定地把一盘面吃光。
这也算是生活的历练。
不,没有那么刻苦辛劳。别把我想成穷苦思乡的悲剧美少女。只不过,我母亲大人说的需要校正——美丽的女子并没有比较容易过活。更何况,我美得不到位。
要像李红那样,我这辈子是达不了那层次。
我跟杜介廷说我想搬家。
“不是才刚安定下来,为什么要搬家?”他问。热咖啡的烟雾袅袅弥漫过他的眼畔。镜片后的那双眼亮得有神,丝毫不被雾气遮拦。
我们坐在柏林自由大学附近的咖啡店里。人声鼎沸,热烘烘,也闹烘烘。
不是真正的那种吵得人神经衰弱的“闹”。只是一种“人气”。
“住不惯。”我看看四周。
“怎么会?你那地方我也看过了,虽然稍远了一点,但设备齐全,环境不算差,房租又便宜,为什么不习惯?”杜介廷好纳闷。
难怪他纳闷。换作我,我也纳闷。
我没有那么娇嫩。但我不能告诉他真正的原因。
“只是不习惯。我想看看有没有其它更适合的住处。”
杜介廷不出声地看了我半晌,伸手摸了摸我的脸颊。
“真想搬的话,我看干脆就搬过来跟我一起住好了。”他住的公寓有个大客厅和露台,电气、暖气各种设备样样齐全;窗子望出去是绿荫荫的公园和宽宽的天空。对普通的留学生来说,算是很享受。
“别开玩笑了。”我让他抚摸我的脸,没有拒绝。
“我哪跟你开玩笑了?”他揉揉我的头发,倾身越过桌子亲了我一下。“我央求我的女朋友搬来跟我一块住有什么不对了,嗯?”
女朋友——
是的,没错。我是有男朋友的。
到欧洲之前,我们——杜介廷和我——就相识了。他早我一个月出来,只是他到的是柏林,我去维也纳。
这半年多,我们全靠电子邮件和电话通音讯。他功课忙,每天却总不忘发邮件给我,对我算是有心。好不容易我也来了柏林,他的欢喜可以从他眼里的亲腻看出来。
当然,我是喜欢他的。有这样的男朋友,算是我运气。
杜家是做生意的,家族经营知名的钟表公司,连锁店遍布。杜介廷是家中独子,有个妹妹年纪与我差不多。他条件好,经济情况佳,长得显眼——或者,白话一点,英俊耐看。这样炙手可热,他为什么看上我?
我不是没信心,只是免不了疑惑。
我母亲大人说的,美丽的女子容易过活,是因为身旁多半会有好条件的男子呵护的缘故吗?
我是这么怀疑。但从来没有求证过。
我母亲当然是见过杜介廷的。不过,她没说什么,我也就更无从求证了。
“这样不好,会妨碍你念书。”我低头喝口咖啡,嘴上还残留着他嘴唇的触感。
“一点都不妨碍。你搬过来,什么麻烦都没了,我也可以天天见到你。”
还是不妥。忙碌起来时的那种焦头烂额,一点琐事就可以将人逼疯。杜介廷功课忙又重,我不想成天在他眼前牵牵绊绊的。
“你不相信我?怕我把你吃了?”他开句玩笑。然后稍稍压低声音说:“这半年我想你想得心都疼了,可把我想死了!过来跟我一起住,嗯?理儿……”越说越低,声声蛊惑。
我蓦地红脸,被他声音的黏稠沾了一身。
可是,他过来拥我、吻我时,我没有回避。我说过,我是喜欢他的。
没有人侧目。我们和店里其他那些喁喁细语的情侣没有两样。
“让我想想。”我伸手搂住他的腰。
“我就是怕你想。”他叹口气,好像真有那么几分无可奈何。
我瞅着他。他揉揉我头发,眼底尽是泄气;在我嘴唇上啄一下,将我搂进怀里,妥协说:“好吧,你就好好想一想。不过,别让我失望。”
我嗯一声,偎着他。
这样偎在他怀里,感觉十分的温暖,甚至,沉溺在这样的舒适。
我抬起头,看着他那有棱有角的侧脸。想想,我何其有幸,这样一个万中选一的男人会是我的男朋友。而且,最重要的,他的心里搁着我。
“介廷……”我忍不住喊他。
“怎么?”他回我一笑。
“没什么。”我摇头,也笑。
他几分亲爱几分呵疼的吻吻我的脸颊,大手包着我,就那样融在初薄的光雾中。
恋爱是甜蜜的。巧克力式侵袭的浓郁的甜。我正在品尝这样的甜蜜。
第二章
我准时走进办公室。当然,不会有人欢迎我。
好不容易耶诞过去了,新年也过去了,舒马兹杨终于回了柏林,拨空施舍给我。姑且不论他是否真的离开过柏林,对于他的“大方施舍”,我是应该感激的。
我走过去,对半个多月前见过的秘书说明身分;她瞄我一眼,手指着一旁的沙发,说:“请你稍坐一下。”态度算是客气的,但也只是点到即止。
我等着。约莫五分钟,秘书开口叫我:“呃,卢……吕小姐……”搞不通那拗口的中文姓氏。
“刘。我姓刘。”我带着笑协助她。不怪她,我不是什么要人,没有重要到让她必须确切地明了我的姓氏发音不可。
“刘小姐。”秘书点个头,还是那一号不变的表情。“请跟我来。”
她一直走到最里头,敲了门进去,说:“舒马兹杨先生,刘小姐到了。”这一次总算将我的名字完整不差地拼念出来。
桌子后面的人抬起头,扫了我一眼。
秘书又说:“费曼先生约十点半和你见面。”
十点半?现在是十时过一刻。也就是说,他顶多给我十五分钟。不,可能十分钟都不到。
秘书退出去。我赶紧说:“你好,舒马兹杨先生。我是刘理儿,谢谢你拨空见我。”
舒马兹杨又扫了我一眼。看得出来,不大有兴致。
“你说,是曼因坦教授介绍你过来的?”他开口的第一句话,语气中的淡相当明显。
“是的。我有曼因坦教授的介绍信。”我赶紧走过去,双手奉上曼因坦教授特地为我写的介绍信,不敢浪费他的时间。
他接过信。那刹间,一股隐约的香味匆忽窜来,暗中偷袭。我一时忘却,脱口说:“好香!”
然后我就知道要糟了。
他抬抬眉,往我望来。
我连忙解释:“我是说你身上的古龙水。”
他连眉毛都没动一下,说:“谢谢。”
他大概会认为我是轻浮的女孩,第一次碰面的男人竟然就说他“香”。我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怎么会脱口说出那种没脑筋的话?我并不是那种天真无知的十六七八岁的小女孩的。
心头忐忑着。
是的,我承认,我怕舒马兹杨对我印象不好;怕刚刚那脱口不得体的话坏了我的形象。
学音乐也好像做学问一样,只要有老师肯收留,那就没问题了。当初因为曼因坦教授收我到门下,我才得以进入维也纳音乐学院;后来曼因坦教授因为健康缘故,离开音乐学院,将我转介给舒马兹杨,我只好收拾包袱到柏林。
当然,留在音乐学院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只是,我一直随曼因坦教授学习,没有人会主动而且太乐意接受别家的门徒;更何况,教授又将我介绍给舒马兹杨。
所以,姑且不论乐坛或舆论对舒马兹杨的评论如何,他是我剩下的希望。
也不是没退路,我可以重新再来。但路途太漫长了,而且,我也没有那种本钱和时间挥霍浪掷。
“你说你叫什么名字?”舒马兹杨看着信,皱着眉。
“刘理儿。”我恭敬回答,一刻都不敢耽误。
舒马兹杨没有浪费力气跟我客套。冷淡、不亲切,这些都符合我对他的印象。
但说他傲慢……嗯,他的架子是大一点,却倒没有我想像中翻着白眼看人、鼻子朝天的模样。
我不知道曼因坦教授在信里是怎么写的,舒马兹杨的眉头还是皱着,好像曼因坦教授给他带来了什么大麻烦。
我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不敢有太多太大的脾性,站在那,等着徒刑宣判似。
“唔……”舒马兹杨终于开口,将目光由信件调回到我脸上。“既然是曼因坦教授介绍过来的人,我不会拒绝。不过,我事情实在忙。这样吧,这里有许多优秀的老师,我将你介绍给他们。”
“可是,曼因坦教授介绍舒马兹杨先生你……”我有点矛盾。他没拒绝我,言下之意答应让我进舒马兹音乐学院,可他也不收我。
他不收我,我其实也不觉得失望。可他要将我随便丢给其他人,我可也不愿意。
我有我自己的盘算。舒马兹杨不收我那也是好的,我可以回维也纳求曼因坦教授转介我到莱比锡或科隆,或者,就继续留在维也纳音乐学院那更好了。
但想,柏林有杜介廷,我又舍不得。
“你真的想跟着我学习吗?”舒马兹杨忽然抬头,冷不防追问。眸色里一抹似笑非笑的讥嘲。
我楞一下,有点慌了手脚,一丝的狼狈。硬着头皮说:“当然。所以我特地从维也纳跑来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