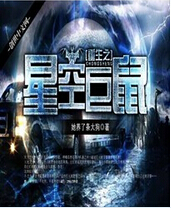在亚洲的星空下-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教人惋惜。更不明白的是,他怎么会看上那个东方女孩,那么不起眼……”
我悄悄退开。说真的,我也不懂,也有和她们一样的疑问。
可以说,我对自己缺乏信心。不过,这不是“信心”就可以说明的事。
回到座位,财务顾问史密特先生不断说些他到各地旅游的所见所闻,企图让气氛活泼起来。我也很配合,他有问,我必答,也不再回应布林克曼夫人偶尔抛出的一两根隐形的刺。
项庄舞剑,项伯起舞翼邦。一场“鸿门宴”,到底还是让我全身而退——应该说“几乎”。
吃完饭,客人都离去,舒马兹夫人留舒马兹杨和我过夜。舒马兹杨回绝,舒马兹夫人像也在意料中,望我扫一眼,说:
“我就开门见山直接说吧。你们的事,我不赞成。理儿小姐,你不适合我儿子,你跟他不相配。”
“我也没指望你会赞成。晚安,母亲。”舒马兹杨牵了我。
但我没他那么从容。当面被人指陈和舒马兹杨不配,尤其对方又是他的母亲,毕竟是不好过的事。
“你做什么事都要这么任性?当初劝你别跟那个日本女人来往你也不听,消沉了这么久又不肯振作,现在又想重蹈覆辙了?”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你如果知道你在做什么,就不会回绝慕尼黑歌剧院的邀请和玛琳夫人的赞助了。”
“那是两回事。时间晚了,我们要告辞了,晚安。”
“等等,阿萨斯——”舒马兹夫人阻止说:“我还有话要说。你如果真要跟理儿小姐,我也不反对,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舒马兹杨与我对望一眼。沉声问:“什么条件?”
“重新创作,回舞台。”舒马兹夫人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来,很有重量。
“办不到。”舒马兹杨一口回绝。
“就算是为了理儿小姐,你也不肯?”这一招借刀杀人,舒马兹夫人实在太厉空口了。
舒马兹杨脸色变得越发难看,不看我,语气僵硬说:“不管任何理由,我都不会再上舞台。”
“听到没有?理儿小姐。”舒马兹夫人转向我,“即使我承诺答应你们的事,只要他重回乐坛,他也不肯。这表示你在我儿子心中一点份量也没有。我很抱歉这么说,不过他心里我想根本没有你。他曾为了一名日本女人作曲,还打算公开献给她,但他显然没打算为你这么做。”
舒马兹夫人不惜泄露这件事,大概想即使逼不回舒马兹杨上舞台,也可将我逼开。
她的打算也没错。这样被比较,尽管我早知道,下意识还是有点不是滋味。
我感到舒马兹杨牵着我的手紧了紧。
“晚安了,母亲。”他不多废话,拉了我离开。
冷风迎面扑来,我打个寒颤。
原以为可以全身而退,结果,还是受了内伤。
这天晚上,舒马兹杨送我回家的途中异常的沉默。
他的过去不是不可以碰——他都已经亲口告诉过我了;问题是碰的方式。舒马兹夫人那样赤裸裸的捅一刀,准确无比的刺进要害。
“晚安。好好休息。”舒马兹杨一直送我到门口,轻轻吻我的脸颊。
他是有心的。虽然一路沉默,沉寂的气氛像在拒绝。
“晚安。”
其实,怎么能睡得好。我想睡都睡不着。
王净睡了,我不想吵她,但捱到半夜快三点,我从床的这头换到那头,从床上坐到床下,还是睡不着。
失眠教人难受,那是当然的。想想,闭着眼数到一千九百九十九只羊的时候,那第二千只羊却任凭你怎么赶怎么哄怎么威吓胁迫也不肯跳过那栅栏,还在那里不断的咩咩叫,已经跳过栅栏的一千九百九十九只丰跟着咩咩叫起来,耳鸣加混乱,让人完全束手无策。
所以我放弃了。
我坐在地板上,想了许久,打了电话给静子。
“静于,是我。理儿。”我知道我是有些反常。
“理儿?”在维也纳的静子被我吵醒,声音带着浓浓的睡意。“现在几点了?你怎么还没睡觉?”
“三点。”柏林和维也纳零时差,我的半夜也是静子的半夜。“对不起,吵醒你了,静子。”
“没关系。”静子的声音清醒起来。“好久没见了,我很怀念你的声音呢。”
“你最近好吗?”静子学的是小提琴,不会比我轻松。
“还顺利。你呢?”
“从头来。先前还被要求跟小朋友一样使用节拍器抓节拍,只准弹练习曲和技巧难度低的曲子,现在升入‘中学’了,可以弹一些难度稍高的曲子。”我没打算说这些的,说出来反而缓和一些情绪。
“啊?!怎么会这样?舒马兹杨先生还真是严格!”
听到舒马兹杨的名字,那第二千只不肯安分的羊又咩叫起来,烦得我耳鸣。
“静子,我去维也纳找你好吗?你能不能让我在你那儿待几天?”
“当然好啊,欢迎你来。不过,理儿,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你怎么会这么以为?”
“我听你的声音有点消沉,好像有什么苦恼。”
静子一向细心,再想我半夜三更莫名其妙的突然打电话过去,真没事也许才奇怪。
“是有点为难的事。”
“你不会要跟我说,你爱上舒马兹杨先生,要跟你男朋友分手吧?”静子半开玩笑,嘻嘻笑起来。
“对了一半。我跟杜介廷早已经分手,现在和舒马兹杨在一起。”
“不会吧?理儿……”静子吓一跳!“舒马兹杨先生听说有许多女朋友,你怎么会跟他在一起?”
原因太冗长,解释起来更大费周章。我解释得不清不楚,静子大概也听得迷迷糊糊。不过,重点说清楚了就是。我和舒马兹杨有了关系;现在我想去维也纳。
静子说:“你随时来,我都欢迎,理儿。可是这样好吗?我觉得你在逃避。老实面对事情比较好吧?问题都会在那里,不会消失,你躲得远远再回去,它还是在那里。一定要解决的。”
“可是待在这里我……睡不着。”
“你以为来维也纳你就睡得着?”
大哉问。不必说,连过路的都知道答案。
“我该怎么做?静子,”
“我是很想给你建议啦,理儿。可是,这种事你最好自己想清楚,自己处理。”
“如果我想不清楚呢?”
静子很干脆。“想不清楚就不要想了,顺其自然。”
这个“干脆”在我意想外。陷在泥淖里,以为思考就一定要有一个答案。
没有人规定饭吃不下去就不能不要吃;歌唱不下去不能不要唱。“想不清楚就不要想”——事情,好像变得意外的简单。
可是,一切都是理论上的。
看看时间,差一刻就四点,睡不着就是睡不着。到这一刻,我也不得不放弃。
也谈不上受煎熬。没那么严重夸张。
我不是在意舒马兹杨肯不肯为我作曲,肯不肯为了我而答应他母亲的条件重回乐坛、舞台。我也没想与他恋过的那名女子相比较,没想贪心的希求自己在他心中必是特别的存在。
每个人都会恋爱,虽然比重不一样,可我想没什么“特别”这回事。“特别”一般和“寻常”相比较。可是“特别的存在”和“寻常的存在”其实没什么不一样,同样都存在。
都这么清楚明白,没出息的我偏就是被舒马兹夫人那些话侵略影响。我到底还是有女子天生的虚荣。
楼底下传来汽车辗动停熄的声响,因为夜深人静,格外的清楚,甚至惊心动魄。
不一会,对讲机响起来。
我跳起来。
门被轻扣。舒马兹杨出现在门外。他还是晚宴那袭装束,两眼和我同样布了血丝。
相对先是无言,等彼此都看清楚了,才发现相思真是折磨人。一夜没睡,两个人面对面,都露出疲惫。
舒马兹杨的蓝眼睛有些黯淡。
那哀愁的眼眸是因为谁?
“理儿,”我们坐在房间地毯上,舒马兹杨对着我垂低的眼眸。“你答应过我,不管我们之间发生什么,你都会坚持下去,不会轻易放弃。”
半夜三更他来就是为了确认这个?煎熬他的折磨我的原来都相同?
“我没有反悔的意思。”其实说谎。我差一点想去维也纳。
“你在意我母亲那些话?”
不在意是自欺欺人。骨子里,我原来有的是世间女子的小心眼和虚荣。
“在意。”但明白承认还是难堪。我究竟还是不超脱。
“你不要放在心上,也不要比较。我母亲千方百计想说服我重回舞台、作曲、演奏,连你也拖下水。”
“其实,我想她真正的用意是要我知难而退。”所以才不惜重提过去。“这一招很厉害,我几乎——不,根本是不断自我怀疑,心眼全变小。”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不怀疑?你希望我那么做吗?”
“你肯吗?”
我没有为难的意思,舒马兹杨苦笑一下。
“诗人写情诗,艺术家为情人作画,音乐家则谱情曲,献给他们的情人。爱情成为他们创作的泉源动力,激发他们的潜能。”他伸手抚摸我的脸,拨开垂挡的发丝。“遇见了你,我的确又有了创作的欲望热情。我真正想为你作一首曲子,只属于你的。可是,我没打算公开发表,也不想重回演奏生涯,你能谅解吗?”
“我可以问为什么吗?”多少人追求梦想的就是这个。如今我会在柏林,为的也是这个。
“累了。成了名又要成为舒马兹家应酬的工具。”舒马兹杨揉了揉太阳穴,靠着床背。“像现在这样的生活平静轻松多了。”
“我很想认同你的话,可是你其实并不喜欢你在做的事。别自欺欺人,看你收的学生就能明白。”
“理儿……”被我说中,舒马兹杨口气承认:“没错,我是不喜欢。但我更不想重回演奏家的生涯,我不想再上舞台,连指挥也不想。”
“那么,你就只剩下作曲了。”
“你真的希望我那么做?”舒马兹杨问得迟疑。大概他自己也在犹豫。
“没有。老实说,我喜欢你演奏时的那神采,亮得教人睁不开眼睛。我曾经看过你的演奏会实况录影,看得非常嫉妒而且自怜,不甘愿的承认我永远也无法达到你的成就。那是一种很受伤的感觉,必须承认自己是那样的庸碌。”
“你是希望我重回舞台?”舒马兹杨的脸黯下来。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觉得有必要解释。“我只是说我喜欢你弹琴时的丰采。你自己的曲子,在由你自己诠释时,特别有股激荡,我喜欢那样的感觉,如此而已。”
“那么,如果我坚决不愿重回舞台,你会不会失望?”
“不想回舞台那就不要回舞台。”舒马兹夫人要是知道我这样鼓动舒马兹杨,大概会恨不得将我分尸。
“你这样说,我好像更有勇气了。”舒马兹杨像是松了一口气。
“你自己心里早早有了决定,别拖我下水。”
虽然觉得可惜,但那是舒马兹杨的决定,我也只能支持他的决定。不过,打死都不能让他知道我这想法。
舒马兹杨略微动一下,稍倾着头,说:“我想了很久,不再重回舞台公开演奏,或许可以接受录音演奏,一边创作乐曲。你说这样好吗?”
“为什么要问我?”
“我想知道你的看法。”
虚荣的我,有种受重视、被放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