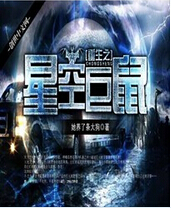在亚洲的星空下-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也请别以为我在利用我的美。我说过,在东方人中,我美得不够纤柔;在一堆高挑修长又丰满且轮廓深刻的白人女子中,我也只落得稀松平常。流着泪哭泣的我,也许有一点让人同情可怜,但肿眼红鼻子,绝不会吸引人的。
况且,王净说过,美丽的女子是应该被宠爱的。至于被同情可怜,也只会被同情可怜,不会被爱。
所以,我哭到力气歇了,也就是力气歇了。
星期日,我练完琴,王净打工回来,我们下了她包的水饺,喝着冷啤酒,一边叫烫一边冻得心口麻凉。
王净看着我“壮观”的吃相,说:“浓情蜜意的时候,连狼吞虎咽都是好看的;一旦不喜欢你以后,这些都成了厌恶的理由。”
“别担心,你一直是很文雅的。”
“你呢?都这么馋相吗?”王净笑。
我也笑。“我只有偶尔才会这么放纵。肚子饿嘛。”在外头,我是有“教养”的。
“有没有想过打工?”
“没有。”母亲大人不会允许。
“想也是。看看你那双手,我看你家事都不太做。”王净拉了我的手,笑咪咪的,没有讽刺的意思。
“那倒是。不过,倒不是因为好命,是我母亲大人的浪漫。”
“怎么说?”
“因为她说钢琴家的手是用来弹琴的,不是用来洗衣拖地煮饭。”
“哈!”王净觉得新鲜,“那你将来嫁人了以后怎么办?”
我眨眨眼,微笑不说话。
我的日子其实过得很省,没能力奢侈。想想,来柏林有些日子了,我连电影都还没看过。我爹的浪漫,给了母亲大人一段风花雪月的好时光;母亲大人有样学样,对我很尽心,我有义务坚持母亲大人的浪漫。
“其实也很简单,叫老公煮饭。”王净自答。
惹得我笑出来。看样子,她应该没事了。
“你有能力,王净。将来成大事业,老公不煮饭,就请人帮你煮饭。”
“那倒是。我偶尔下下水饺调剂一下就是。”王净配合我,说得跟真的一样。她在洪堡大学念商科专业,一口德国话呱呱叫,比我还流利十倍。学成了,大概也会比我出息十倍。
水饺冷了,配着凉啤酒更加冷飕飕。我放下啤酒,不敢再喝。
“欵,理儿,”王净突然问:“你知道现实和梦想的差别吗?”
我一本正经回答:“现实是电影里的风花雪月减去百分之七十,小说里的浪漫折掉三分之二,再将戏剧里的偶然拿走八成七。”
“说得很好。”王净笑咪咪点头。“那前两天在咱们公寓门口上演的那出法国新浪潮电影的男主角,请问是谁?”
“舒马兹杨。”我以为她知道。
“舒马兹杨?他?”知道那是舒马兹杨,王净大大惊讶一番。
“你不是看过他的照片了?”我觉得奇怪。
“是看过。可是还是有差距,而且当时你们两人间的气氛挺凝重的,我也不好插在中间,就避开了。他找你做什么?”
“他说我休息太久。”
就这样,不会劳动舒马兹杨亲自上门。聪明的王净,眼珠子一转就可知必有缘由,但她没追问下去,她懂得给人空间。
“你跟他学习,好像很辛苦?”转了话题。
“有一点。”
“他不好相处吗?”
我没回答。王净自说:“那是一定的。我也是那么听说,乐评家对他的评语也不好。看了他本人,我也觉得他那个人不太好说话。可怜的理儿,一失足成千古恨。”
就好像论学术做研究,各家有各家的理论成见,各自有各自的门阀派别。跟了哪家,再要更换师门,虽然不是说绝对不可,总是犯忌。所以在投师的时候就要想清楚。
乐坛的情形其实也差不多。我投在曼因坦教授门下,教授因为健康缘故将我转介,一般也还会接受;就是当初一接触舒马兹杨,发现不妥,曼因坦教授若火速再将我转介,也许也还来得及补救。但现在,我觉得机会渺茫。
其实,那么多世家子弟争着投在舒马兹杨门下,也不能说他不济。但看看他门下那些学生——舒马兹杨音乐学院里真正有本事的,多半是在奥尔夫那两人门下。
我觉得舒马兹杨就像他们欧陆君主封建时代,陪着那些王侯贵族消磨时间取乐的宫廷乐师。
我会这样想,表示我对舒马兹杨的没信心。偏偏曼因坦教授却对他深信不疑,一点都不受乐评家和舆论的影响。
“可怜我之前,先担心你自己吧。被功课压垮了没有?”日耳曼民族做事一板一眼,实事求是,求学问业是混不来,也马虎不得。
也难怪舒马兹杨要我从头再练起。
“已经驼了一半。”王净叹大气,“想想,念这么辛苦不知要干什么,将来毕业也不过赚那几文钱,不如人家天生命好,衔金汤匙出世的。老天就是不公平,有钱的人生就是传奇,我们这些没钱的,活该是列传。”
“怎么说?”王净口齿伶俐,有时候会说一些很有意思的事,不成理的也成理。
“有钱的人,因为有钱,可以不事生产,可以四海吟游,做尽一切风花雪月的事,飘飘又浪漫。浪漫,这些是传奇的本质。有钱的人也就容易变传奇。没钱的人哪,做得要死不活只为一口饭,说书的叫那是轰轰烈烈。列传是没钱人的奋斗史,失败居多。”
我哈哈大笑,没有悲剧美少女心有所感所触的颦眉愁。
王净嗔我一眼,嗔我的哈哈笑。她觉得我应该微拧眉,坐望窗前,同叹一声愁。
“你打哪学来这理论?”水饺已经被我们扫光。啤酒早就不再冒泡。
王净刚要开口,电话响起来。她腾手去接电话,才“喂”一声,脸色就僵了。
我大概知道是谁了。收了东西避开。
才回到房间,王净就跟进来,赤着脚爬上我的床。床头搁着那瓶香奈儿十九号,她顺手拿着把玩。
“他说他和那个女的分手了,要来找我。”眼睛不看我。
我“哦”一声,拿走她手上的香水,朝空中喷了两下。我不擦香水,拿它来当空气净化器。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王净问。
“到底怎么回事?”我反问。
她停顿一些时候。“我想想。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
她不用告诉我其实我也知道,把我自己的事拿来翻版就可以。
“王净,这种事有一次就有第二次。”我看着地上。
“如果你男朋友回头找你呢?”呵,她也看穿我的狼狈了。
看,同样遭遇的人,身上散发的酸腐味道多么浓。我都没说什么,王净光嗅一嗅就闻出来了。
我想了一下,然后说:“不知道。”
然后王净说:“我也不知道。”
知道才怪吧。
我想起还在海岛时听过的一句广告词:女性主义就是败在衣服和爱情两件事上。
何止是女性主义。亵渎一点,女人都是爱情的附庸。
我母亲大人说的,美丽的女子比较容易过活。我想,不是因为她美丽,而是因为她遇到了一个浪漫而专一的男人。
到头来,女人的幸福还是维系在男人身上,还是得以色事人,以男人的爱来堆彻她幸福的城堡。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推论正不正确。不过,我想,女人的幸福其实不在男人的爱,而在男人的专。
情专必深。情深却不一定专。
我笑起来。为自己的好头脑、逻辑观念这样清楚。
但就像找不到一首完美的协奏曲一样,这个地球也找不到会对情情爱爱专心一致的男人。
他们说这是因为受荷尔蒙影响的缘故。
想着我又想笑了。
我想,还是人性的缘故。是性格,是担当,是承诺的深度。
第七章
女人的眼泪,果然算得上是一项武器。舒马兹杨虽然不会没事冲着我笑,但不亲切的态度已经从“很”度的极数随为常度的极数。
如果他能继续保持这种“人性”的态度,我想我倒不介意伏在他胸膛上多哭几次。不过,“眼泪”这种非常性的武器其实不能多用,只有在非常时候才能使用也才能发挥作用。
不管怎样,这就好像破冰时刻,柏林的低温感觉起来不再那么寒飕飕。
现在舒马兹杨要我改弹汉农的练习曲,曲调不美不说,弹得又教人手指发痛。但我就像时钟嘀答嘀答,把节拍抓得一精二准。
舒马兹杨没浪费口舌称赞,我自己也不觉得得意。以前我弹的音乐,就像泼墨;现在的音符,却像精钟表机械,一板一眼,精良十准。
不过,除了练习曲,舒马兹杨也允许我弹一些技巧难度较低的乐曲。底盘功夫不稳,招式学得再多再精准,也只会流于花稍。舒马兹杨这样“磨”我,我也不能说什么了。
多年前我看过舒马兹杨的演奏实况录影。舒马兹杨的音乐干净清历,不拖泥带水。技巧当然是好的,火候十足,但绝不是精钟机械那样一滴一跳。他的音乐像古中国的诗,声韵齐动,却又不拘泥于平仄,时有破格;在谨守格律的跃动下,充满飞扬的诗意。
就是那种在日耳曼民族一板一眼的精确技巧中,蕴含的古中国流动飞扬,甚至哀美绵缠的诗意,使得他一手遮蔽了欧陆、甚至世界乐坛的半边天。
我不是说,属于古中国的一切一定都是好的。但汉文字,字字有它自己独特的境界意涵,诗词所显的意境绝对是独步的。我读英诗,即使浪漫如雪莱之流,也抵不过一句“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哀美。什么情什么爱都没说,但那浓浓的情感满满从字里行间流泻出来。舒马兹杨的音乐带着如此的诗意,使得他的音乐也是独步的。
只是,那都过去了。他要我弹汉浓,不允许我把钢琴弹得像一幅泼墨。
上完课,我忍不住。“我还要弹练习曲弹到什么时候?”
他藐我一眼。“还早。等你把汉浓的弹熟了再说。”
“我觉得我已经掌握得很好——”
“你‘觉得’没有用,我‘觉得’才算数。”一句话就驳回了我。
我总觉得,他对我有偏见,束缚特多。
“舒马兹杨先生,”我又不知死活,“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你本来就不是亲切的人,但你似乎对我特别有偏见。你不喜欢东方人?”我没说他对我的态度差劲,算是懂得修辞了。
“我有必要喜欢吗?”舒马兹杨来一手反诘。
“我没那么说。不过,如果报导没错,舒马兹杨先生,令尊的母亲应该来自东方。”
舒马兹杨眉梢一挑,一副“那又怎么样”。
我识时务,闭上了嘴巴收拾东西。
舒马兹杨突然问:“当初曼因坦教授为什么会收你?”
“你又欠了教授什么人情?”我不想回答。
没有道理他问什么我就一定要回什么。
“你这是交换?”他沉下脸。
“一问还一问,这很公平。”不知道别的学生是怎么同他相处的。跟舒马兹杨,我总觉得跟敌人对峙差不多,和跟曼因坦教授时完全不一样。我对曼因坦教授充满崇敬;教授像我父亲祖父一样,我是又敬又爱。
不是说我不尊敬舒马兹杨,我没那么势利。虽然他的辉煌已经过去,虽然跟在他门下我心底是有点不情愿,虽然乐评家对他的褒贬不一,批评他江郎才尽;我是愿意接受的,可是他那个人像刺猬一样,我也就无法由衷的,像崇敬曼因坦教授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