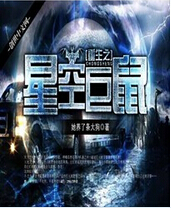在亚洲的星空下-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连补偿都不想要。起身走出去。
真的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坐在舒马兹杨的车子里,就在他身旁。街对面,是昨日杜介廷和我分手的街角。
“你还要跟着来吗?你应该有约会吧?”他没道歉,我也不道谢。
“约会是晚上才约的。现在这时候,是应酬。”舒马兹杨没让我的刻薄占便宜。
我意识到我受了伤的手。吓!他弄伤了我的手,所以当一趟免费司机应我的酬。
我一点都不会领情。
推门进咖啡馆。我也没有把握杜介廷和章芷蕙会不会在里头。
我想和杜介廷再谈谈。只要他肯跟我谈,也许能挽回什么。
我要了一杯咖啡。有人跟在我之后进来。是舒马兹杨。
他走向吧台。
许多人认出他,引起了一阵小骚动。舒马兹杨在乐坛的浪头就算已淘过,余波仍然在荡漾。尤其当时,是他自己嘎然主动斩断一切,原因不明,就变了传说。
一杯咖啡我喝了半小时,没让我白等,第二个半小时,杜介廷拥着章芷蕙推门进来。
看见我,杜介廷楞了一下,走了过来。章芷蕙跟着过来,看仇人一样看着我。
“理儿……”杜介廷的声音听起来倒有几分过意不去。
“你想怎么样?”章芷蕙目光发狠,不退让又理直气壮。
谈起恋爱,好似女人总是比较奋不顾身,比较张牙舞爪。
我看看杜介廷。什么都不必再谈了。
母亲大人在维也纳浪漫地邂逅我爹,我到底没有我母亲大人的运气。
剩下半杯的咖啡我没喝完。我不要了。
结果跟杜介廷一句话也没说到,我哑了口,推门出去。
舒马兹杨跟着出来,我也不吃惊。我想他有点闲。
我没有哭。伤心是有一点,难过也有许多,偏偏眼泪就是挤不出来。根据一些心理学的理论,如果我能嚎啕大哭,对身体或许比较好,对情绪也有帮助,或者闷在心口,抑郁成疾,也许会得内伤。
我没说过,我不太喜欢弗洛依德或容格心理分析那一套。日耳曼是个太实事求是的民族,不怎么讨人喜欢。
“喂——”舒马兹杨抓住我。他不是一个亲切的人,但连他也以为我大概迎风在掉泪。
“干嘛?”我皱眉。干干燥燥的眼眶和脸庞倒教他意外。
他示意我跟着他。上了车,我说:“你不去约会吗?时间不早了,下回去准备来不及。”
他点了根烟,吸了一口,看我一眼。“如果你想哭,我不会介意。”
这个人以为他是什么?神父?等我告解?
“是不是你还要慷慨的借出你的胸膛,让我俯在上头哭?”我讽刺。我不怕他了。没所求就不怕了。
“如果你需要的话。”
舒马兹杨一本正经,却教我恨了。
他全看到了。聪明的他以此类推,大概全部都了然。
“情绪渲泄出来会比较好。这里没有别人——”
“你就是别人。”我打断他。
“你可以当我不存在。”
我不想说话了。撇开脸。
“刘理儿,你这样对你自己没有好处——”
“你一定要我哭吗?!”
“我看你压抑得很辛苦。既然那么在意,就不必装得毫不在乎——”
“别说得你什么都知道似!你自己呢?比我好不到哪里去!”我对他大吼。“别人苦不得有机会站上舞台,你偏要装模作样拒绝慕尼黑国家剧院的邀请和玛琳夫人的赞助。你想表示什么?不屑吗?你舒马兹杨是天才没错——但你的辉煌过去了,江郎才尽罢了!”说到最后口不择言。
哦,我不是有个性,我只是恼羞成怒。
“你——”舒马兹杨的蓝眼珠窄起来,脸色铁青得吓人。
他扬起手臂。我以为他会打我,但没有。他忽然发动车子,没有示警,一下子就飞冲出去。我的胸膛狠狠撞了车座前缘,又弹了回去。
车子疯了。超过速限,疯狂地四处飞撞。下过雪,路滑,很容易失控。
“舒马兹杨……”我受不住。全身被撞得发痛。
他没理我,继续横冲直撞。突然,车子拐进一条小巷子里,煞车不及地冲撞上一堆摆放整齐的垃圾桶。
我下意识闭上眼睛,身体侧弓,紧紧抓住椅背。
直到天地都安静了,舒马兹杨冷冰冰的赶我下车。
“出去。”他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眼神是狠的。
“冰天雪地的,你要我自己走回去?”我全身都在痛。
“那不关我的事。”舒马兹杨身上流的血不是温的。
“可是关我的事!”我叫起来。我连身处在哪里都不知道。“你至少要送我到最近的地铁站。”
“我没那个义务。”
“你有!”
“笑话!凭什么?”舒马兹杨居然冷笑起来。
我压下气。“是你将我带到这里的,就有义务将我带回去。”
“我可没有绑住你手脚押你过来。”
“舒马兹杨,你绅士一点。”我瞪着他,一点都不怀疑他会将我丢在零下一度的雪天里。
“我本来就不是绅士。出去!”他的语气更冷。
我不动,和他冷刺的目光僵持着。
“你不出去是不是?好!”他打开车门,丢下我,头也不回就那么走掉。
“舒马兹杨!”我早知道会这样。一定会被他丢下的。
车子陪着我也无济于事,我不会开车。
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心情太恶劣的缘故,我不想跟任何人类说话。折腾到了快晚上十点,终于才到家。
又冷又累的关系,我抑不住的颤抖。胸前锁骨下青了一块,手臂也有多处瘀伤,就连胸侧也青紫一片。
我呆呆望着,手脚冰冷。怀念离开已久那亚热带的岛屿、太平洋湛蓝的海。太平洋连到地中海,我就又看到舒马兹杨地中海蓝的冰冷眼眸。
第六章
右手背的伤让我休息了一个礼拜。我已经不愿去想后果,做了只把头埋在沙坑的鸵鸟。
我打电话给曼因坦教授。只是问候,打扰他的清修。
“是不是有什么事?”教授毕竟活得久、看得多,一半成了精。
“没有。”我忙不迭否认,却又画蛇添足的加一句:“呃,教授,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将我介绍给舒马兹杨先生?”
曼因坦教授呵呵笑两声,笑声一副“来了”的架势。
“他对你不好吗?”问得匪夷所思。
我以为曼因坦教授应该问的是“学习习不习惯”、“跟得上步调吗”、“练习得如何”等等什么都好,而不是这一句“好不好”。
这扯上私人的关系感,不纯粹。
“我特别拜托他照顾你的。”教授又说。
我想不出话,又问一句。“教授,我……呃,你觉得我有那个素质吗?我——”
曼因坦教授哈哈大笑起来,之宏亮,没人会相信他身体欠安需要安静休养。
“怎么了?理儿。怎么突然怀疑起自己?”
不是突然,是一直。我没信心。
“教授,请你老实告诉我,我的资质如何?你后悔过收我吗?”
曼因坦教授又笑。“你也是这么跟阿萨斯说的吗?理儿,难怪他跟我抱怨我丢了一个麻烦给他。”
“他联络过你了?”我心一惊。
“你别担心。”曼因坦教授没有直接回答。“阿萨斯的脾气就是那样。好好跟着他,他会引导你的。”
说来说去,我关心疑惑的,曼因坦教授还是没有给我答案。我没跟他说舒马兹杨把我的手弄伤,我已经休息了好几天了。
不管如何,电话是两天前的事了。我甚至打电话给我母亲大人,试探回去的可能性。母亲大人疑了心。
“发生了什么事?”她的第六感永远比其它五感强。我们家的女人,是用“感觉”过活的。
“没有。我只是……”我吞吐一会,“妈,你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的资质吗?你真的认为我有那种才华吗?”
“你在说什么啊?理儿。怎么突然问这种丧气话。你是爸跟妈的女儿,当然有那个才华。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可是……”这就是我的母亲大人。我有说过她也很浪漫吗?倾家荡产的送我到欧罗巴,相信她的女儿是一颗不世出的明珠。我却觉得自己只是一粒裹了沙的蚌珠。“妈,如果……我只是说如果,如果我放弃这里的学业,回去的话——”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老实告诉我,理儿。你实在不太对劲。”
“没事,你别担心。我只是想,要花那么多钱,如果我回去把剩下的学分修完,可以教教小朋友钢琴,或到外头钢琴教室兼课,那样的生活也是很好——”
“你不用担心钱的事。”母亲大人说:“你真的不对劲,理儿,说这种泄气的话!”
可是,母亲大人可能没有想过,能站上舞台,被聚光灯投照的到底没几个。最后,很可能——而这个“可能”将近百分之百,我也只能如其他千千百百的人一样平凡无显的过这一生,像舒马兹杨说的,捞个教职,教教DoReMiFa,就是这辈子最大的成就。
“你别再胡思乱想。钱够不够?过两天我会汇钱给你。”
母亲大人在维也纳度过她美丽的青春。可是,柏林不只有风花雪月而已。
马克又升值了。多吃一只鸡蛋,我都觉得像在吃新台币。
看,我是这么的不浪漫。母亲大人说美丽的女于容易过活,因为她们不管柴米油盐吧。买瓶牛奶,我都要算一下汇率。我很惶恐又抱歉的戳破那些对美丽女子的幻想。不过,我说过,在一大堆高鼻深眼窝的白人女子中,我的美也只落个平凡无奇,而且我还缺乏东方女子特有的婉约。那才是西方人认为的东方美,东方男于爱的纤柔美。
我有太多的自我怀疑,一切都不到位。要不,杜介廷选了章芷蕙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把窗打开。扑进来的冷气冰得能让人心脏麻痹。柏林的冷,是很切确的。
“别这样开暖气又开窗的,费电。”王净进了门,“啪”地一下就把窗子关起来。
“今天怎么这么早?”我看看时问,才七点,她在餐馆打工,一星期有一半要晚归的。
情人节的隔天,她从法兰克福回来,圆润的一个人变成了一个骷髅架,以前水灵灵的眼睛则成了两个大黑洞,表情是死了。我看她那样,不必问也知道怎么回事。
那一天半夜,她伏在我肩膀哭泣,一直问为什么。
从上海到黑龙江,距离那么远,感情都没有死,怎么到了异乡,柏林到法兰克福也不过几个小时的车程,距离拉近了,两情反而夭折了。
其实不必太痴。要不然眼睛哭肿,实在很麻烦。
王净哭了三天,然后就到餐馆上工了。课业那么重,她要伤心也没时间。她不要我安慰或同情。她说,美丽的女子应该是被宠爱的,而不是用来安慰或同情。
我有说过吗?王净长得甜美,和章芷蕙的婉约古典不一样。对美丽的女子来说,同情她就像“嗟来食”,忍无可忍。
我笑。果然生物还是有很强的自愈本能。我不想杜介廷,结果,也是活得好好的。
就是这样。我们两个都存活了下来。
只不过,我的右手背多了一道浅浅的疤。有点丑。它实在是碍眼。看到了它,我就想起舒马兹杨。想起恶魔给人的印记。
我知道我简直胡思又乱想。我也为自己这种乱七八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