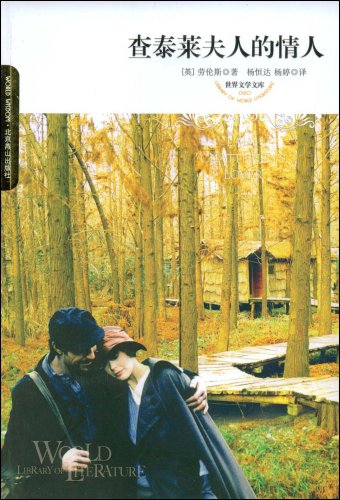��̫�����˵�����-��41��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Ϲ����ĸ����ˡ��е�ֻ�Ǻ���Ů�ӡ������������ǰ��ˣ�����ȴ�е���һ���ࡣ��
�������أ��������ô�������ʵ���
���ǵģ�����������������ʱ���Ҳ�������������ʱ���ұ��������������ȥ������
��Ϊʲô�����������أ���
��Ϊʲô������Ц����������ȥ�Բ��أ����ӣ���
�������Ů�ӵľ��飬�ƺ����̫���ˡ�����˵��
��������Ϊ�Ҳ������۵�Ե�ʣ�����һ���ϣ�����������ȴ�����������Dz���һ��̬�ȣ�������ƭ�����أ��Ҿ��������ۣ���֪����������һ��Ů�ӵ���ʲô�����û�еõ����Ҿ�����˵�ҵõ��ˡ���
�����������ڵõ���ô����
�����ǵõ��ˡ���
����ô��Ϊʲô��������������
������̫���ˣ�����Ҳ��Ϊ�����Լ�����
����Ĭ�����ţ�ҹ�������ˡ�
���������Ů֮������Ҫ��ô�������ʵ���
�����ҡ�������Ҫ�ģ����ң�������ܹ���һ��Ů�ӷ����ʵ��Ĺ�ϵ������������������Ҫ���¡���
�������㲻���أ�
����ô�ұ�ֻ��û�С���
����˼��һ�£�Ȼ���ʵ���
����������һ��Դ�Ů��û�й�����ĵط�ô����
����Ӵ�������ҵ�Ů��Ū���Dz���أ�������ҵĴ�������ʹ���仵�ģ����Ǹ��ܺ��ɵ��ˣ��㽫��������õģ�Ҫ�Ҷ�˭�������������Ǽ����£��Ҳ�����Լ�Ҳ�Ǹ�����ʧ�����ˣ��Һ����š�����������ȴ�Dz��������ϵġ���
����������
������Ѫ�����ڵ�ʱ���㲻�����������ɡ�����˵������ʱ�㲻���ɰɣ��Dz��ǣ���
�������ǵģ��ҵ�һ�з��վ������������ģ���Ҳ�����ҵ���������˺��ɵ�Ե�ʡ���
��������ĺ���ȥ�ɣ�����ʲôҪ������
������������ϯ��̾������¯�����¯���ţ�����������
��������һ�Ա�����˵�սʿ��������˵��
����Ҳ�������ô������Ц��˵����������������ǰ����սȥ�ˣ���
���ǵģ�������ʱ�¡���
������
��վ�������ѿ��ݵ�Ь��ȥ��ɣ������Լ��IJ���һ����Ҳ�ŵ����ȥ���������������ӵ���ȥ�����Dz����ˣ������Ż𣬰�ֽ�ҽ�����ȥ���������ջ��˶����ࡣ����˵������������һЩ��֦���ڻ���ϣ�Ԥ�������յģ�Ȼ�������˹�����ȥ��һ�ᡣ
��������ʱ������˵��
����ҲҪ��ȥһ�������
�����Եĵ��ڰ������ȥ�����Ǹ�����֮ҹ����ҹ��������Ż��㣬���������µİ�����ʪ�ˣ��������������߿���һֱ���߿���Զ��������Զ����һ�е��ˡ�
��������ġ���ս���Żص�����ȥ���������ڰ�Ϩ�˵�¯����ǰ��
���ǣ���ѽ������ս���š�������Щ��֦����ȥȡ��Щ��֦��ֱ��һ¯���������ܵĻ��棬��������������Ծ�ŷ����ŵĻ��棬ʹ�������������������ů�����ǵ��������ǵ���ꡣ
��������Ĭ�ء���Զ�����ţ��������������֣�����Ҫ�һ����ֻ�þ�����ȥ����
���ǵģ�����̾�˿�������Ц�š�
�������������������������
���������ɣ�����ϸ��˵�����������գ���
�ڻ�ı����Ġk���У����������������汾������һ�����ǡ������������ĵġ�� k�ġ�����������������أ�����Ѫ��ת���ˡ���ʼ�������������������������ˡ�
��Ҳ����ЩŮ�����ĵ����������㣬���Һúõذ���ģ���������Ҳ�����ܡ�Ҳ���Dz�ȫ�����ǵĹ�ʧ�ա�����˵��
����֪�������Լ�������һ��������Ķ��˼��ǵ��ߣ�����Ϊ�Ҳ�֪��ô����
��ͻȻ����������������������Ը��������һ���ˣ�����һ�ֶ��������ͷ����������
�����������ڲ��������ˡ�����˵��������Ҳ����һ�ֱ�����Ķ��˼��ǵ����ˡ���
���Ҳ�֪��������������ǰͷ���кڰ����������
����������������������˵����Ϊʲô��Ϊʲô����
�����ǵ�һ�У�����ÿ���ˣ������кڰ������������������á���Ԥ�Լҵ�������������˵����
��������Ҫ˵���ֻ�����
����Ĭ�ţ����������Ծ�������������һ��ʧ���ĺڶ��ڡ�һ����������һ�а��������Ƕ����ˣ����ǵ��������ʧ���������������ʧ���ĺڽ��С�
������ô����˵����������˵����������˵�����·���ֻ������˵Ŀ��֣�������˵������Ƶġ���
���˷ܵ������������ˡ�
����������˵���������һ��Ů������õ��ҵĿ��ֺ����㣬��һ��ȴ��δ�õ�����Ϊ�Ҿ����ܵõ��ҵĿ��ֺ����㣬������ͬʱ��������õ����ġ����Ǵ���û��ʵ�ֹ����£�����Ҫ������еġ���
��������ʹ���û�����ι������е�Ů�ˣ�ʵ������������Ҳ�����εġ�����˵��
���Ҳ�������Ů����ʲô��˼����
�����ƣ����������������
������������ϥ������š�������������Ʈ���ģ����ڵģ���������������ʱ������˵�Ļ���ֻ�ǰ������ø�Զ��
���Ͼ�������ʲô�����������˵��
���Ҳ�֪������
��ʲôҲ���š���������ʶ������һ��������˵��
���dz�Ĭ�ˡ�Ȼ�����˷�����˵��
���ǵģ������ŵ�ʲô�����ġ�������Ҫ��� k���ġ������ż������������Խ���ʱ����� k���ģ�Ů������� k����ȥ���ܡ�һ��ȫ���ˡ�������������̸���Խ���������ζ������Ϸ����
�������㲻������غ����Խ��գ�����˵��
��������һ�������������Խ����˿��ҵ�����������䷬���Ƶġ���
��ѽ��������������Ц��̸��˵�������������䷬������һ�˰ա���
��Ц����������ֱ������˵��
��������ģ�һ�ж�Ҫ�е�� k���Ķ�������Ů����ȴ��ϲ����������Ҳ������ϲ������ϲ������ġ����ҵġ�����ġ�������̸�������Խ���Ȼ����ȴ˵����������Ƶġ����Ķ���ʲô���ҵ����飿����Һ��ɵ���һֻè��һֻ���Ƶġ��Ҹ����㣺��ʹ����� k���ĺ����飬Ҳ����������С��㰮�Խ������Dz����Ե��ˡ�������ȴ�������������ϸ�ʲô������������ã�ȥ������������ġ����㿴������������ģ��DZ������Ǹ����ڣ��DZ���Ů��ϵ����Ҫ�ġ���
������ǡǡ������Ҫ����ĵط�������������Ǵ���һ�еġ���
����ô���ðգ���Ҫ��̸�ˣ�����˵�š���վ�������������Ǹ������ذա�����Ը��������Ը�ٸ�����������Խ��ˡ���
���뿪��������վ��������
������Ϊ����Ը��ô������˵��
����ϣ����Ҳ��Ը������������������������㵽¥��ȥ˯�գ��Ҿ�����¥��˯���ˡ���
�������������Dzģ���ü�����ţ�������һ���Զ�������������Ƕ���һ���ġ�
��û�е��糿�Ҳ��ܻ�ȥ������˵��
��������¥��˯ȥ��������һ���һ���ˡ���
���Ҳ�֧����һ����ȥ������˵��
���߹�ȥ��������Ь���ã���Ҫ��ȥ������˵��
����ʼ�ڴ�Ь������������������
����һ�ȣ�����֧����˵������һ�ȣ����Ǿ�����ô�ˣ���
������ϵ������Ь����û�лش�ʱ����ţ����ݾ���һ��ڣ���Ҫ��ѣ�ˣ�������ʶȫʧ�ˣ���������վ���Ƕ���Բ�����۾���������һ��֪����ʧ�ˡ�
���־���ʹ��̧��ͷ����������Բ�����۾�����ʧ�ŵ����ӣ�����һ��������������������ڻ��������ӵ�ţ�������ȫ������ʹ�������������������������š�
������äĿ��̽��������ֱ��̽����������������������ů�ĵط���
���ҵ�С�˶���������������˵�����ҵ�С���Һͣ����Dz������գ�����������Ҫ�����գ��Ұ������Ұ����������������ִ�������������������Ǻͺ���һ����ա���
��̧ͷ��������
����Ҫ���ơ��������˵����������û���õġ��������������һ���ô����
����������۾���������������ͣס�֣�ͻȻ�ؾ�Ĭ���������ر��š������������岢û�бܿ���
Ȼ�����ع�ͷ���������������ţ����ϴ������ǹŹֵķ�����Ŀ�Ц˵�����ǵģ������Ǻͺ���һ������IJ���֣���
�������ô������˵�����۳��������ᡣ
���ǵģ���ģ��ĺ������߶�������һ�������
��һ����������һ��Ц�ţ�������һ�ַ��̵ľ��⣬������һ�ֿ�ζ��
�������ؿ����ţ�����¯��ǰ�ĵ�ձ�ϣ�����������ȥ�����ҽ����������棬�������Dzŵõ��˼��ְ�����Ȼ������Ѹ����¥���ޣ���Ϊҹ�������غ��������ˡ��������Ƕ�������Ū��ƣ�����ˡ���С����Ƶ��������Ļ������������˯�����������ͬ���˯������������ǰ�˯�ţ�ֱ��̫�������ң�ֱ�����տ�ʼ��ʱ��
Ȼ�������ˣ������չ⣬���Ŵ����Ĵ��⣬ɽ��ѻ�ͻ�ü�ڴ�����У��ⶨ���Ǹ����ʵ��糿��ԼĪ�����ˣ�������ƽ����ʱ����ҹ��˯�ö��죻���Ƕ�ô���ʵ����ӣ�Ů�˻�������ء������˯�š������ָ������������������������־�����۾������ʵ�����Ц�š�
��������ô������˵��
���������������ţ���Ц����������ͻȻ�أ�������������������
���벻���Ҿ�������أ�����˵��
�����Ƿ۰�С�����������ţ��컨������б�ģ��ݽǵĴ������������ţ�������տյأ�ֻ��һ����ɫ���¹�һ�����Ӻ����źñ���˯�ŵ�С�״���
���벻�����Ǿ�������أ�����һ��˵��һ�߸����������������Ƕ������������������ı�����˯���£����������ā�������������� k�غ���ŵ�ʱ�����Ե��������ò�������۾�������ô��ů�����أ������������������һ֦��һ����
����Ҫ���������ˣ�����һ��˵��һ�����������ı�����ϸ���˯�¡�����ͷ�������������������Ƕ�����¶�����硣����ֻ�е㴹��������ɫ�ā�������ϲ�������ā���������Ƶ�����ҡ�š�
����Ҳ�ð�����¿����ˡ�����˵��
���ǣ�������
��Ҫ��Ҫ�������������
�������ľɶ̹����ˣ��ѳ���������ȥ������������������;����⣬����һ��һ��İף����������ķ��������۶��н�ڵġ���Ȼ�أ��������¾������Ĵ��˵��������������������ϴ����ʱ��һ����������ɹ�ڰ�ɫ�Ĵ����ϣ�������̫�����������
���ǣ������ǰѴ����գ������������ˣ�������̫�������գ�����˵��
�����´�ȥ�������ſ��ݣ������أ��ְ����ݣ�������ʱǰ�㣬�������ߣ����Ѵ��������ˣ����������һ�ᣬ���ı��ǰ��۵�ɫ�ģ������ģ�ȴ���������ġ�
������ϸ����������������һ�����ڵģ��������ڵ�������
��������Ӵ������˵������ô�����������գ������������ۡ�
��������˼������ת��ȥ����Ϊ���ij������������˷��š�
���ڵ���ʰ�������ij��£�������ǰ���������˹�ȥ��
����������˵��������������ϸ������������ͦ����ֻ���ā����������ҿ����㣡��
���ó�������ȥ��ľ������������������Ӱ������˽������������Ĵ��ˣ�����С��С�����Ͱ�ͦ�ġ�����ʿ������һС����ɫ�ķ�����ë���У����ű��£�� k�k�ؾ��������������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