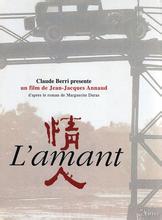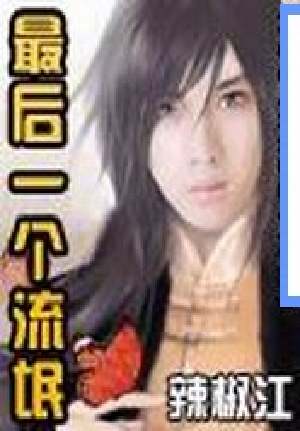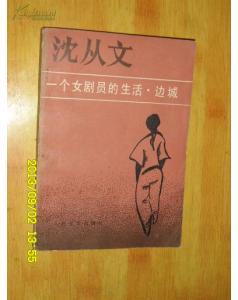一个陌生男子的来信-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由黎湘南的反应来看,她的感觉自是鄙夷多过羨慕,也排拒了好奇。高日安了解地宽宥她。尽管她有时会说出二十七岁女人的老练世故,但其实她还是一个尚未成熟的小女孩。还有受她父母离婚的影响,也让她看待事物多有讽刺挑剔的偏颇态度。
因此,听见黎湘南这些尖酸刻薄的讽语,高日安并没有情绪上的波动。他思及她的家庭狀況,直觉认为她应该不是专为舒睛而语出讽刺。果然,黎湘南按着又说:
“像我爸,貪的一直就是我妈的美貌;等地年老色衰,他得天天面对鸡皮黄脸婆,实在看不下去,就随便找个什么个性不合的理由搪塞,离婚了事。我看过他那个后妻,的确年轻又美丽,还真与你那个后现代精制品有异曲同工之妙。男人就是这点贱,标准的感官动物!”
高日安并不惊讶黎湘南会说这种鄙劣意识这么强的话,虽想引正她的偏颇观点,但她难得说这么多话,还主动提起她父母和家里的事,因此只是静静地听,并不打岔。
“至于我妈,”黎湘南继续说道:“她也算挺有骨气的。我爸像丟垃圾一样甩掉她,地也不吭声,反正她有事业可倚靠,也可以再找第二春。女人如果有钱有地位有成就,男人就会像蜜一样黏过来。她跟我说了一大堆废话,总之她恍然大悟,她也要学学那些货腰女郎的烟视媚行狀──当然,没有那么糟,我只是打比方。”
“她跟我说,她重新再自修,懂得修饰自己,肯定自我,看男人的眼光逐渐在改变,了解到如何和男人相处成为朋友。我不知道她说这些话时,安慰自己的成份有多少。她就是不服输。但是再怎么坚强的人,一旦遭受否定,难免会自暴自弃自寻墮落。你就没看到她在酒吧、餐厅中找男人的那种惨狀。她也是年轻美丽过;向来养尊处优的女人,我不懂,她怎么会不顾羞耻到那种地步 !”
“可是我一点也不同情她。”黎湘南说到这里,甩了一下头发,背脊渐渐放松,靠在沙发上。“她没有认清我爸那种男人的本质,只贪图他的多情温柔,那是她瞎了眼。他们离婚时,她一个子儿也没跟我爸拿。她说她不要我爸的施捨,那是最起码的尊严。她还说那是她的自尊骄傲,但我却认为那叫笨。我跟她说她应该跟我爸拿一大笔赡养费,然后用那些钱去养一个小白脸。”
“她不肯听我的,我就找我爸要了那笔赡养费。我爸倒是很大方,不过我想他一定不曾让他后妻知道。现在我跟我妈住在一起;我爸一直叫我去他那里。我妈怕他将我拐走,成天到晚担心。他们两是管不住我的,什么监护权,只是狗屎,那是法律上的事;不过,我是他们的女儿,当然会一直跟着他们,尽管他们离婚了。”
“我爸当然知道这点,他知道我并没有比较偏向那一个,他一直渴望我搬去跟他住;但你知道,我不能去下我妈。我妈是个徹底的失败者,我即使不同情地也必须陪着她。可笑的是我爸那个后妻;我还没有踏进我爸家那个门,她就紧张兮兮,怕我抢走我爸对她的爱。难怪她担心。我爸很爱我,因为我是这世上和他唯一有血缘的人,我的身上流有一半和他相同的血,甚至是相同的温度。”
黎湘南说到这里,已躺在沙发上,闭着眼,像是躺在棺材里一样的安静。她轻轻启齿,说得很慢:
“从小我爸就是钟爱我,甚至超越了我妈。我记得我小时,我妈还为此跟我爸吵架,骂他不正常。不管怎样,我爸爱我宠我是不争的事实。以前还住在一起时,他回家一定先抱我亲我,然后再亲我妈。很多人都以为我爸对我的爱是不正常、乱伦的感情;只有我知道,他爱我,其实只是他自恋的缩影,因为他最爱他自己,而我体內拥有一半的‘他’。”
“他那个后妻也了解我爸对我超乎寻常的爱,对我非常惊恐,深怕我分了她好不容易才到手的财富是的,她担心的就是这个。她一心以为只要她为我爸生个孩子,我爸就会将他对我的宠爱转移到她和她孩子的身上。那个白痴!她不知道我爸除了我,根本不可能有其它的孩子。他精液里精虫的数目和活动力异常的低,我是亿万分中的奇迹;除此之外,我酷似我爸,也不是轻易制造得出的偶然。那个女人就是想不透。美丽的女人通常都没有大脑,蠢得要命!我爸对她大概也厌了,没事就叫我去找他,撇下她带我去吃饭看电影到处逛。我当然更不可能同情她,一个连自己结婚对象都认识不清的人,除了蠢,还能说什么?她贪的就是他的钱。”
黎湘南说到此就住口不再说话。她闭着眼,均勻的呼吸,像是睡了过去。
高日安注视着她像睡着的容颜,一边仔细思考着她刚刚说的那些话。那些话怎么听,都不该也不像是会由一个十七岁少女口中说出;但他一站也不惊讶,好似早料到她会用这种揶揄讽刺的态度表达她的想法。她的措辞多少也反映了这种心态。
父母离异的小孩多半敏感、多疑,对周遭一切充满不安和不信任。有些內向寡言的人就有封闭自己、忧郁的倾向;有些则躁郁不安,神经兮兮的,彷彿举止都失常了:当然也有以逃家、旷学等所谓“叛逆”的行为表达不满或报复的。而黎湘南究竟类属那一种,就费人思量了。
她用的那些字眼,像是“养小白脸”、“货腰女郎”、“烟视媚行”、“找男人”、“白痴”、“蠢”,甚至“精液”、“精虫”、“乱伦”等,都充满了强烈的骇俗性,可是她却说得那么不在乎。最让人惊讶的是她整个思维方式,那种成熟度,真令人怀疑她其实只是个十七岁的女孩。
他怀疑她为什么突然告诉他这些。他坚信她不会没有目的地让他了解这么多;不过,她既然说了这么多,他就会试着想挖掘更多。
“湘南,”他声音很低沉,相当有催眠的效果。“照你这么说,你很能理解你父母离婚的原因,也能体谅他们,那么你为什么曾在此后突然失踪?”
“谁说我失踪了?”黎湘南突然睁开眼睛坐了起来。
“不是吗?或许我该说,你离开家一段时间。为什么?”
“呵呵,狐狸尾巴露出来了!”黎湘南双手枕在脑后,瞟一瞟高日安,呵呵笑起来。“高日安,我爸妈要我来这里,要你盘问的,就是这个吧?我不会告诉你的。你不是心理学专家吗?那你自己去猜啊!”
“你总得先给我个提示吧?”高日安笑笑的,并未被黎湘南的态度激怒。他知道她有意挑他生气,但他不会上当。
“专家也要人提示?”黎湘南声音冷冷的,眼光如冰。“你犯不着那么尽忠职守。他们在找上你之前早就找过好几个专治精神病的,都比你有名气。你把我推开,他们顶多再将我塞给一个精神医师,不会对你有任何微词。不过,老实告诉你,摆脱你我会很高兴,你比那些呆子难应付多了。”
“是吗?那可真是我的榮幸。”高日安答得啼笑皆非;不过他当然不会让黎湘南知道他这种感受。
黎湘南冷笑一声,突然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告诉你这么多吗?”
“正想洗耳恭听。”
“下星期我就不会再来了,从此我们不会再见面;为了报答你这两个月来的辛劳,索性就告诉你一些满足你。”黎湘南重新躺回沙发,双腿跷得高高的。“你比那些人还讨厌。那些呆子的心里拿我当神经病看,至少眼神会洩露出那种观感;但你不是,你故意不用研究的眼光看我,还裝得很了解我似的。你比他们更狡猾。你跟那些呆子都是一样的,偷窥别人的心理,然后告诉对方他是不是一个疯子。”
“这就是你对我的观感?”高日安冷静地说:“很有趣。不过,你不觉得我们两也差不多?在我试着想了解你的同时,你也在暗地研究我。”
“你错了,我不研究任何人,那是你们这种人才会做的事。”黎湘南猛然翻身站起来。“我要离开了,以后我们没有再见的必要。”
“等等,我要跟你父母谈谈。”高日安边说边拿起电话。
“你谈破嘴也是一样的。”黎湘南悠闲地倚在门边说:“我爸想要我见他就必须答应我这个条件;我妈如果不希望我离开她也得答应这个条件。不过你放心,他们会寄给你一张丰厚的支票,不曾让你失望的。你慢慢和他们谈吧,我先走了!”
大门轻轻喀一声,开了又关,黎湘南的身影随着声响消逝在门外。高日安那通电话迟迟没有打通。他放下电话,朝窗外瞄一眼,耸耸肩,抓起椅子上的外衣,边穿边走出办公室。
第二章
电脑终端机一直吵杂地哔哔叫响,列印出一长捲整齐的资料。乔志高随便将资料摆在桌上,专心在窗边摆着的高倍率大口径的单筒望远镜上。他湊眼,正对面大廈舞蹈学苑热力四射的女郎,个个对他拋送媚眼,齐跳大腿舞。
他仔细搜索,看到那个身材惹火的舞蹈老师。知道她叫舒晴,先前一直是教社交舞的,最近才又兼教有氧舞蹈,而且是隔邻大廈一个心理学家或医生什么的未婚妻。舒睛的确是个妖冶艳丽的女郎,不过她不是他的对象,他对舒晴那种类型的女人早倒尽胃口,他看上的是那个叫黎湘南的女孩。
黎湘南──那是她亲口告诉他的名字。上次他算好她下课离开大廈的时间,事先等在那里,假裝匆忙地撞到她,藉故和她攀谈起来。
他早就认识她了;透过这架高倍的望远镜,早将她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攝入脑中。她看来清纯可人,毫无心机,和他在店里常见的那些庸脂俗粉相差甚巨。来店里的那些女人个个像廉价粗俗的人造花,没有生命力;但黎湘南完全不一样,她是朵清新冷艳的蓝玫瑰。说她艳,是强调她神秘的气质,和舒睛那种俗丽的野艳完全不同。
但今天他从早守到晚,一直没看见黎湘南的身影。他查过她的时间,她今天该来上舞蹈课的。
“怎么回事?”乔志高喃喃自语。时间不早了,他该准备到店里去了。
他匆匆离开大廈,跳上他那辆颜色红得像火似的“火鸟”,这是一位常来店里的女客,在包下他一个月以后所付给他的“小费”。
他是他们店里最红的小生。他的架式像电影明星,是店里最英俊、最酷、体格最棒──甚至技巧最好的一个。来店里的女人都喜欢找他,他对她们耍酷,但不挑剔。
她们简直为他疯狂!乔志高忍不住吹了一声口哨,方向盘一旋,大弧度滑过一个转弯道。
但是他恨那些女人,恨那些下贱的人种。
他上班的店有个绮丽的名字叫“织女的爱”。织女是只有在大阳下山后才见得到情人的,而且一年只有一次,在午夜时藉着喜鵲搭起的桥会见牛郎,像在偷情一样,所以他们的店大阳下山以后才会开;午夜是偷情的最高潮,太阳升起以后,门就闭得紧紧的了。他是活在夜里的男人,所以只能以牛郎的方式,隔着星河,偷偷望着活在阳光下的黎湘南。
黎湘南是一个纯洁的化身,相对于他所属的黑夜,她显得充满光明。他不敢对她说他对她的爱慕,牢记着人鱼的传说,怕一对她开口出了声,最后他会变成了泡沫。
上次见面,他对她自称是落拓的作家。想像他是那种满怀文学理想,怀才不遇,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