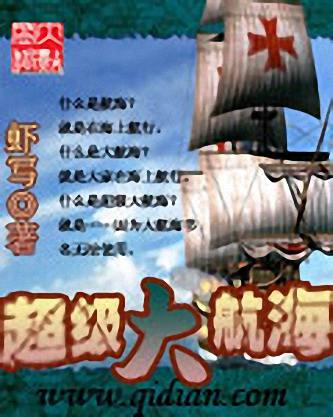大航海时代-正-第4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如跟我去北方吧,穿越草原和沙漠,说不定会发现你要找的石城还是什么城的呢!”
众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调侃着年轻人。他们倒也不是故意取笑沙里裘,只是现在的生活已经这么辛苦了,若再不找点事开开玩笑的话,谁还能熬得下去呢!
坐在拉斐尔身边的码头小伙子小声说道:“这个沙里裘就喜欢找那些传说中的东西。自称是寻宝人。美人鱼啊,独角兽啊,吸血鬼啊,幽灵船什么的最感兴趣了。前段时间找到一块石板说是什么霸者之证,现在又说要去沙漠中找二千多前的石城。非洲这一带根本就没有一块石头啊!”
刚一提到霸者之证,就有人问道:“沙里裘,上次那个什么霸者之证的,究竟卖了多少钱啊?”
又一个人说道:“你就别再提了。埃斯皮诺沙肯出五万买那块破石板已经是天大的运气了,他居然还不卖。结果被打得浑身是血,东西给抢走了,还一分钱没得到……”
“啪”得一声响,沙里裘放下手中空了的杯子,一声不响地低着头走出了酒馆。酒馆里一下子静了下来,没人在开口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满脸胡子的中年人才说道:“其实,我倒真的很希望沙里裘能找到霸者之证上说的那个宝藏。如果有了钱,就可以离开这里去过好日子了。”
“是啊。美人鱼也好,什么也好,如果那些东西真的有的话,我一定跟他一块儿去找。”先前让年轻人跟自己出海的男人说道。
“我也想到那个什么石城去啊。至少那里应该不会有像埃斯皮诺沙这样的人在。”
“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也只能过一天算一天了。如果像沙里裘那样完全疯了倒也好!”
接下来又是长时间的沉默。沉默犹如一道冰凉的细线捆住了人们的手脚,酒馆里的人现在看起来跟佛得角的人们没什么两样。
因为不想被这种气氛所感染,拉斐尔三人结了帐走出了酒馆。清冷的空气反而让心情舒服了不少。拉斐尔长长地吐了口气,仿佛是要把刚才的不愉快全都排出体内。
库拉乌迪和阿尔加迪斯站在拉斐尔身后,望着少年单薄的背影,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压在上面。想要说些安慰的话,到了嘴边却又说不出口。
拉斐尔反而很有精神地说道:“我们赶快回去吧。弗里奥大叔他们差不多也该醒了。”他顿了顿,又说道:“我,一定要消灭埃斯皮诺沙!”
本书由。提供下载
非洲篇 第三章、声色非洲(东非、索法拉) 第一节
(更新时间:2007…5…1 16:33:00 本章字数:4588)
阿伦海姆号丽璐•;阿歌特
卡米尔•;马利奴斯•;奥芬埃西
费南德•;迪阿斯
埃米利奥•;菲隆
安杰洛•;普契尼
水手塞•;罗依特
库比
阿伦海姆号轻快地在海面上行驶着,犹如一只巨大的白色海鸟贴着海浪滑行。艰苦的旅行总算在开普顿告一段落,因为这里已经不再是菲南•;西鲁韦拉所支配的海域了,所以住宿也好,采购也好,都不受限制。其实说起来,这里的条件和地中海的那些港口比起来差了不知道多少倍,但是无论如何比起前段时间是好得太多了。就算海上风浪比较大,水手们也只当那是摇篮曲;就算吃的东西不合口味,他们也当那是宫廷宴席。水手的性格本来就比一般人要乐观得多。因为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如果能平安抵达下一个港口那就是大喜,如果遇上暴风雨迷失方向那就是大凶,大喜的事就算一直祈祷也不一定如愿,大凶的事却是越不希望它出现却偏偏会遇到。只要在海上,性命就没法由自己来做主,因此水手们只相信力量,尽力做好自己能做的事,剩下的就交给老天来裁决了。
从开普顿到下一个港口索法拉距离不算太远,阿伦海姆号的水手们一路唱着歌,一边卖力地开着船。一个名叫塔恩的小伙子甚至在桅杆与帆之间玩起了杂耍,看他灵巧地爬上爬下,身影出没于白帆之间,不时来一个倒挂金钩,再沿着帆一路滑到甲板上,顿时赢得一阵叫好声。
不知道这幅情景被船长看到了会说些什么,是把他臭骂一顿然后罚他不许吃晚饭,还是大大地赞扬一番并且自己也要爬上去试一试,一切都取决于船长大人的心情。不过,不管她做哪种选择,都会让卡米尔伤透脑筋。
事实上,虽然船长大人并没有看到这一幕,可拉斐尔此时同样是一张苦瓜脸,因为这位船长大人正在向他不停地发牢骚。先是把西鲁韦拉这个卑鄙小人从头到脚骂了个遍。丽璐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便开始天马行空地想象,凡是她所见过的看不顺眼的人全都变成了西鲁韦拉。比如艾特的大饼脸,西德兰瓦的三角眼,桑得尔的鼻子,舒派亚的肚子等等,把这些她讨厌的东西都凑到了西鲁韦拉身上,只差没给他加上牛角和蜥蜴尾巴了。然后遭殃的就是交易会所的掌柜、旅馆的老板、码头工人之类的角色,真亏得丽璐还记得他们的名字,连费南德都没那么大本事。
卡米尔已经连着听了五天了,虽然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一句重复的骂词,不过他还是有点忍受不了了。费南德是在丽璐开始发牢骚的第二天就不见人影了,估计是躲到酒桶里去了,埃米利奥和安杰洛则在甲板上忙东忙西,完全没有想帮卡米尔的意思。
这天,丽璐突然话锋一转,不再提那些受过气的人,而是开始骂起埃斯皮诺沙来。
“还有那个埃斯皮诺沙!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丽璐没头没脑地就这么来了一句,把正在找借口溜掉的卡米尔吓了一大跳。
埃斯皮诺沙这个名字对他们来说,仅仅和非洲霸者之证联系在一起,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就连费南德也不知道。不过,在开普顿的时候,卡米尔和费南德曾谈到过这个人。
“开普顿似乎比西非的那些港口要好很多嘛!”这是到达开普顿的第二天,卡米尔和费南德喝酒时说起的。
“是这样吗?”费南德只对眼前的酒感兴趣。前一段时间连饭都吃不饱,更别说喝酒了,所以费南德几乎是一到港口就钻进酒馆里去了,直到第二天卡米尔来找他,他还在喝,而且一点醉的迹象也没有。
“这里的房子看上去漂亮多了,不像卢安达那里那么寒酸。而且这里的人也比较有精神。”卡米尔打量了一下酒馆,很干净,也够宽敞,四四方方的桌子被磨得很光,椅子坐起来很舒服,而且酒的品种也比较多,从卡米尔进来到现在,已经看费南德要过三种不同的酒了。老板也好,客人也好,都带着笑意,似乎正享受着这里的生活。
费南德一口气喝光杯子里的酒,又让老板再加一杯。“你看到卢安达房子破,人人都苦着一张脸就觉得那里糟糕。房子好,又笑嘻嘻的就是好地方吗?”费南德看着杯子里泛着泡沫的黑啤酒,不过目光却是落在很遥远的地方。
“难道不是这样吗?”卡米尔说道。“看看卢安达就可以知道那个西鲁韦拉的为人了。人们造不起好房子是因为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都被西鲁韦拉夺走了,笑不出来是因为被迫要听他的命令。那家伙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殖民者!”
费南德摇摇头说道:“西鲁韦拉的确是个不怎么样的家伙,不过他的手段可比不上埃斯皮诺沙呢!”
“埃斯皮诺沙?那个得到非洲霸者之证的人吗?在东非一带做贸易的商人?”卡米尔问道。
“你认为他是怎样得到霸者之证的?”费南德反问了一句。
“这……”卡米尔从没想过这个问题。
费南德说道:“如果有一样名叫霸者之证的东西放在眼前,而且它能带给你无穷的财富,那么每个人都会想要得到它。不管是谁最先发现的,为什么最后会被埃斯皮诺沙得到呢?没有理由说一句我想要别人就会乖乖地交到他手上。不过,如果真的是这样……”
“也有可能是抢来的。或者偷来的?”卡米尔说道。
“不管是用什么方法,总之埃斯皮诺沙在东非必定有着强大的势力,让人宁愿放弃就在眼前的财富也不敢得罪他。你想他会是怎样一个人!”费南德一点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又接着说,“如果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或者压迫,肯定会有所不满,即使不在脸上表现出来也感觉得到。卢安达看到的那些人就是这样子,看起来像是行尸走肉一样,只不过是表面上装作顺从而已。可是这里不一样,都被埃斯皮诺沙欺压到了头顶上,居然还笑得出来,如果他们不是被虐狂,那就是精神已经麻木了,对反抗已经不抱有任何希望,过一天算一天。没有希望也就没有痛苦,所以才笑得出来。”
费南德的声音越来越响,他本人却还没意识到。店里的几个客人朝他看去,卡米尔连忙推了推费南德,他才停止了说话。
有好一会儿,两个人谁都没开口。费南德一杯接一杯地灌着酒,卡米尔则是有些担心地看着他。在卡米尔的记忆中,费南德从没像这样失控过,这似乎是他第一次露出真正的表情。
“别再喝了。你会醉的!”卡米尔说道。其实看费南德的眼神就知道他现在清醒地很。那双红(???)色的眼睛似乎正在看着什么,当然并不是看眼前的空杯子。
费南德说道:“我怎么可能会醉!我可是在酒桶中泡大的!”
卡米尔没有接口,他从没问过费南德关于他自己的事,费南德也从来不说。只有在塞尔维亚和克丽丝蒂娜跳舞之后提到了两句。他的父亲是美洲的阿兹特克人,母亲是西班牙人。对美洲人来说,西班牙人就像是魔鬼一样,烧毁他们的家园,强占他们的土地,掠夺他们的财富,还禁锢了他们的自由。可想而知作为拥有西班牙血统的费南德来说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
费南德自顾自说道:“我的母亲,因为是西班牙人,所以一直无法被父亲的族人所接受,父亲死了之后,母亲和我就被赶走了。母亲在靠近港口的地方开了家小酒馆,因为离港口比较近,所以有很多水手会来,总算能勉强生活下去。我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每天看到的就是水手、酒和赌博。”
“在家乡,所见到的人都是愁眉苦脸的,生活也的确很辛苦,每天晚上在帐篷里都冷地睡不着。到了酒馆以后却可以经常听到水手的大笑声,我也曾经以为他们是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后来母亲突然病倒了,没几天就死了,不过她却很高兴地说她终于可以去见父亲了。对母亲来说,这些年是一天一天熬过来的,为了要把我养大,她吃尽了苦,只有死才能让她从痛苦中解脱出来。那时我才知道为什么水手们看上去总是那么快乐,因为他们连替自己悲伤的力气也没有了,他们只能够大笑,希望下一次出海就可以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感觉上,和这里很像……”
费南德虽然在说自己的事,可是看起来就像是在讲不相干的人事情一样。卡米尔也渐渐了解费南德的个性了,他越是认真的说话越是不能相信,越是满不在乎的表情反而说明他越在意,为了不让别人察觉所以刻意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没人知道他真正的心思,没人知道他有多少痛苦的回忆,没人知道他心底的伤有多深。或许费南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