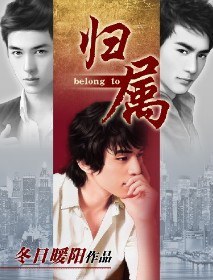何日彩云归-第6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徐忆兰睡到半夜,被天佑长一声短一声的呻吟惊醒:“天佑,你怎么啦?”她翻身下了床,摸黑走到外屋。
“我。。。。。。我痛。。。。。。”天佑嗫嚅地说。
“是肚子痛么?”忆兰焦急地询问,并把外屋的灯打开。她走到天佑床前,撩开蚊帐,俯身探向儿子。
只见天佑蜷缩着身子,大汗淋漓地侧卧在床。他那双痛苦的眸子布满血丝,两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见儿子这般模样,徐忆兰慌了手脚:“哪里痛?哪里痛呀,快告诉妈妈?”她伸手去试儿子额头,“呀!这么烫呀!”她快哭出来了。
“妈妈,我。。。。。。我受伤了。。。。。。哎哟。。。。。。”天佑断断续续地说。
“伤在哪儿?怎么会受的伤?”
天佑捂着下身,无力地对母亲说:“昨晚。。。。。。一根扁钢打在了我的身上。”
“你到哪儿去啦?怎么会有铁东西伤了你?”
“我。。。。。。我。。。。。。我去货运站干了一天的活儿,回来的路上。。。。。。”
“哎呀!你怎么能瞒着妈妈去下这份苦力呢!你的骨骼还嫩呢!”她难过地抱怨儿子,“让妈看看伤在哪里啦?”忆兰小心翼翼扒开儿子的短裤,只见天佑的阴囊处已红肿得像个小皮球。见伤得这般严重,她感到一阵的心酸:“怎么会弄成这样啊!哎呀,我的儿子呀!”
无疑这又是一场劫难!
一阵忙乱过后,忆兰陪儿子来到医院。经医生诊断,天佑的右侧睾丸已经破碎,另一只也已感染。
医生建议:必须马上住院,摘除睾丸。
听到这样的结果,忆兰一时呆住了,做梦也不会料到天佑会遭如此厄运。一个男孩子失去睾丸将意味着什么?当她反应过来,联想到不堪设想的后果时,她的头像挨了重重一棒,心脏仿佛被利刃戳中,她失声痛苦,苦苦哀求医生:“不能啊!不能摘除呀!求求医生,想想办法救救孩子吧!”
医生们经过研究,定出了治疗方案:摘除右侧的,尽一切努力保住左侧的。
也许天佑正值青春勃发之年,生命力旺盛,手术后两周,他的身体康复的很好,左侧的睾丸保住了。医生说,天佑的身体发育不会受到影响。能有这种结局,忆兰已觉万幸了。
天佑出院后继续在家疗养。经过了一次次的磨难,他成熟了许多,心境也开阔了许多,他不再怨天尤人,不再沉湎于痛苦之中,他已能面对现实,去适应环境。
有一天,他从街道办事处找工作回来,心情异常的好,见到母亲便说:“妈,上海自力铁工厂招收学徒,我已经报了名。”
“能去铁工厂也挺好,只是你还需要再休养一段时间。”
“我的身体已经好了,只要工厂一通知要我,我马上就可以去上班了,只是。。。。。。”
“能进工厂是最好不过的事,去不了也别急躁,我们慢慢再找,你岁数还小,晚两年工作也不要紧。”
“我知道,你不要替我担心,工厂不收我的话,我可以在家自学,要学的东西多着呐!”
“对呀,学好了本事不信没地方用你。况且这家工厂不一定不收你呀!”
母子俩都被一种不安的成分困扰着,但是他们仍抱着希望,仍然相互安慰着。
几天后,天佑幸运地被自力机器厂招为学徒工。厂方根据新招学徒工的考试成绩把天佑分配到维修车间当了名钳工。
天佑第一天下班回家就把工作服穿了回来,并绘声绘色地向母亲介绍他的工厂:“我们厂挺好的哎,厂里自己有食堂,还有澡堂呢!我们工厂虽然是小型工厂,可是我们厂出的钻床还很有名气呢。”言谈中,他已经爱上了他们工厂了。看得出,他把自己的命运和他的工厂结合在了一起,他已调整了生活航向,决心在新天地里干一番事业。
见儿子喜不自胜的样子,徐忆兰感到释然,她一面喜滋滋地听儿子介绍他们工厂,一面频频点头。
“妈妈,你知道么,我师傅是八级钳工哎,八级钳工的本事可大哩!技术上的难关都难不倒他哎!”
“是么,你师傅有这么大的本事呀?”
“真的,我们厂只有我师傅一个八级钳工哎,妈妈,我真有运气碰到这么好的师傅,我师傅说,钳工是万能工种,技术最全面。师傅让我努力学习、要求进步,爱工厂,爱工作。”
“对呀!他说得对,有这么好的师傅带你,算你好福气喽!”
天佑高兴得合不拢嘴:“妈妈,今天师傅给了我一把鎯头、一把锯弓、一把锉刀、一把铁錾、一把刮刀,师傅说,基本功要从这五把工具练起。对了,我师傅还说,他从几十个学徒工里挑上了我,叫我不要辜负他。”
“那你怎么说?”
“我说:那是一定的,我决不会让师傅失望的。”
“说得好!天佑,你真不能辜负师傅喔。”
“不会辜负的。”
大佑见哥哥和母亲那么开心地交谈,生怕冷落了自己,他便手舞足蹈地嚷起来:“我长大了也要当钳工!我长大了也要到哥哥的工厂去!”
“大佑长大了也当钳工,也到哥哥的工厂去。”忆兰搂过小儿子开心地又说:“天佑,再过几年,你就能讨个老婆回来啦。”由于高兴她与儿子开起玩笑。
天佑很单纯,他从未考虑过母亲刚才所提到的这类问题,听母亲这么一说,他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不要,讨老婆作啥,我不要,我要和妈妈一起过,”说到这儿,他望望弟弟,“要讨,就让弟弟讨一个回来好啦。”
大佑一听哥哥自己不肯讨老婆,反倒把讨老婆的“重担”推卸给他,他的眼睛一下鼓了起来,小脸也涨红了,连连摆着手嚷道:“哥哥为啥不肯讨?!为啥让我讨?!我也不要老婆!不要!”他的头摇的像个泼浪鼓。
“不要、不要,大佑也不要,”忆兰把大佑揽在怀里,“你们都跟妈妈过一辈子。”望着天真可爱的大佑,徐忆兰笑的好开心哟!
当枯叶纷纷扬扬地从枝头坠落之时,当瑟瑟的北风开始光临这座城市的时候,传来司马祺威被划成右派分子的消息。
乍一听说,徐忆兰甚觉愕然,她不相信这是真的,然而,这确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当她进一步得知,司马祺威不仅被开除了党籍,而且还被撤消了厂长职务的时候,她的心变得沉重了。
一个她心目中的好人,一个她所敬重的人,落到如此险恶境地,她怎能不为他难过?不为他今后的前程担忧呢?
厂里到处有人议论这件事,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话题离不开谈论右派分子的种种罪行,每当人们谈论这类问题时,个个表现的义愤填膺,人人对右派分子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在皮革厂内,大家议论的焦点是司马祺威,他是一厂之长,又是从延安过来的老干部,他的特殊身份引得人们的特殊关注。
每当人们议论司马祺威的时候,徐忆兰总是缄默不语地忙着自己的工作。一颗心却慌乱起来,常常屏住呼吸听着,她急于了解司马的更多情况,又不敢去打探,只能从人们的只言片语里捕捉司马祺威这个名字,她对这个名字异常敏感,异常关心。
这天上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天上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初冬的雨水是冰凉的,风也呛人。
徐忆兰在库房整(http://。)理着收料单子,忽听汽车刹车声,她伸着脖子向窗外张望,只见一辆送货卡车停在了仓库门口。她放下单子,赶紧去把库房的大门打开。不经意中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是谁?忆兰的心陡然一动。
只见那人穿了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衣,他的头发和脊背都被雨水淋湿了。只见他把耷拉在额前的一绺湿发向后撩了撩。然后一个翻身从车上跳下来,动作麻利地打开后槽帮。
是司马!徐忆兰看清了眼前的司马祺威。他怎么当上装卸工呢?干这么重的活儿,他吃得消么?她的心中起了波澜。
只见司马祺威转过身子,背对着卡车,很内行地岔开双腿牢牢地站着,他的右臂插在腰间,头颅向左侧歪着,左臂勾向后脖颈,左手张开,摆出准备接应货物的架式。
车上的另一名工人搬起一个木桶放在了司马祺威的右肩膀上。司马迅速地抓住木桶上沿,身体稍稍顿了顿,感到平稳后,他“噔噔噔”地迈开步子进了仓库。
徐忆兰呆呆地注视他的一举一动,当他经过她身边时,她竟然有些手足无措。
司马祺威被重物压迫着,身子不由地向前倾,头稍稍地向下低垂,一只手狠命抓住木桶,显然,他觉得肩上的重物很沉重。他进了库房,不知把货物往哪儿放,他开始放慢脚步,微微抬起头,寻找着码放铁钉的货位。他看到了徐忆兰不由一怔,嘴角微微抽动一下,不知是否想对她微笑。
见此情景,忆兰的一颗心抽紧了,她向他靠近,下意识地张开双手,她想帮他一把,又无以下手。一阵慌乱过后,她才想起应该为他引路:“来,放在那里。”她领着他来到码放铁钉的货位。她比刚才从容了许多,并帮他卸下货物。
卸下了重物,司马祺威吁了口气,同时,目光移到了忆兰的脸上,定定地注视着她,苦涩的目光中闪出一道光亮。
徐忆兰避开了他的目光,她不忍心看到他那双痛楚的目光,她不敢看他眼中的那束光亮。
司马祺威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反身往外走,准备继续卸货。
徐忆兰见他满头满脸的雨水,不声不响把一条毛巾塞到他的手里。
司马祺威接过毛巾,把头、脸和脖颈上的雨水擦净后,把毛巾还给徐忆兰,他的嘴张了张,但没说什么。他又开始把货一桶一桶扛进仓库,徐忆兰则帮他把货一桶一桶从肩上卸下码放整齐。两人配合默契,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
司马祺威随卡车离去时,忆兰站在门口目送他老远老远。
就这样,司马祺威在车队当装卸工的日子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春天。
一天,司马又到仓库卸货,没看见徐忆兰,他有些焦急,四下望望发现她正登在木梯上整(http://。)理货架顶部,司马走了过去。一般情况,他从不主动找她说话,这次是例外,显然他有重要的事情告诉她。
徐忆兰听到有人喊她,低头往下看,看到了一脸凝重的司马祺威,她下了木梯。
“小徐,我就要离开上海了。”
“离开上海?”她异常震惊,“到哪儿去?”她追问一句。
“到青海。”
“到那儿去干什么?”
“接受改造。”
忆兰惊讶地睁大眼睛,只觉一颗心坠坠的疼疼的。
“得去多久?”她哑着嗓子又问。
“不知道,”他苦笑笑,“估计不会短,三年、五年,兴许一辈子。”说这话时,他并不显得有多紧张。
“什么时候动身?”
“后天。”
“呀!后天!怎么走这么急?”两人面面相视,无语。良久,徐忆兰又问:“行李都准备好了么?”
“有现成的衣服被褥。”
“那怎么成,青海一定很冷很冷。。。。。。”
又一阵沉默之后,司马祺威开口道:“小徐,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什么事,你只管吩咐。”她抬眼看他,眸子里渗出缕缕忧伤。
“我走了以后,请你帮我关照庆华,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