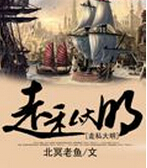大明悲歌:布衣王妃-第17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刚上了茅厕,忽而想到一绝对,我若对上了你可要说话算数,听着:吃了拉,拉了吃,有吃有拉,有拉有吃,吃吃拉拉,拉拉吃吃,先吃先拉,先拉先吃!如何?哈哈,我答上来啦。”
“啊。。。。。。”白杨仰天哀嚎,“再来,上联:为你痴为你累为你受尽所有罪!”
林诗诗张口便来,“下联:为你死为你狂为你咣咣撞大墙。”
“横批我来:为爱疯狂。”
秋冰月哇哇叫着情不自禁地冲上来拥抱林诗诗,不停抹泪:“诗诗,你太有才了,都会举一反三啦!”
空留朱祐枫原地继续保持吐血状。
白杨则疯狂的摇着扇子:“我需要冷静,我需要冷静。。。。。。”
月,纵自在逍遥,不再现会白杨与林诗诗在船头的打情骂俏,秋冰月与朱祐枫并坐在船尾,哼着小曲,朱祐枫的嘴角弯到最好看的弧度,看着她开心的笑,绽出甜蜜的小酒窝,听她美美的歌唱,那歌声醉了苍穹醉了明月,也醉了他的心!
四人一路上打打闹闹,嘻嘻笑笑,那晚对了一夜的诗后,白杨与诗诗的关系终于得以稍稍缓和,大家一起观观景,说说醉人情话,终于到了江南地界,水路无法再行,给船家结算了船钱,一行人弃舟上岸,大家下得船来一路步行,心便越来越凉,真是处处可见拖儿带女的流民,处处不见庄稼,处处水汪汪,处处凉荒荒,哪里还有昔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风景旧为谙的江南美景。”
朱祐枫下船时已易了容,因怕遇上朝廷派来的官员,大家都是一脸凝重,冰月与诗诗也收起了笑脸,距离堤坝十里时已无路可走,全是大水肆虐后留下的残垣断壁,街上淹死的牲畜随处可见,空气中飘浮着浓浓的臭腥味。
“河水弯又弯,冷然说忧患,别我乡里时,眼泪一串湿衣衫,人于天地中,似蝼蚁千万,独我苦笑离群,当日抑愤郁心间,若有轻舟强渡,有朝必定再返,水涨水退,难免起落数番,大地倚在河畔,水声轻说变幻,梦里依稀满地青翠,但我鬓上已斑斑。”
悲凉的歌声自身旁飘过,是一个粗壮的农夫,身上披着蓑衣,样貌憨直,拉着一辆破旧的牛车,车上坐着一个穿着破衣的农妇,怀中抱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孩,是他的妻儿吧?他正一步一回头的从朱祐枫他们身边走过。
第九十六章
“这位小哥,”朱佑枫忙开口唤住他,“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农夫愣了愣,摇摇头道:“家园被毁,无地可种,女儿贱卖,还能去哪里?去一个能讨得一口饭吃,有个地儿睡得地方便足够了。”
“天灾不可避免,可皇上不是已派钦差大臣前来,救灾的银子也尽数拨到了么?”
农夫嘲讽笑笑,“都是官,哪有民的活路,朝廷拨了银子,我们老百姓如何见得着,银子都被官家换成了粮食,再卖给灾民,五斤米要二两银子,二两银子够一户人家吃一个月了,老百姓根本买不起,只得卖儿卖女,背井离乡。”
说完悲叹一声,摇摇头,一步一步消失在雨雾里,看着灾民饿成菜色的面庞,悲凉蹒跚的背影,众人心中都酸涩不已。
“岂有此理,天灾连连不断,国库空虚,皇上能凑出这些赈灾的银饷已是相当不易,这些地方官,竟然还敢发民难财,既让我知道,岂有不管之理,他们吃了进去,统统都要给我吐出来。”朱佑枫忿忿说道。
“小枫,你现在身份不过只是一介布衣,如何有权去责问他们,如此一来,岂不是要暴露你的身份?”白杨轻声道。
“白杨,你看看这等悲惨荒凉景象,那么小的孩子,头上插一根草就随意被贱卖掉,从此远离父母,为奴为婢,此生用不得见,人心都是肉长的,若是能有一线生机,哪个爹娘会舍得卖掉自家的娃儿,我决定了,我要留在此地,直到洪水消退,河道治理完工,哪怕公开身份,也要镇住这些恶霸,不论他们的背后的人是谁?绝不手软。”
“既如此,那我也决定再次陪你上这个没有烽烟的战场,做你的副将,就算天塌了,也有我陪你顶着。”
白杨伸出手,两支充满力量的手再度紧紧相握。
突然两只洁白的玉臂加入进来,齐声道:“还有我们。”
秋冰月看向朱佑枫道:“这回你可别想在甩下我,你们男人上河堤,我们女人就留在城中安抚灾民,我学了这么久的医术,终于可以有施展的一天了,开家医馆,悬壶济世,也是我的梦想。”
朱佑枫深情地注视着他,只轻轻说出一个字:“好!”
“还有我,我也不走,当年我的家乡瘟疫时,也是这般光景,我虽不会医,可我有武功,劫富济贫的事还是能出力的。”
林诗诗眼泛泪光,看着白杨。
白杨被他大胆地目光看得别过脸去,面颊微红,道:“随你。”
“既然大家都有了主意,老乞丐就先率帮众弟子散去做事了。”
蒙帮主向朱佑枫等人一揖,丐帮弟子便尽数散去。
“七师弟,你是随着我们还是随王爷?”武当七侠中的大弟子钟殊离问道。
“各位师兄不必管我,白杨愿紧随王爷,若有事再发信号联络吧,各自小心。”
钟殊离点点头,“我们先上河堤看看。”说罢转身领着武当六侠离去。
“小枫,我们如何行动?”
“走,去会会那个皇上派来的钦差,看看此人是个什么角色。”
朱佑枫冷着脸道。
四人先去附近尚还经营者的客栈要了两个房间,未做任何休整便向河堤而去。
这是一件河堤边临时搭建的棚子,棚子四周都堆着乱七八糟的沙包稻草,简陋之极,空气中充满着潮湿腐烂的泥土气息,棚里有一张长桌,一个官员模样的人正在埋头看牛皮图纸,他的官服上满是泥水,黑靴上是水干后结成过一块一块的泥块,看得出此人必定亲自去河堤上视察过多时。
此刻他正拿着笔在纸上画着,算着,棚子里进来好几个百姓,吵得不行,他头也没抬,心思全在图纸上。
“嘘,别吵。”人进入状态的时候最怕有人打扰,那位官员头也没抬,不理会来人,过了一会就没人说话了,他又进入了沉思,自语道:“这里需加固堤坝,这里。。。。。。还有这,全是淤泥,得清了。”
感觉身旁有人,随口问道:“你说,这片堤上的良田是否该清除掉,不清会破坏了整个河道。”
“该。”
一个语气很重的声音在他耳边炸响,官员猛地抬头,他从没见过那样一双眼睛,亮丽的如同天上的明星,是那黑夜里最闪亮的星辰,不若太阳般狂热,却也要给人温暖,官员眨眨眼,再看,那个目光又变得很犀利,变得要将人看穿,将人逼退。
官员猛地一回神,怒喝道:“大胆狂徒,谁让你进来的?来人。”
“大人不必急着将我等轰出去,或许大人此时正需要人手也说不定?”朱佑枫气定神闲的说道。
“哼,何人在此放肆,本官可是朝廷的钦差大臣。”
“既是钦差大臣,便只会再此比比划划,全然不顾外边正洪水肆虐,阴风骤雨?百姓疾苦是在这图纸上便能看得见的么?”
“嘿,你谁啊你,哪冒出来的瘪三,敢对本官指手划脚,你们还愣站着干什么?还不将这些人轰出去!”官员气白了脸冲门外侍卫嚷道。
“不必你们动手,我说完自然会走,工部侍郎徐大人。”
朱佑枫拿过桌子上唯一的一个杯子一口饮尽了杯中之水,重重的放在了桌上。
“你,你轻着点。”
可把徐贯心疼的呀,这可是前天刚订好的桌子,工具不齐,手艺不精,他都舍不得压,生怕压坏了,这人可别给他拍散架了呀。
徐贯这才细细打量着面前之人,他很高大,挺拔,充满慑人的力量,虽身着一件半旧的墨绿色布袍,用同色布袋束发,黑布靴,腰悬佩剑,五官也不算出众,可浑身却散发着与生俱来的高傲与潇洒,自信与霸气,却又混进了善于洞悉人心的细腻与机警,浑然天成,那是一种很奇妙的魅力,让人无法形容,这气势是他永远无法企及的,心道和此人打交道一定要小心。
徐贯用手轻抚胡须,微微点头:“这位大人不知在朝中官拜何位?能知徐某人官职?大驾光临,有何要事?”
朱佑枫把玩着桌上的青花茶碗,语调缓慢而铿锵说道:“徐贯,浙江淳安人,天顺元年进士,历任兵部主事,福建右参议,辽东巡抚,在福建时曾自作主张将管家粮仓分给灾民,差点宰了管粮仓的军官,在辽东时严办不法军官,将罪大恶极者游街示众,现如今在辽东一提起你大爷的名号,军中的老兵油子都会吓得哆嗦,我说的可对?”
“下官拜见大人。”
徐贯在朱佑枫话音刚落下便一撩衣袍跪了下去,他虽不知此人是何来历,但能将他的官历了解得一清二楚,定是朝中数一数二的大人物,此次是微服私访吧?可此人面生得紧,究竟是谁呢?
其实徐贯曾在兵部任职,算起来还是朱佑枫的手下,只是朱佑枫早年便带兵出征哈密卫,从而将兵部尚书一职卸了去,故二人相交不多,但朱祐樘将全国六品以上官员的简介张贴在文华殿中,曾经他们兄弟二人就并臂站着一同认真研习过所有官员的资料。
只见朱佑枫自怀中缓缓掏出一块金光闪闪的腰牌,徐贯睁大了眼睛,口中喃喃道:“皇上御赐如意金牌,见牌如见圣面,”颤抖高呼道:“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四周侍卫亦跪下高声齐呼。
“都起来吧。”朱佑枫环顾了一眼四周,将金牌收回怀中,这金牌是他出征时朱祐樘赐给他的,之后发生了许多事,故一直未能返还宫中,能拥有此金牌者朝中只有他,只是朝中大臣却无人知道,没想到在此派上了用场,他原也想公开身份,但为免日后横生枝节,想想还是作罢,这才将金牌示出。
“本官姓氏不便奉告,还望徐大人见谅,徐大人请坐。”
朱佑枫伸手将徐贯扶起,严厉说道:“我不与大人打官腔,我来此之前已去城中查看过,江南水患如今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是河坝,大坝不是毁了么?咱们便把他堵上,还要修的固若金汤,第二是百姓吃饭的问题,听说此地的官员与奸商勾结,将朝廷拨下的灾银换成粮食,再以高价出售给灾民,可有此事?”
“确有此事,不过。。。。。。”徐贯看看朱佑枫,吞吞吐吐。
“你即知此事,为何还任由他们胡作非为,让百姓卖儿卖女,背井离乡,你便是这样做钦差大臣的么?对得起皇上的重托,对得起灾民的眼泪,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么?还是徐大人也沦为了官商勾结,唯利是图的小人 ?'…'”朱佑枫狠狠拍了一下桌子。
徐贯吓得跳起来,“哎哟,大人,您轻点儿,小心桌。。。。。。小心手疼。”
朱佑枫一顿,冷哼一声。
“下官不敢欺瞒大人,下官到此地已一月有余,早已查清这些内幕,迟迟未能采取行动,绝非下官是贪赃枉法之徒,胆小如鼠之辈,只是大人怕是还不知这些官仓背后之人是谁,本官早已上奏皇上,只是宫中仍未见回音,下官不敢擅自动手啊!”
“你!”
朱佑枫抬起手,看到徐贯可怜巴巴地看着桌面,又悻悻的将手收了回去,站了起来,“我还真是小看了你,当年你的那些手段都去了哪里?我原一直不明白皇上为何单单排了一个军中之人前来治河,到了此地方才明白皇上的苦心,原来这里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