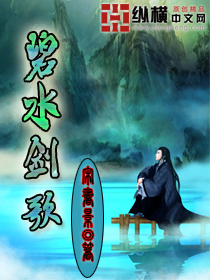玉落碧水凝黛情-第14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梦中似乎有双深邃的眼睛,映着灼灼火光,直抵人心;又似乎有一双温暖的手,不时抚在她额头:朦胧中,是谁的声音,低低同自己说话?听不清他说什么,只听到他的声音,心里便渐渐安宁下去。
再次清醒的时候,终于可以睁开眼晴。屋子里静悄悄的,听不见任何声音。纱幔轻盈,烛光摇曳,有淡淡的药香从外边飘进来。铜鼎玉炉,恍若江南梦里。
“丫头——”南宫倾城亲自端着一碗药从外边进来,看见已经睁开眼晴的黛玉,惊喜的一下子哽住。
“嗯?玉儿?!”爬在床畔的水溶从疲惫中惊醒,急忙抬头,顾不得眼前的晕眩,猛然间握住了黛玉的双肩,把自己的脸埋在她的怀里,抵着她瘦弱的身子,低声的叫着,“玉儿……”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黛玉微微低头,想撑起手臂同样去拥抱他,却发现自己一点点力气也没有,手指略一动,身子便疼痛万分。
“先让丫头吃药!”南宫倾城走到床边,抬手拉了水溶一把,“等我走了,你们再说悄悄话。”
“哥……”黛玉抬起眼皮,苦笑着看南宫倾城。这个一向十分注重仪表比女人还美的男人,此刻也胡子拉碴一脸的憔悴,往日的风采不知哪里去了,只有一双妖媚的眼晴里闪烁着惊喜的目光,一如往日。
“丫头,三天了!已经三天了!你再不醒来,这家伙恐怕要杀尽荷兰余孽,顺便把哥哥我也杀了……”南宫倾城一把推开水溶,坐在床边,隔开二人,端着药碗装模作样,不喂药,只顾着说话。
“躲开!”水溶此时的仪容,比南宫倾城也好不到哪儿去,一身家常玄色夹袍歪歪斜斜的披在身上,衣带松松垮垮的系着,发髻松散,王冠未带,下巴上原本湛清的胡子茬此时已经长出凌乱的胡子来,让他原本硬线条的五官上,更多了几分沧桑之感。
南宫倾城话未说完,便被水溶一把夺过药碗,另一只手顺便把眼前的障碍清开,“说那么多废话做什么?先给玉儿喂药。”
黛玉微笑,看着这两个人又吵又闹的情形,生离死别之后的重聚,在此时才真正的体味出甘甜来。
“玉儿,喝吧,别怕苦。”水溶把黛玉轻轻地扶起,让她靠在自己的怀里,熟悉而强烈的男子气息将黛玉包围,隔了衣襟,隐隐感觉到他的体温,他扶住她肩头,低头凝望她,目光温和专注,“等你的伤好了,我带你出去骑马。”
“我自己骑,你要专门给我挑一匹好马。”黛玉撒娇般的靠在他的肩头,憔悴的笑着,眼晴里闪着幸辐的水光。
“好。只要玉儿好好地,什么事都依你。”水溶爽朗的一笑,将药碗递到黛玉唇边,一面看着她喝,一面轻拍她后背,落手极轻,也笨拙之极。
待到黛玉把药喝完,水溶忙又从一边的高几上端过一碗温热的蜜水给她漱口。
黛玉低头喝水,但觉心中暖暖的,如在云端,眼晴涩涩的,有水滴落下溅在他手背。
“好了,玉儿……吃了药,再睡一会儿,伤就没事了。”他把她轻轻地放好,又拉过簿被给她盖上,然后又安静的坐在床边。
“我没事了……”黛玉看着水溶,再看看床边站着的南宫倾城,“你们都去休息吧。”
“我无所谓,原本就是一个大闲人。不过有人军公务堆积如山,再不去前面升帐议事,恐怕各路将军都要闯到这后院卧室来了呢。”南宫倾城靠在床边,斜斜的站着,微笑着看了水溶一眼。
“不用你多嘴。”水溶不满的瞪着南宫倾城,没眼色的家伙总在这儿站着,人家两口子想说句私房话都不行。
“你们都出去,我要再睡一会儿。希望我再看见你们两个的时候,都是原来的样子。”黛玉无力的抬手,牵了牵水溶的歪斜的衣衫,这位向来以肃整冷漠著称的王爷,何时这样衣衫不整过?
“呃……”水溶低头,看见自己系错了的衣带,脸上闪过一丝尴尬的浅笑,抬手把黛玉的手放入被子里,又俯身吻了吻她的额头,轻声道:“你好好睡,我去去就来。”
说完,水溶起身,一把拉过南宫倾城转身往外走,出门前吩咐门口的丫头一声:“照顾好王妃。”
“你拉我做什么?”南宫倾城被水溶拉出门口,方甩了甩袖子,似笑非笑的瞪着水溶,“莫非你心中有鬼?”
“胡说!明明你心中有鬼。”水溶瞪了南宫倾城一眼,又回头看了看屋门口垂着的撒花门帘,“玉儿的身子到底怎样?贺兰臹那一掌可是正好打在她的后心!”
“没事,若伤及心脉,此时她又如何会醒来?既然醒了,那就没事了。放心吧……”南宫倾城敛了敛平日里玩世不恭的笑容,看着水溶,压低了声音,却坚决的说道:“我要带她走。”
“不行!”水溶断然回绝。
“这里不适合她!这里兵荒马乱,缺医少药,你要每日忙于军务,跟回纥和胡人相互周旋,她的身子是什么状况你也知道。所以一一我必须带她去江南,等她的伤养好了,你再来找我接她。”南宫倾城放缓了语气,深深劝道。
“不行,玉儿哪儿也不去,就在我身边。”水溶不给南宫倾城说话的机会,抬脚离开。三筝如魅影一般尾随而去。
“顽固!”南宫倾城对着水溶主仆匆忙而去的背影,生气的骂了一声,转身又回到了屋里。
黛玉已经沉沉入睡,南宫倾城精心调配的汤药显然已经发挥了作用。此时的她呼吸平稳,脸上带着新生婴儿般的宁静。她的睫毛浓密的在眼底投下一片阴影,眉头微微皱着,仿佛做着一个永远都不醒的梦。
南宫倾城不去梳洗,只是静静地坐在黛玉的榻前,看着她,仿佛自己也跟着她一起入眠似的,心中什么也不想,比睡梦中更加安宁。
宁朔城主将府邸的后宅虽然不及王府奢华,但日用所需也是应有尽有。黛玉在这里养伤,倒也未尝不可,只是南宫倾城却忽然之间舍不得把她留在这里自己离开。
兄妹之间,血脉相连的感觉,深深地牵动着他的心,好像妹妹病一分,哥哥便痛三分似的。这种感觉很奇怪,初时南宫倾城还以为自己爱屋及乌,因为水溶所以对这个妹妹不一样,但通过这一次,他是真的明白了‘血浓于水’的真理。
丫头,若是我没有被抛弃,该多好?那样,我便可以亲眼看着你一点点的长大,从一个黄毛丫头,出落成今天这样的绝世美人。那样,我会有一个永远值得回忆的少年时光,而你也一定会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丫头,你长得跟娘并不是很像。只有几分柔媚像她……
当初,娘亲突然早产,生命垂危时,是否也是这般苍白无力?
……
水溶有军务要忙,不在黛玉身边的时候,南宫倾城看着黛玉熟睡的脸,一味的胡思乱想,打发自己的寂寥。
五月的塞北,风虽然大,但却不再那么冷冽。
黛玉再次醒来,又是一天的时光。睁开眼睛看见守在自己身边的人依然是水溶,只是这次他并没有睡着,而是披着一件云雁纹月白长衫坐在床边,手中拿着一份军报,一边读,一边皱紧眉头。
“又有麻烦了吗?”黛玉轻轻出声,水溶紧皱的眉头展开,手中的军报随意放在一边,人已经转过身来,探手抚上她的额头。
“嗯……不热了。恢复的不错,倾城的药,还算拿得出手。”清爽的笑意和简单的话语,把黛玉的心填的满满的。自从(炫)经(书)历(网)一场同生共死,两个人之间仿佛和以前不一样了。哪怕是最简单最细小的一个动作,在彼此的眼里心里也充满了柔情蜜意,令人心驰神往。
“哥哥呢?”黛玉抬手握住水溶抚在自己额头上的宽大手掌,轻轻地揉捏。
“说是要为你寻一味药,去了半日,还未回来。”
“我都好了,又去寻什么药?”黛玉轻叹,自己这副身子,究竟要用多少药来培着?
“贺兰臹打在你后心的那一掌,差点伤及你的心脉。如此重伤,必用良药。否则落下病根儿,老了可要受罪。玉儿听话,好好养着。”水溶轻轻地抚摸她消瘦的面颊,肌肤依然滑腻,但小脸在他的掌心里越发的憔悴,这一场劫难,让原本就消瘦的黛玉越发憔悴不堪,整张脸上,就一双眼晴显得越发大了,忽闪忽闪的眨着,更加令人心疼。
“他们……”提及贺兰臹,黛玉心中百味陈杂,说不出什么感觉,恨自然是恨之入骨,但也有几分同情和悲哀。
“贺兰臹没死,还活着。”水溶自然知道黛玉心中的疑问,不待她问,他率先回答。
“我见过贺兰臻。”黛玉眼前忽的闪现另一个人,那个中原话说的十分撇脚的魁梧男子。
“何时?!”水溶一愣,惊讶的问道。
“贺兰臹带着我入宁朔的那个晚上……”黛玉把当晚的事情简单的说了一遍,水溶听完后冷哼一声,说道:“果然不出我所料。”
“怎么,难道他也算计你吗?”
“贺兰臹是他父亲一场酒后失德的闹剧生下的孩子,虽然身上流着回纥人的血,但却不被回纥贵族奉承,相反,贺兰臻作为回纥王的养子,却更能得到西藩王族重臣的赏识。然贺兰臻身上流的血终究不是回纥王的。所以贺兰臹变成了贺兰臻的绊脚石。”水溶一边给黛玉说着,一边把她扶起来,又拿了靠枕垫在她背后,让她坐着更'炫'舒'书'服'网'一些。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贺兰臻想借你的手除去对手?”黛玉轻笑,这种借刀杀人又顺便送人情的把戏,在大户人家的内宅之中十分常见。原来战场上,男人之间,玩儿的也是这一套。
“可我为什么要帮他?既然当时他亲手把你送回贺兰臹的手中,那么他也算得上是帮凶了,如今看来,我放了贺兰臹一条人命,又送他回回纥去,还真是做对了。西宁王被倾城摘了脑袋,西疆军易主,北疆亦受到许多束缚。此时非常时刻,西藩能挑起一场王室之间的内乱,是再好不过的了。”水溶平静的说道。
南宫倾城因痛恨西宁王谋同贺兰臹,设计暗害水溶,所以在西宁信使带着贺兰臹入宁朔的时候,独自一人闯西疆,趁夜高风黑杀了西宁王。
幸亏西宁军中有几个将军与水溶素日有些来往,当时把事情压下去,没有闹大,朝中下谕旨令水溶临危受命担当起镇守西疆的重任,水溶连日忙碌,密调兵马,把西疆军用自己的北疆军暗暗地辖制住,方得以喘口长气。
是以,黛玉这几天养伤昏迷的时候,水溶却是日理万机,每天最多只能睡一两个时辰。
“可你不是说过,要把贺兰臹碎尸万段的吗?”黛玉偎依在水溶的怀里,抚弄着他胸前的衣带,解开又系上,系上又揭开,来来回回,变换着结子的样式。
“是,但不是现在。若现在回纥没有内乱,我朝西疆不然大乱。受苦的,是我天朝干千万万黎民百姓……”隐忍和无奈在水溶的话中带出来,让黛玉再次对他肃然起敬。
黛玉自然不是那种沽名钓誉之人,事实上,水溶这样的话也绝非沽名钓誉之话。
国破家何在?黛玉被贺兰臹一路劫持,感受最深的,便是这句话。
“天朝百姓何其幸,有我们这样一位忠义凛然的北静王。”黛玉轻叹,“只是端坐庙堂上的那个人,实在是昏庸至极,欺人太甚。”
“他被太后囚禁了。就在你被贺兰臹俘走的那天晚上,东平王协助太后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