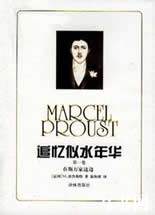追忆似水年华-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文,笔锋犀利,但也冷静和客观。
我想起那天晚上弹吉他的他却是非常感性地,把一种淡淡的有关岁月和青春的伤感传染给我们,我甚至感受到了离别的痛。我常常看见他一个人走在校园里,穿过林荫道和花坛,走到图书馆去,我更经常地去图书馆,坐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静静地打量他,看着他从书架上取下书或者杂志,专著的阅读,有时是会心地笑,有时同时抬起头沉思,经常是一个晚上的时间我都会这样虚耗过去,当他的视线转向我时,我连忙低下头假装看书。有时在路上碰到了,他笑着说,嗨!我挤出一个笑,点点头,慌忙就逃走了,过后想起来就脸红,笑自己怎么如此失态,也不知道杨涛发现了没有,要是发现了,他会在心里取笑我吧,有时看书,书中浮现的面容还是他,只是面目有些模糊,没有清晰的轮廓,惟有笑容是切实可感的,那阳光一样的笑,再隐晦的天空都会变得灿烂了吧。我不由得想着我可以拥有这样的笑容,那么我的生活一定是温暖的了,不管怎么样的失意和打击都可以面对的了,我沉思的时候无意中划下的字竟然是他的名字,这个发现让我心慌意乱。因为他曾经说过的话,我可以常常微笑。狄云是最早注意我变化的,她说,禾子,你好象变了很多哦,你变得爱说爱笑了,是不是春心动了哦。我追着她打了两拳,说,胡说些什么呢,我这种人,怎么会。
我去过杨涛宿舍几次,从他书架上拿走几本书。他的宿舍楼在我的前面,我总会从他的窗下经过,晚上,从教学楼回来,我会禁不住看向他在二楼的窗,如果亮着,我心里便会欢欣一些从窗户里映出来的人影里辨认是不是杨涛,我会想,杨涛,他在做什么呢?看书还是聊天呢?如果窗户暗着,心里便会一下沉落下来。当这已成为习惯的时候,有一次,我把它写成了一首诗,交到了文学社的稿件里:
《昨夜之灯》
昨夜
我从梦中的故园走来
我流浪的路还很长很长
我去看多年的誓言
看他们从生根到发芽
不知有没有开花
我会辛勤地浇水,施肥
不管它是昙花还是玫瑰
想象着会有满天如花的诗句
飘下来
就象风
安静了,停在对面的屋檐上
少年的誓言成长起来
像发丝,和风轻轻擦过
只剩下飘和遥远
花却一直没开
花庖渐渐长大了
用躲避的眼睛
看冬天一个个地过去
我一直在漆黑的夜里
仰望晨星
害怕有一天
我会忘了,那个种花人
曾经看它的眼睛
不知道
它什么时候就会消失了
就像我突然剪短的长发
从此,季节的河流中
不会再有诗
走过昨夜的灯光
我怀想起,遥远的发丝
然后盼望着它滋长
绵延出一路的明亮
再次看到杨涛的时候,他问我,你那首诗在写什么呢,写一种信仰还是一种希望。
我说,那只是一种隐喻,你怎么理解都可以。
文学社的刊物《江南一叶》被评为最佳刊物,社友们都戏称是我和杨涛联手的结果。我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出什么里。杨涛说,收稿、选稿、选图片不都是你吗,谦什么虚哦。我说,那不也是你的意思吗,我可都依着你的。旁边的人看得笑死了,说你们两个怎么回事,一唱一和地。我一下子红了脸,转过头去。
我依然按照文学社的要求定期交一篇稿子,这时我已经是文学社的责任编辑,负责整理稿件和改稿,于是常常会遇到杨涛,有时我们会聊上几句,和想象中的浪漫的中文人不同,我所看见的杨涛总是沉着和冷静,有条不紊地处理社团内部事务,包括一期刊物的排版、印刷。
有一次,他对我说,你的文章太阴郁了,缺少阳光,这是你底子里的东西,不要不承认。
我说,我只是比较敏感而已,要看透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你的文笔刚健,大气,朝气蓬勃,你敢说这是你的全部吗?
杨涛说,生活本就有笑和痛,我着眼的是明亮的部分,你却相反。
我说,大家都喜欢明亮的东西,有多少人关系黑暗中的挣扎?
杨涛楞了一下,笑着说,你真是个比较奇怪的人。
我和杨涛的意见常常是相左的,比如在刊物中插图的选择上就常常发生分歧,我要已日薄西山为背景、,而他会选择小桥流水人家的温馨图画,我喜欢淡远,他喜欢景物的逼真,我们努力想说服对方,结果常常是依我的意见,他故意做住无奈的样子,说一声“好男不和女斗”。
寝室里的生活是很有意思的事,每个人都会有走的很近,比较要好的朋友。李晓和吴含是同乡,她们是很要好的,特别喜欢坐在一起用家乡话聊天,两个人叽叽咕咕的,旁人根本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她们可以从上午一直聊到下午,连中饭都可以省略掉的。晚上熄了灯,为了怕影响我们,两个人就跑到阳台或者浴室里继续聊,聊够了才像一只猫一样无声无息地钻进来。走廊上总会有穿着睡衣抱着电话机的女孩,夜深人静了还发出蚊子一般的哼哼声。我们还凑钱买了锅,周末有空的时候就在寝室里吃火锅。守着一只小火炉,吃吃停停,一边聊天打趣。
我和彤云常常走在一起,其实我们的性格也并不相合,她外向开朗,我性情古怪,她一路上可以像只小鸟一样叽叽喳喳地说个不休,我则常常保持沉默,我们走在一起也只是一起去吃饭,上课。有一个周末的晚上,寝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们随意的说着无关紧要的话,彤云躺在上铺看小说。她突然探出头对坐在桌边的我说,禾子,我中学时最好的朋友小名也叫禾子,大学时的好朋友也叫禾子,看来我和禾子真的好有缘。我呆了半天,后来我们才真正亲密起来。我们一起钻到文科楼里去摸那些被虫子蛛过的门窗,在中文系的教室里,一个白发的先生正在讲解古诗词。我们遛到后面去坐好,一本正经地记笔记,外面有竹影婆娑,逢着讲王维的禅诗,便像入了禅境,时光倒流,浑然忘我。
圣诞快到的时候,大家商议着怎么过圣诞节,有说去参加舞会的,有说去弄篝火的,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是卖圣诞卡,再用赚来的钱聚餐。
我们先去批发了很多的圣诞卡,五毛,七毛一张,可以卖到一块,一快五,先是在学校里摆一个小摊子,可是销量并不好,要买卡的人虽多,可卖卡的人也很多。后来我们决定每个人拿一百张到各个寝室里去卖。这次是单独行动了,没人掩护,就象作贼一样不安,敲开一个个门时,一开口脸还发红,别人一句“不要”掉头就走,一天下来,销量少的让人心灰,只有彤云的业绩最好,卖了几十张,她是个敢冲敢闯的人,还有一张甜甜的笑脸。大家受了她的鼓励,在寝室里对着镜子练习笑容,作出很灿烂的样子,还依照“异性相吸”的道理,跑进男生楼,一下子销量猛增,我的业绩仍不是很好,狄云便跟我一起做,我看着她笑咪咪地柔声细语地和别人说话,心里惭愧的很。
到圣诞节那一天,每人手里的卡都只剩下几张了,就留着自己用,寄给同学了,我挑了两张漂亮的寄给了杨文和何宁,其他的则胡乱的寄掉了。
晚上的时候,我们跑到学校附近一家大的餐馆聚餐,彤云为此还拒绝了那个男生的邀请。餐馆外面有“圣诞老人”在迎送顾客,空中还挂着一个细长的圣诞老人,手脚一伸一缩,滑稽的很。化妆舞会里有音乐和吼声震耳欲聋,也是热烈的气氛。我们举起手中装有橙红液体的酒杯时说的是,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快放暑假的时候,学校里在办学生助理贷款的事,。吴叶问我,禾子,你贷不贷款?我说,不贷,我可以自己挣一些的,你要贷吗?她说,我怎么会贷?我用不着。我说,是啊,你怎么会贷?我想起了平时,她可是长向我们描述她家境的优越的,她说她家的房子是八角形的,家人非常地宠她,她曾经去过香港和中国的很多地方,她的一个叔叔送她的一支钢笔就值几千块钱,她说这些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沉默,不明白她何以要如此炫耀,不免给人浅薄的感觉,她见没反映,有点急,说,怎么,你们不信吗?我们便说,信,怎么不信。虽然我们从那支钢笔上无论怎么也看不出何以如此值钱。或者是买了衣服一定要我们帮她看看,说这是什么什么牌子的,要多少多少钱,后来有人说看见她在商场打折的时候买衣服。
有一次,她问我,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
我笑着问她是查户口的吗,那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
她说,我父母做的是秘密工作,不能告诉别人的。我听出她是在说笑,但心里有点反感,毕竟询问别人的家庭是一件不礼貌的事。
她家里给她打电话,她捂着话筒小声地说话,但我还是听见了一些,因为她是安徽人,方言比较好懂。似乎家里的人要她贷款,她不愿意。我觉得心里怪怪的,但又不好问。想起以前我们说到家人时,问谁有兄弟姐妹,她说没有,可后来她无意中说到她姐姐怎么样怎么样,我有些奇怪的问她,你不是独生女吗?她楞了一下说,我什么时候说过,一定是你听错了,我一直就说我有姐姐的。我说,哦,那可能是我听错了。
我出去做家教,走到校门的时候看到了吴叶,她和一个中年男人站在一个角落里,那个人面朝着我,看起来有些苍老,穿一件皱巴巴的衣服。吴叶东张西望,一转头看见我,连忙转过头去,象没看见我一样。我有些疑惑,又有些好笑,自顾自走了。
后来,回到寝室,她已经回来了,对我说,刚才在校门口我好象看见你了,隔的太远没叫你,那个人是我的老乡,因为见过几次面,这次他们有点事想找我帮忙。我说,哦。她说你不信啊?我说,我信啊,干吗不信,你没必要向我解释的,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她说,我怕你误会。我说,我误会什么,有什么好误会。她不语了。
第二天,她把我叫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还未开口,就哭了起来。我问她,她也不说。我急了,说你在不说,我就走了。
她这才说,禾子,我妈妈生病了。
我说,严不严重,要不要回去看看?
她说,住院还缺一笔钱。停了停,又说,禾子,你家境不好,这我是知道的,最近我们家出了事,经济也很钧捆,跟你是同命相连。
我说,我那里钱不多,但我可以帮你向同学借。
她说,不,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说,你这又何必呢,你母亲病了这么大的事情,你又何必掩藏呢?
她说,你不知道,有的事你不知道。
我说,我什么不知道,我什么都知道。
她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我说,你不就是怕别人看不起你吗?一个人家庭出生有那么重要吗?你家里没钱难道就是耻辱吗?我告诉你吧,没人会看不起你,除了你自己。
她呆呆地站着,我说,还站着干什么呢,救你妈要紧啊。
后来我们向院里申请了一笔临时助学金,给她母亲交了住院费。在病房里,我看到了她的母亲,一个头发花白的瘦弱的妇人,她看女儿的眼神带着歉疚,好象生病是她的错一样。她的床边还站这一个人,就是那天来找吴叶的那个人,不说我也知道,他是她的父亲。我问过了吴叶,她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