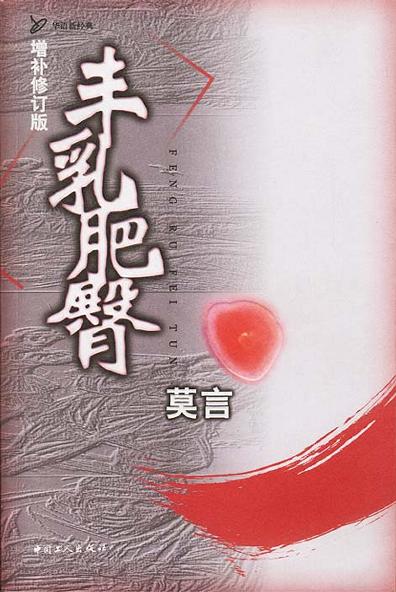莫言丰乳肥臀 重见天日-第7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走进院子,他说:“这是干什么?不就死了个半截子废物嘛!是我打死的。” 公员人员把上官来弟和鸟儿韩铐走了。 五个月后,一个女公安送来一个瘦得像病猫一样的男孩。并转告母亲,上官来弟第二天上午将被枪决,家属可以去收尸,如果不收尸,就送到医院解剖。女公安还告诉母亲,鸟儿韩被判处无期徒刑,不久即将押赴服刑地,服刑地点在塔里木盆地,距离高密东北乡有万里之遥,起解前,家属可以去探视一次。 上官金童因为撞伤了学校的小树,已被开除学籍。沙枣花因为有偷盗行为,被茂腔剧团开除回家。 母亲说:“我们要去收尸。” 沙枣花说:“姥姥,算了,别去了。” 母亲摇摇头,说:“她犯的是一枪之罪,没犯千刀万剐的罪。” 枪毙上官来弟那天,观众足有一万人。一辆囚车把她拉到断魂桥边,车上,同案犯鸟儿韩陪着游街。为了防止罪犯胡说八道,执法人员用一种特制的刑具,封住了他们的嘴巴。 上官来弟被枪毙后不久,上官家又接到一张报告鸟儿韩死讯的通知书。他在被押赴服刑地旅途中,企图跳车逃跑,被火车轮子轧成了两半。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第四十一章
为了开垦高密东北乡那上万亩荒草甸子,大栏镇的青年男女,统统被吸收为国营蛟龙河农场的农业职工。分配工作那天,场部办公室主任问我:“你,有什么特长?”因为饥饿,我的耳朵里嗡嗡响,没听清他的话。他噘了一下嘴唇,露出一颗镶在嘴巴中央的不锈钢牙齿。提高了嗓门他又一次问:“有什么特长?”我想起了刚才在路上,看到了挑着一担大粪的霍丽娜老师,她曾夸奖我有俄语天才。于是我说:“我俄语很好。”“俄语?”办公室主任冷笑着,炫耀着那颗钢牙,嘲讽道,“好到什么程度?能给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当翻译吗?能翻译中苏会谈公报吗?小伙子,我们这里,留苏学生都在挑大粪,你的俄语能好过他们吗?”等待分配的青工们发出嗤嗤的冷笑。“我问你在家里干过什么?干什么干得最好?”“我在家放过羊,放羊放得最好。”“对,”主人冷笑着说,“这才叫特长,什么俄语呀,法语呀,英语日语意大利语,统统的没用。”他匆匆写了一张条子,递给我,说:“到畜牧队去报到,找马队长,让她分配你具体工作。” 路上,一个老职工告诉我,马队长名叫马瑞莲,是农场场长李杜的老婆,响当当的第一夫人。我拿着条子,背着铺盖去报到时,她正在种畜场指挥着一场破天荒的杂交试验。种畜场的院子里,拴着一头发情的母牛、一头发情的母驴、一只发情的绵羊、一头发情的母猪、一只发情的家免。配种站的五个工作人员——两男三女——都穿着雪白的大褂、捂着遮住鼻子嘴巴的大口罩,戴着|乳胶手套的手里,都端着一具授精器,好像五个严阵以待的冲锋队员。马瑞莲留着一个半男半女的大分头,头发粗得像马鬃一样。一张红彤彤的大圆脸,长长的细眯的双眼、肥大的红鼻子、丰满的大嘴、脖子粗短、胸脯宽阔,沉甸甸的Ru房宛若两座坟墓。——混蛋!上官金童暗骂了一句,什么马瑞莲,这不是上官盼弟嘛!因为我们上官家臭名远扬,她竟然改换了名字。由此类推,那李杜,就是鲁立人,他曾叫蒋立人,也许在蒋立人之前,还叫过x立人,Y立人。这一对改名换姓的夫妻,被贬到这偏远之地、看来也是一对倒霉蛋——她穿着一件俄罗斯花布短袖衬衣,一条像豆腐皮一样、皱皱巴巴、哆哆嗦嗦的黑色凡尔丁裤子,脚蹬一双高腰回力球鞋。她指头缝里夹着一支跃进牌香烟,缕缕青烟缭绕着胡萝卜一样的手指。她抽了一口烟,问:“场报记者来了没有? ”“来了,”一个戴着近视眼镜、面容枯黄的中年人从拴马桩后闪出来,哈着腰说,“来啦。”他手里拿着拧开帽的自来水笔和打开的笔记本,笔尖按在纸上,随时准备记录。马队长响亮地笑着,用那只胖嘟嘟的手,拍了拍中年人的肩膀,说,“主编亲自出马啦!”中年人道:“马队长这儿,是出头条新闻的地方,别人来,我不放心。”“老于,很有积极性嘛!”马瑞莲赞扬着,又一次用她的手,拍了那主编的肩头,主编小脸煞白,像怕冷一样,紧紧地缩着脖子。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编辑着八开对折油印小报姓于名正的中年人,曾经是省委机关报的社长兼总编辑,一个大名鼎鼎的右派。“今天,”马瑞莲说,“我真要给你一个头条新闻。”她深情地望了文质彬彬的于正一眼,把手中的烟卷儿滋滋地吸到烧痛嘴唇的程度,然后“啪”地一声吐出去,让烟纸和残余的烟丝分离——她这一手绝活,会把捡烟头的人气死——她喷吐着最后一口青烟,问配种员们:“都准备好了吗?”配种员们举起配种器,无声地回答着她的问题。血液涌上她的脸,她搓着手,激动不安地拍了拍巴掌,然后又掏出—条手绢擦了擦手上的汗水。“马精,谁是马精? ”她大声地问。那个端着马的Jing液的配种员往前跨了一步,声音在口罩里显得窝窝囊囊。“我是,我是马精。”马瑞莲指指那头牛,说:“你去给它,那头母牛,把马精授进去。”配种员迟疑着,他看看马瑞莲,又看看身后那四位同行,好像要说什么话。马瑞莲道:“还站着干什么?干这种事儿,趁热打铁才能成功!”配种员眼里流露出恶作剧的神情,他大声说:“马队长,我遵命!”配种员捧着装有马Jing液的授精器,飞快地跑到母牛背后。当那配种员把器具插入母牛的产道时,马瑞莲的嘴巴半张着,呼呼地喘着粗气,好像那一管子马精不是授给母牛而是授给了她。然后,她干净利索地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她命令牛的精子去包围绵羊的卵子。她让绵羊的精子和家免的卵子结合。在她的指挥下,驴的Jing液射进了猪的子宫,猪的Jing液则冤冤相报般地射进了驴的生殖器官。 场报主编的脸灰溜溜的,嘴巴咧着,很难说他是想放声大哭还是想放声大笑。一个女配种员,端着绵羊Jing液的那一位,她的睫毛弯曲着,眼睛不大,但黑亮无比,几乎没有多少眼白。她拒绝执行马瑞莲的命令,把配种器扔在搪瓷托盘里,摘下手套,拉下口罩,露出她的汗毛很重的上唇、白皙的鼻子、和线条优美的下巴,愤怒地说:“简直是恶作剧!”她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声音清脆悦耳。 “放肆!”马瑞莲双手拍出一声脆响,流沙一样的目光撒到女配种员的脸上,她阴沉沉地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戴的”她用手做了一个摘帽子的姿势 ,“不是‘手提帽’,你是极右派,是属于永久性的、永远摘不掉帽子的右派,对不对?!”女配种员的脖子像经了严霜的草茎,脑袋无力地垂在脑前,她回答道:“您说的对,我是极右派,永久性的。但是,我想,这是两码事,科学和政治,是两码事,政治可以翻云覆雨,可以朝秦暮楚,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但科学却是严肃的。”“住嘴!”马瑞莲像一台疯狂的锅驼机,空咚空咚跳动着,喊叫,“我决不允许你在我的种畜场里,继续放毒。你也配谈政治?你知道政治姓什么?你知道政治吃什么?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脱离了政治的科学就不是科学,在无产阶级的辞典里,从来就没有超阶级的科学。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科学,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科学。”“如果无产阶级的科学,”女配种员孤注一掷地、大声地打断马瑞莲的话,“如果无产阶级的的科学硬要逼着绵羊和家免交配并期望着产生新的物种,那么我说,这无产阶级的科学就是一堆臭狗屎!” “乔其莎,你太狂妄了!”马瑞莲牙齿打着颤说,“你抬头看看这天,你低头看看这地,你应该知道天高地厚!你竟敢说无产阶级的科学是臭狗屎,反动透顶啊!单凭这一句话,就可以把你关进监狱,甚至枪毙!看你这么年轻,漂亮,”上官盼弟变成的马瑞莲降低了调门说,“我放你一马,但是,你必须给我把授精任务完成!否则,我可不管你是什么医学院校花还是农学院的校草,那匹蹄子比脸盆还大的种马我都制服了,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 场报主编规劝道:“小乔,听马队长的吧,这毕竟是科学实验嘛,人家天津郊区,把棉花嫁接到梧桐上,水稻嫁接到芦苇上,都获得了成功,《人民日报》白纸黑字登着呢!这是一个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时代,是一个创造人间奇迹的时代,既然马和驴交配能生出骡子,谁又能担保绵羊和家兔交配不会产生新的畜类呢?听话,去吧。” 医学院校花、极右派学生乔其莎脸涨得通红,委屈的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她执拗地说:“不,我不,这违背基本常识!” 场报主编道:“小乔,你好糊涂啊!” “不糊涂就打不成极右派了!”场报主编对乔其莎的关切显然引起了马瑞莲的不满,她冷冷地顶了他一句。 场报主编立刻垂下头,不吱声了。 一个男配种员走上来,说:“马队长,我替她做吧。甭说是把绵羊的Jing液射进家兔的子宫,就是把李杜场长的Jing液射进母猪的子宫,我也丝毫不为难。” 配种员们怪笑起来,场报主编伪装咳嗽才避免了笑出声音。马瑞莲恼羞成怒,骂道:“混蛋,邓加荣,你太过分了!” 那个邓加荣,拉下口罩,显出一张无法无天的马脸,冷冷地说:“马队长,本人既没有手提帽也没有永久帽。本人家三代矿工,根红苗正,你可别用吓唬小乔的一套来吓唬我。” 邓加荣说完,扬长而去。马瑞莲把满肚皮鸟气全撒在乔其莎身上:“你,干不干?不干的话,这个月的粮票我可要全部扣发了。” 乔其莎憋着,憋着,终于憋不住了,眼泪连串成行地滚出,嘴巴里也发出了哭声。她裸手拿起配种器,跌跌撞撞地跑到发情母免前——那兔子颜色青紫,脖了上拴着一根红绳——按住了它,它扑扑楞楞地挣扎着。 这时,上官盼弟变成的马瑞莲终于看到了我,冷漠地问:“你来干什么?”我把场部办公室主任的条子递过去。她看看条子,说:“到养鸡场去吧,那儿正缺一个干重活的壮工。”她不再理我,对主编说:“老于,回去发稿吧,稿子嘛,留有余地吧。”主编哈腰道:“到时请您看小样。”她又对乔其莎说:“乔其莎,根据你的请求,同意你调离配种站。你收拾收拾,去养鸡场报到。”最后,她对我说:“你怎么还不走?”我说:“我不知道去鸡场的路。”她抬手看看腕上的表,说:“走吧,我正要去鸡场办事,顺便把你带过去。” 远远望得见鸡场用石灰刷得雪白的墙壁时,她停下了。这是紧靠废旧枪炮场的、通向鸡场的泥泞小路,路边的小沟里,汪着一些暗红色的污水。在那片用铁丝网拦起来的空地上,狂长的野篙子淹没了破烂坦克的履带。坦克的红锈斑斑的炮筒子凄凉地指向蓝天。牵牛花的嫩绿色的藤蔓,缠绕着一门高射炮断了半截的炮管。一只蜻蜓立在高射机枪的枪筒上。老鼠在坦克的炮塔里跑动。麻雀在加农炮粗大的炮筒里安家落户,生儿育女;它们叼着翠绿色的虫子飞进炮筒。一个头上扎着红绸蝴蝶结的女孩坐在炮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