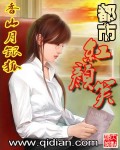漂泊红颜-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时我就买一大串香蕉扔在车里,饿了就剥一根吃。中午大家都回来了,余阳在厨房主勺,汪虹打下手兼进行英语会话,我躺在客厅沙发里养神儿。经常有这样的情况:饭刚吃了一半儿,甚至刚刚端上桌,电话来了,客户要货,放下碗就得走。晚上对我们来说是最轻松的时候,吃罢饭,喝过茶,如果有兴致的话就开车出去玩儿——去酒吧喝酒,去夜总会看表演,或者去卡西诺试试运气,写意得很。
有一天我回来得早,他们俩都不在。有些无聊,便去汪虹屋里想找本书看。随手翻开一本捷克语教材——她正在努力学捷语——见里面夹着一张写着中文的纸,原来是汪虹的姐夫写给她的便条。
汪虹:
我今天就要去德国了,把账跟你清一下。
1,你去荷比卢德法时留下的20件砂洗衬衣我已经卖掉,是220克郎一件卖的。扣除你的成本2000克郎,共得利润2400克郎。按我们事先的约定,我拿走1200克郎。
2,电话费单已到,共2870克郎。电话我打的比你大概略多一些,因此我们按55%对45%这样的比例分摊,你应该交12915克郎。扣除你的应得利润1200克郎,你仍欠我91。5克郎。
3,房东来收房租,三个月共15000克郎,我只住了一个半月,按分摊原则,我应交纳3750克郎,替你交了11250克郎。
4,你共欠我11341。5克郎,请你按今天的牌价27:1付给我美元,我要给你姐寄回去。
一人在外,要多注意身体,我们都非常惦记你。
姐夫
1993年10月23日
我想起当初汪虹听到我说不收房钱饭钱时的惊愕表情。
大家在一起朝夕相处,余阳的气嗓子渐渐改了不少——不能一天到晚贱兮兮的呀。我们的话题愈来愈丰富——对于我来说,每一个在海外闯荡的中国人的经历都是一部传奇,我极其渴望知道他们的故事。如今汪虹就在身边,我断定她一定有不少有趣儿的故事。她并不爱多说话,除非你循循善诱,挑起有意思的话头儿。
在这方面我是强项。
我一点一点地知道了她的全部故事。
她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天津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母亲是一家大厂的高级工程师。她上边儿只有一个姐姐,大学毕业后留校教书。一家四口儿,倒也其乐融融。
汪虹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分配到卫生局工作,抄抄写写。后来又调到一个区级法院,在民事庭做书记员。
“用‘诸事不顺’来形容我在国内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她对我说。
先说工作,她在法院和一位女同事共享一个办公室,这位女同事和庭长关系有点暧昧,庭长有事没事总往这屋里跑,俩人眉来眼去,打情骂俏,也不避讳汪虹。汪虹这人死性得很,属于那种南北巷口不知道拐弯儿的人。她看着烦,没少顶撞她。结果是庭长整天给她脸子看,她还不知道为什么呢。
有一天,她刚从财务科领工资回来,正要点,走廊里有人喊她。她随手把工资往抽屉里一放,出去了。
五分钟后回来,钱没了。
办公室里就她和那位女同事,她认定是这女人偷了她的钱,大吵大闹,让她把钱交出来。
女同事本来就不是善茬儿,哭喊着给庭长打了电话。
庭长气冲冲地来了,责问汪虹有什么证据说她偷了钱?
汪虹说:“办公室就俩人,我只出去了五分钟,又没有人来过,你也没来过,不是她是谁?”
庭长一拍桌子:“胡说八道!这能算证据吗?我还说你根本就没往抽屉里放过钱呢!”
汪虹也一拍桌子:“你才胡说八道!你为什么这样护着她?为什么?你说!”
来看热闹的人都捂着嘴笑,一位女审判员眼尖,看见那女人的坤包儿拉链儿上卡着一截儿工资条儿,便大声说:“哟,你的工资条儿卡在拉链儿上了。”
实际是给汪虹提个醒儿。
汪虹也莽撞,一步跨到那女人面前,劈手夺过坤包儿,拉开拉链儿。
正是汪虹的工资,一分不少。
从此,她在法院也不能呆了。
原因是她过去的个人生活。在卫生局工作时,她爱上了一个小伙子,那个小伙子也爱她。她怀孕了,小伙子却要结婚了——有人给他介绍了局长的女儿。
那年她23岁。
她痛不欲生,但也无可奈何,在母亲和姐姐的陪同下去医院做了人工流产。
卫生局不能呆了——局长就不同意。父母多方求人送礼,又正赶上公、检、法扩编,调进了法院。
但如今法院也呆不住了——那女人不知从哪儿把汪虹这件丢人事儿给打听出来了,在法院是逢人便讲,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
好在她还有个从未谋面的大姑。
她给大姑写了一封信。
1991年1月,她收到了大姑寄来的邀请书。她欣喜若狂,几年存下的郁闷污浊之气一朝尽吐。
在当时的中国,出国发展还是一件很新鲜的事。那时办护照光有邀请书不行,还必须有单位证明。她去法院开证明,全院立刻轰动了。与她熟悉的和不熟悉的,要好的和不要好的,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来向她表示祝贺——连庭长也来了。
她成了院里的焦点人物。
1991年10月1日,国庆节,她告别送行的朋友,怀揣800美金,带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
从此天涯孤旅!
那时苏联虽然还在,但已经危在旦夕。一个多月以前,苏联的部分共产党人为了挽救苏联及其社会主义理念,出于对戈尔巴乔夫的严重不满,发动了著名的8。19政变,软禁了戈尔巴乔夫,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并宣布接管国家政权。可惜民心向背今已非昨,叶利钦登高一呼,军民响应。不过三天,政变失败,戈尔巴乔夫重回克里姆林宫。此君受了党内同志一惊,余悸犹存,立刻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继而叶利钦又宣布俄共为非法组织,明令取缔。此时的苏联政局正是一片混乱,父母都为汪虹担心,劝她推迟行期,看看再说。但她执意不肯。年轻和勇气使她无所畏惧,她以为前程必定似锦,却未料只有荆棘丛生;她以为从此坦途通天,却未料崎岖坎坷,跋涉艰难——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她的包厢里还有三位旅伴:一位蓝姓北京姑娘,是要从莫斯科转道匈牙利的。她的男朋友在那边做生意,要她去助一臂之力。另两位是先生,一高一矮,高个儿姓李,矮个儿姓卢,供职于北京一家外贸公司,此番去莫斯科洽谈贸易。旅途寂寞,大家自然比平时亲切几分。车到二连浩特,彼此已经熟悉得如同朋友一般。
二连浩特是列车在中国境内的最后一站,距北京有一夜的车程。这是一个边陲小镇,属于内蒙古自治区。不仅全体旅客要在此查验护照签证,列车也要在此换车轮。汪虹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听说火车还要换轱辘,新鲜得很。李先生见多识广,便给她讲起原委:
在19世纪40年代,有一位美国铁路工程师到俄罗斯来访问。他建议沙皇政府修铁路时采用宽轨,并列举了一大堆宽轨的好处,预言全世界很快都会采用宽轨。还举了一个例子——人在喝醉酒时是并住腿站得稳还是叉开腿站得稳?
俄罗斯盛产醉鬼,这个例子有极强的说服力。
在以后的年代里,俄国人不止一次地希望当初没有轻信这位美国工程师的话。
全世界都使用窄轨,只有俄国和蒙古——它实际上的附属国,铁路也是由俄国人修建的——使用宽轨。
汪虹把这个故事记到了本子上。
换轱辘需要两个小时,大家都下车到站台上散步。进入十月的内蒙古已经颇有点凉意了,汪虹穿着毛衣犹不觉暖,又披了一件风衣,先在站台上的售货亭里买了一张印有国门照片的明信片,坐在候车大厅的长椅上,以膝为桌,匆匆写了几行字——
爸爸、妈妈、姐姐:
我已到达边境小镇二连浩特,现在列车正在换轱辘——没听说过吧?过一会儿就要走出国门了,就是明信片上这个大门洞。
那边就是蒙古。
在国内总给家里添乱,总让你们操心,好在这回出国了,新生活已经在我面前展开,我会成功的。
汪虹
1991年10月2日
她看了一遍,把明信片扔进了邮筒。
列车再次开动,缓缓地驶出了国门。可是才开了十分八分,又停下了。看看外面,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落。老李告诉她,这里叫扎门乌德,是蒙古的一个小镇。蒙古的海关和边防检查站都设在这里。
果然,列车刚刚停稳,蒙古海关和边检人员便上了车。礼貌还说得过去,用蹩脚的英语问声好,然后就查验护照。可你把护照递给他,他并不看,眼珠子光盯着你的行李。当时这趟车上也有不少中国人带货——当然比不上随即到来的国际大贩运——又穷又贪的蒙古海关和边检人员已经开始尝到了甜头。但汪虹这个包厢没人带货,边检人员看看没油水可捞,便开口了,对汪虹说:
“大大!”
汪虹不明白什么意思,还以为护照有问题呢。还是外贸人员见多识广,卢先生说:“孙子问你要泡泡糖呢!”
汪虹笑了,用英语说:“我没有口香糖。”
“香烟。”
他见没有口香糖,又用标准的中文说出了“香烟”。怕汪虹听不懂,还把两根指头放在唇边,做吸烟状。
汪虹烦了,她无法想象一个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竟无耻到这种地步,刚想发作,卢先生递过来一包万宝路,那边检接过装进口袋,竖起大拇指,又是一句中文:
“好朋友。”
拿着护照下车了。
汪虹说:“怎么都成叫花子了?”
大家就苦笑。
三分钟不到,那小子又上来了,发还盖好入境章的护照,倒麻利。又朝送他烟的卢先生笑笑,用大拇指比划打火的动作——这小子还想要个打火机!
卢先生没辙儿,从衣袋里摸出个打火机递给他。
他接了打火机笑眯眯地刚想走,汪虹把他叫住了,用英语对他说:“你们当年真不该离开中国,中国什么都有。”
他耸耸肩,用英语回答:“这不是我的责任。”
走了。
与汪虹不久就会碰到的俄罗斯、罗马尼亚海关边检人员相比,这小子简直就是个道德君子。
列车很快启动,随即加速,辽阔的蒙古高原扑面而来。
第四章 心痛的感觉
与内蒙古相比,这里更空旷、更辽阔也更荒凉。在内蒙古境内你可以经常看到村落、炊烟、牛羊,这里什么都没有——除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老李问汪虹:“你刚才对那小子说你们为什么要离开中国,我也听说这里以前是中国领土,具体是怎么回事儿你知道吗?”
汪虹说:“这是一段离我们很近的历史,是出于种种原因不被提起的国耻。”汪虹在大学里是历史课代表,这回轮到她娓娓道来了:
清朝初年的时候,朝廷为了便于管理,便把蒙古分为三部分,即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漠南就是今天的内蒙古,漠北漠西就是这里。那时候,清政府在库伦,就是现在的乌兰巴托派驻大臣,定期举行针对沙皇俄国的军事演习。因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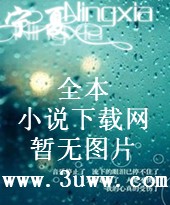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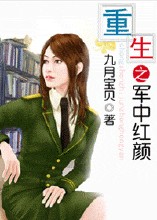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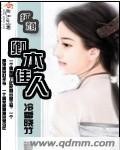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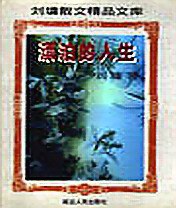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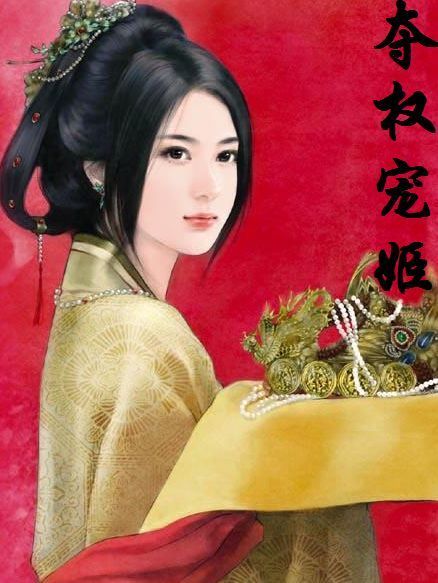
![[星宿x柳宿]重生之红颜忆柳封面](http://www.xxdzs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