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青空之蓝 作者:沧月-第5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心思单纯,毫无戒备,闲谈间,便被他用几句话将家世全套了出来。
原来,这个少女是个贫苦的中州人家的孩子,从四年前起就在落珠港的这个码头上干活儿。然而,这些年来她渐渐长大,出落得越来越美丽,在鱼龙混杂的码头上抛头露面的干活儿,难免惹出事非。这一次,便是被一个来船上提货的商人调戏,这个烈性的少女一怒之下居然操起扁担,毫不客气的将对方打落到了水里。若不是他偶然经过,这个丫头便要被一群奴仆和码头监工狠狠地教训一顿。
“哎呀,看来以后每天来上工之前,要用灶灰把脸抹花了才行!”她一边喝着面汤,一边皱着眉,“这些臭男人!”
他听着,不知道怎么接她的话,只是觉得她的声音如此悦耳动人,一颦一笑都如清水出芙蓉一般,比他看到过的任何女孩子都美丽。
她喝完了汤,便准备回家。他毫不犹豫的把随身携带的伞送给了她,虽然这把伞价值上千铢,是父亲用皇帝御赐的流云纱裁了衣服后的余料做的。她显然不知道这把伞色贵重之处,只是看着上面如青空般变幻不定的流云纹赞叹:“真好看阿!谢谢你拉!”
他看着她撑着伞走入那条雨巷怔了片刻,忽的回过神来,再也顾不得什么,追上了几步,大声喊道:“等。。。。等一下!”
“还有什么是?”她有些惊讶地站住身。
“我。。。我。。。”他站在街上淋着雨,却不知道说什么好,心跳得很快,脸上热的厉害。他知道自己的脸肯定变了色,然而越想要镇定下来,却越是慌乱,完全不像是十岁就被严厉的父亲称为“吾家千里驹也”的天才少年。
“哑巴了么?”她等了片刻,惊讶地看着这个张口结舌的少年,笑了一下,转过身去,“不管你了,我可要回家去给爹娘弟妹们做饭了!”
眼看她又要离开,他终于结结巴巴的说出了一句话:“那。。。那我明天请你吃面,好不好?”
她笑了笑,“嗯”了一声。
那一瞬,他心里仿佛有一只小鹿跳了一下,狂喜轰然而啦,几乎忍不住手舞足蹈起来。
看到他失态的模样,她笑了笑,转身走了几步,忽然回头一笑:“我叫安堇然。你呢?”
安堇然,安堇然。一个多么宁静美好的名字,从此仿佛烙印般刻在了他心上,成为他心里永远难忘的一道伤痕,腐烂了,见骨了,痊愈了,却永难抹去。
那时候,她十七岁,他十八岁。
那时,我忍住了冲到嘴边的话,犹豫了一下,却回答道:“我叫慕。。。慕少游。”
十年后,他依旧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回答,用谎言遮盖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或许,从小被父亲以权谋之道训导长大的他,即使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轰然而至的真爱,内心里还是无法放下戒备吧?
毕竟,在这座城市里,他的身份太特殊。
那一天后,他便认识了她。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很短暂,从相识到分别也不过六七月,从白帝八年的晚春四月到深秋十月。
然而,这样短短的一段时光,却成了他之后十年里最难忘的记忆,其中掺杂着太多复杂的情绪:青涩、朦胧、甜蜜、担忧、忐忑和憧憬。
对于他来说,少年时的成长和蜕变,都完成于那短短的半年时光。
从那一天起,每天他都在落珠港的码头等她放工,看着斜阳下,那个纤细的身影卸下沉重的担子,从长而软的跳板上轻盈的走下来,快步奔向他高高兴兴地一起离开。
她的身世和他天差地别。她年纪虽小,家累却重,每天在码头做完工后只能休息一会儿,便要匆匆赶回家去给父母弟妹烧水做饭,打理家务,等一直忙到了晚上,侍候父亲休息,弟妹安睡,还要出门去做另一份工,忙到凌晨才能回家。
所以每一日,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时辰。
那一个时辰里,他们所做的和一般的恋人无异,不过是一起吃吃东西,逛逛大街,不着边际的说一些话,要么就是牵手走在叶城的海滩上,静静的看着大海发呆。然而,即便是在这样无关风月和欲望的静默相处里,即便只是坐在她的身边什么也不做,他的心里依旧能感觉到罕有的平静和温暖。
他们虽然日渐亲密,却并非无话不说。她很少对他说起自己家里的事,正如他也很少对她提起自己的情况一样,偶尔,在点数一天挑担赚来的铜子的时,她会叹气,说父亲的病逐日加重,已经卧床不起。而母亲带着一堆弟妹,每天都等着她赚钱回去买米下锅,如果不快点儿找一个能赚更多的钱的营生,估计就供不上一家人的吃穿用度了。说话的时候她秀丽的双眉紧蹙着,每个铜子都数的分外小心。
他心里“咯噔”了一下,手在口袋里动了动,却是不敢将怀里满把的金珠掏出来。如果。。。如果堇然知道了自己的身份,会怎么样?
与当时的她相比,他的心思显然更加复杂。少年老成的他始终顾虑重重,怯于对意中人说明自己的心意和身份。他不仅是担心幕布一旦揭开,两人之间的巨大落差便会令她远离自己,更是担心除了门当户对的巨族外,其他女子爱上的往往不是他的人,而是慕容家的权势和富贵。
他不敢揭开谜底,生怕真相是自己无法承受的。
他一直举棋不定,为他们之间的未来而忧心忡忡。而她是那样聪明的人,应该是看出了他有所隐瞒,却始终不曾开口询问。
秋天来时,他做了一件最大胆的事:他没有参加镇国公府举办的海皇祭宴会,从一群王室贵族中间逃了出来,带着她翻过了检查的关卡,划船去黑石礁上看大潮。
潮来的时候,天地一片苍茫,充满了造化洪荒的力量,令所有人都觉出了自身的渺小和生命的未可知。她和她缩在黑石礁上,相互依偎着,风卷起的浪溅湿了他们的衣衫,脚下的岩石在巨浪里颤抖,潮头上龙舟竞驰,船头有人在歌舞。
“少游!快看,彩虹!”她惊喜万分地喊着,指给他看大潮背后那一轮淡淡的落日苍茫的雾气下面,闪动着江海的光芒。潮水如一堵墙一样升起来,高达数十丈,日光透过蒙蒙的水汽,居然幻化出了一道晶莹璀璨的彩虹来,就悬在他们的头顶不远处。
“看啊!”她欢喜的像个孩子,伸出手去触摸那尽在咫尺的彩虹。
他却没有看彩虹,只是出神地看着身边的少女。她那美丽绝伦的容颜,即便在彩虹在依然不曾逊色半分美得令人忘记了一切那一瞬他忽然下了人生最大的一次决心:无论面前横亘着怎样的困难,他都要永远的抓住这个女子,要和他永远在一起。
就在她伸出手去抓住那道彩虹的时候,他忍不住俯身轻轻吻了一下她的侧脸。她身子一僵,脸色瞬间飞红,却有迅速苍白了。
“堇然,我们要永远在一起。”他低声道,许下了人生的第一个诺言。
然而,她没有回答。她伸出去触摸彩虹的手僵在空气里,脸色很是奇怪。下一个瞬间,大浪呼啸而来,拍击在礁石上巨大的浪潮在他们头顶散开,笼罩下来,仿佛是一场盛大无比的流星雨。
“永远?”水雾弥漫了视线,他看不见她的脸,只隐约听到她轻轻叹息了一声,“永远到底有多远呢少游?”
“多远?”他凝望着海天之间。“就如海皇苏摩对白璎的心意,生死无阻。”
水雾漫天而来,视线一片模糊。白茫茫一片的礁石上,他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自己面颊上轻轻一碰少女的嘴唇柔软而冰凉,带着轻微的颤抖。
那是他的第一个吻,也是她的第一个。那一瞬间,他仿佛被雷电击中了。“堇然?”他满怀喜悦地伸出手去,然而却落空了。
当视线重新清晰起来的时候,他发现身边的礁石上空无一人,只有滔天大浪从南方天际一波波地袭来,仿佛巨大的白色莲花盛开在周身。而片刻前还在自己身侧的少女,就这样凭空消失了,仿佛幻化在了彩虹里。
“堇然!”他惊骇万分,对着苍茫大海呼喊,“堇然!”
她去了哪里?是掉进大海了么?被潮水卷走了么?
他发了疯一样地呼喊着她的名字,在礁石上四处寻找,甚至跳下大海在风浪里寻觅。然而,她却仿佛是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丝毫痕迹。贵族少年在大海里游着,呼喊着,直到筋疲力尽无法动弹。最后一刻,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任凭幽蓝色的海水在他头顶闭合
几乎溺毙的他侥幸被一艘路过的龙船救起,送回了岸上。然而,也就是从那天起,她却永远从他的生命里消息了,宛如那一道乍现又转瞬消息的彩虹。
变故陡生,一切戛然而止。
他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做了什么那段时间,他将叶城翻了底朝天,甚至出动了镇国公府的所有力量,却始终没有任何她的消息。
那个名叫安堇然的贫苦少女,仿佛忽然间从云荒上消失了。
少年时的他经不起这样突如其来的打击,一度消沉颓废,甚至几次有轻生和出家的念头,如果不是父母拼死阻拦,说不定如今的他早已跟随那个名叫孔雀明王的游方和尚皈依了中州人的佛祖。
然而两年后,在他心口的伤痕渐渐结痂的时候,她却突然又回来了。
从新出现在叶城的她,却拥有了一个他无法相信的身份:青楼的花魁。乌黑的粗辫子解散了,梳成了精致华美的蝉影髻,粗布衣裳变成了精美的鲛陗。甚至,她连名字都换了殷夜来,多么旖旎风情的名字阿,一如她那妩媚的眼波。 。
她已经完全不像她了,然而,他却还是在第一眼的时候就把他认了出来。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探问她的来历,有人说她是个当红的优伶,因为帝都禁止在唱中州戏了,所以不得不转头青楼。
然而他却是知道那不是真的在他认识她的时候,她不是青楼女子,也不是当红优伶,只是一个在落珠港码头上挑担子养家的贫苦少女。
然而那样的往昔,除了他,无人知晓。
他也去过她所在的星海云庭很多次,她有时候会出来见客,有时候会托病不出,对他的态度和别的恩客没什么两样。她的态度如此自若,以至于他有时候会有一种恍惚感,觉得昔年那一段青涩、模糊的初恋并不曾发生过,只不过似乎南柯一梦。
十年后,他在码头上递给她的那把伞还握在同一只手里,然而却已是物是人非。
那两年,她到底去做了什么?为什么会不告而别?为什么又会变成如今这样?是为了钱么?是因为他没有更早地表明自己的身份,掏出满把的金珠来么?
他始终未曾找到机会问他一句为什么。直到今天她忽然来访,身为城主的他终于摘下了面具,失控的问了出那些话。然而问了又如何呢?只换来一句更令人不堪的回答“是啊。。。如果当时你告诉我拟真正的身份,大概,一切会不同了吧?”
她居然就这样坦然承认了,嘴角带着微微的笑。
果然母亲的教导是对的:世上的女人,爱的无不是他的身份和金钱,或许还有他的皮囊。至于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一颗什么样的心,又有谁会在意呢?
也就是她再度出现的那一瞬开始,他的心才终于死了吧?
慕容隽踱回了梅轩,桌上的茶盏犹温。
他坐在方才她坐过的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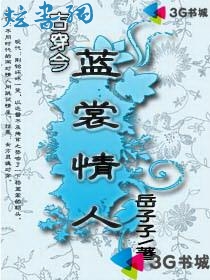
![(黑蓝同人)望见青空[青黄]封面](http://www.xxdzs2.com/cover/noimg.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