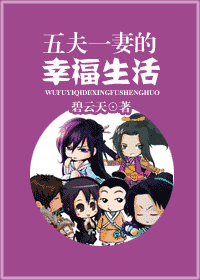你死,我活-第5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阿柯怒火烧心,拿身旁这武功深不可测的家伙毫无办法,只得恨恨地转过头去不理他。他呆呆的出了一阵子神,终于长叹一声,挣扎着爬起来要走。辩机忽然叫道:“阿柯。”
“”阿柯不理。
“那是块邪物。”
“你说过了,和尚!”阿柯拍拍屁股,打算走人了。
“这十几年来,为着争夺这阴阳铜鉴而死的武林人士,少说也有六七十人。这还只是有名有姓,被人确认死于此铜鉴的,其余无名小卒,或不明不白死在荒郊野外的更不计其数。”
阿柯跨出一步,脸色忽然煞白。他站着不动了。
辩机坐起身子,罕见的脸上没了笑容,有一丝淡淡的忧虑自那双清澈的眸子里发散出来。他叼着草根,慢慢地道:“天下真有那么便宜的事么,拿出铜鉴,便能谴人为你卖命?嘿嘿,痴人梦语而已铜鉴不过是个幌子,谁真想要换条命,还得拿值一条命的东西去换才行。”
阿柯呆了一呆,脱口道:“若若是没有这么贵重的东西呢?”
辩机嘿嘿一笑,道:“你真是傻那自然就得拿自己的命去换!段兄将那铜鉴交给我时,说它邪气太重,叫我毁了它。嘿嘿,人的贪欲是那么容易毁得了的么”
阿柯猛地一扑,一拳正中辩机胸口,忽感着手处辩机肌肤一缩,这一拳的力道刹时消失得无影无踪。阿柯收扎不住,合身撞到辩机身上,两人一起倒在草丛中。阿柯拼命一争,劈面一个耳刮子过去,叫道:“死和尚,你害死可可,我跟你拼了!”
辩机双手一送,阿柯顿时腾起老高,夹在老柳树两个枝干之间。他张口要骂,这才感到全身麻痹,不知什么时候已被辩机封了穴道,连声音也发不出来,只有涨红了脸,眼睁睁看着树下的辩机好整已歇的站起身,整整衣裳,哈哈一笑,道:“什么邪物!只不过一块普普通通的铜佩罢了,却无辜被人的欲念玷污。看那位小妹妹的举动,‘杀人’二字恐怕终日都在心中如火般烧着,即便没有这铜鉴,也会有同样的银鉴、金鉴,或者随便什么薄如绢纸一般的机会,让她动手。你认为是害了她,又怎知道她心里,就如同无数想要得到这铜鉴的人一样,欣喜若狂呢?痴人,痴人,人心中的铜鉴,又岂是我能毁掉的?段兄痴人呐!”
长笑声中,身形晃动,并不见他如何动作,已如鬼魂一般飘飘忽忽飞入林中,消失不见了——
第二十章毒发
林芑云坐在厅中,背靠着西域进贡纹金驼毛枕,怀里揣着暖壶,脚上盖着细软绒毯,端着茶杯,两眼呆滞,百无聊赖的看着四五个丫鬟小厮在院中打扫庭路,整理花草树木。身旁的青铜镂空麒麟香炉里,上等檀香的清烟如雾,衬着她锦袍上的藏青纹路如梦一般流动。八扇朱红厅门全部大开,周遭的窗户也被支了起来。下人们沿着窗子,一字排开摆上十几盆名贵花卉,什么杏黄兜兰、卷丹、红枫等,甚至还有两盆极品鹤望兰。冬日里少有的暖暖的阳光照进窗来,一道道光拄中,无数浮尘起起落落,倒也煞是好看。
但林芑云的眼光依旧呆滞。
有一种奇怪的、枯涩的、如牛在呜咽的难听至极的声音,始终高亢激昂的自后院传来,象锉刀一样死命折磨着她的耳朵。因为这声音,整整一个上午,林芑云都沉浸在一种莫名的烦躁之中,害她心不在焉被暖壶烫了几次手。
铛铛还没有出来。哎,看样子,今日午时之前,李洛都不会停止学习吹萧了。
林芑云现下还真颇有些后悔提议让李洛自己学萧,作为进献皇帝的戏目。当初自己是怎么说的“晾将军之才情,纵无宫廷技师之技艺,然忠君之心,上必嘉之”万万没有想到,李洛这家伙武功高强,于这音律方面却简直七窍开了六窍一窍不通!那舞剑弄抢时出神入化的十根手指,按到萧上却如僵硬一般,明明该动小指,他偏偏动食指,待得要动食指了,却又痉挛似的五指齐伸;他那张大口一接触萧口,无论怎么百宝使尽,吹出的总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呜咽之声
真是不知道铛铛的耐心从哪里来的,就李洛这个样子缠着练了这么多日子了,一点也未见长进,她竟也一点也未见厌烦,仍旧那么浅浅的笑着,手把手的指点他笨拙的姿势林大小姐坐在一旁观看,倒好几次怒从心起,拍桌子厉声质问姓李的是真不知道还是在装糊涂耍宝?吵了几次,被铛铛好说歹说劝走。到长亭观河,她嫌河风冷;有人陪着观戏,她又嫌闷得慌,转来转去,还是只有回来,在大厅里呆鸟一样坐着。
阿柯这个名字象暗夜里的微风一样,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肆无忌惮的掠过她的心里,一些酸的甜的苦的思绪就那样跟着翻腾起来,再也挥之不去。林芑云常常呆坐一个晌午,脑子里走马灯般,各种景象层出不穷,却都是一些往常里从未在意过的阿柯又摔了一交偷吃东西时被自己当场抓住每当被阿柯背着,那窄小的肩膀散发出浓浓的少年的气息那个时候,他歪着嘴,嘟嘟啷啷说什么来着
“林姑娘!”
“哐啷!”
“哎哎哟!烫烫!啊!烫啊!”
刚刚进来的秦管家变了脸色,惊恐的看着林芑云一边惨叫一边拼命抖落泼在怀里的茶水,愣了一愣,方慌乱的叫道:“快!来人啊,林姑娘的茶小玉、小红,快来啊!”
待得一阵乱哄哄收拾妥当,林大小姐躺回靠椅时,面色苍白,大冷的天,她那光洁白嫩的脸上也出了一层细细的汗。她颤抖着用一张丝巾慢慢地擦拭,过了好半响,才咕哝一声:“什什么事呀,秦管家?”
秦管家神色尴尬,一迭声的抱歉。林芑云定了神,挥手道:“好了,好了,不跟你相关的,是阿是我自己走了神了。你急着赶来,什么事啊?”
“是,小人孟浪了,还请林姑娘别介意小人急着赶来,原是给姑娘您报信的您要找的精通内功的医者,已经找到了!”
“哦?”林芑云眼皮一跳,坐起身子。但也只“哦”了一声。
“呵呵,说起来您还认识的,小豆子说,就是上次您昏厥时,他在大门口遇见的那位神医啊。”
林芑云神色凄然,道:“那一次吗哎,自我哥走后我已记不住了。”
秦管家在背后偷偷一掐大腿,暗自懊悔怎么这么没记性,硬要提林大小姐的伤心事。他咳嗽一声,含混的带过去,道:“是,此人姓道,自称岭南人士。俱小人明访暗查,此人刚来洛阳不久,但似乎医术不错,在城南李家楼一带设点行医。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此人好似内家功夫不错,日前在飘雨楼与人斗力,小人亲眼见他用一只小酒杯嵌入楼顶横梁之中,这份功夫当真厉害。这才赶紧着请他来府,让林姑娘过过目,看是否合适治疗您的腿伤。”
林芑云心道:“总算是来了!”却不露声色,凝眉不语。秦管家不知这位玲珑心思永不可猜的大小姐又在想什么花样,只有试探着问:“那位道大夫已在外门等候多时了,姑娘先见见?”
林芑云沉默半响,重重叹一口气,方道:“算了,我是早已死了这份心了,难为秦管家还记得这一个多月来,前后来了总有十几位大夫了吧?个个都说得天花乱坠,李将军一试,却是统统不济事,白花了几十两答谢银子,也劳累秦管家了。我这腿病,说大不大,什么药理药方的,我自己也配得,就是需要一位懂医术,又通内功的人来顺脉通气本来李将军功夫是没问题的,偏偏又不懂医,我也是过于小心了,就怕一个不好,运气走岔了经脉,反到坏了事哎,这位八成也是唬人的,秦管家别当了真,请他走吧。终究我这一辈子,是躺在椅子上的命了”说到后来,眼圈一红,娇弱无边,低头不语了。
秦管家一张老脸上满是羞惭之色,搓手顿脚地道:“哪里话,林姑娘这是说的哪里话?小人拼着这条老命,也是要为林姑娘请来名医的几个银子算什么?人好歹来了,是真是假看了再说可好?林姑娘?”
林芑云磨蹭半天,似经不住秦管家一再请求,低声道:“即如此,我也不用看了,就劳烦秦管家先领他去见见李将军,若是内力还行,再说吧”
秦管家见劝动林芑云,心中大喜,忙不迭的答应着出去了。林芑云乐得让他们忙活去,这一下精神也大爽了,唤了丫鬟们来,将躺椅浩浩荡荡抬到后花园里去,指手画脚的安排小厮整理花木去了。
过了一盅茶的功夫,只听院子外人声喧哗,李洛带头走进来,引着身后一人,满面春风,招呼道:“林姑娘!可把大夫找到了,来来来,替你引见这位道名医。”
当道亦僧道貌岸然自李洛身后转出来时,林芑云险些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忙垂下脸,装头痛掩饰过去。但见道名医一系青衣大褂,头戴一顶布帽,倒也干净整洁,只不过体形太胖,将那身本已算是宽大的衣服也撑得浑圆饱满。他一脸肃穆,络腮胡子也刻意修剪,只剩颚下一溜寸长的胡须。他操着蹩脚的八方步,一步一停地跺进来,“恩哼”一声,四平八稳的打量一周,一捻胡子,沈声道:“病人在哪里?”
“咳咳咳”林芑云终于实在忍耐不住,放声大咳起来。铛铛飞也似跑过去,背着众人给林芑云又打又擂,勉强忍着笑道:“我姐姐哎,身子不好,大夫见晾了!”
※※※
阿柯那日傍晚时分才松开穴道,费老大力从树上下来。他这两日接二连三给人当猴耍一般封了穴又解,解了又封的,已是精疲力竭,再也没有力气,当晚就在段念夫妇坟前随便找了个草堆睡下。
夜里,阿柯妖梦入怀,只觉自己已将林芑云杀了,按照约定结庐而居,为她守护。梦里白雾茫茫,他有些不知所措的望着浓雾另一头的孤坟,仿佛在咫尺间,却又仿佛隔着永不可及的距离。忽而那坟上长出一棵槐树,枝繁叶茂。他有些慌乱的抬头看上去,见有一道、两道无数道阳光从树冠空隙之见透射下来,待得再低下头来,那坟已不见了,原先的地上开遍了野花,象无数的眼睛,在风中迷乱的眨着。风里充满熟悉的味道,数不清的跳动的白色的光点在身边萦绕。阿柯心想林芑云呢林芑云呢,但眼皮似有千斤重般睁不开,只有用手四处摸索。忽然间,他摸到一个软软的温暖的躯体,他正想着,是谁呢是谁呢,就听见那人幽幽开了口,道:“每年槐花开的时候,我的心就乱了”
阿柯兀的一惊,小真是小真。他想收回手,但小真一反手,已将他牢牢抓住,按在自己温暖得似要将人融化的胸口,轻轻地道阿柯你不理我了么阿柯你不要我了么。阿柯说不是的不是的,我在找人啊那人孤身一人很可怜她怕黑怕静怕老虎我要赶紧着找到啊
就这样一挣,小真松了手,阿柯一屁股坐在地上。好在眼睛终于又睁开,阿柯四处望望,什么地方啊树也没有了花也没有坟也没有了,只有黑的山黑的石黑黑的木头桩子。阿柯觉得四周冰冷刺骨,肚子一阵阵的打雷似的响。他明白过来,今天应该已是第三日了吧,伯伯已经回去了,妈妈,妈妈就要送吃的来了,他想,有吃的就好啊。他舔舔干燥的嘴唇,耐心的听著有脚步声自那黑暗中一步步靠近,靠近
突然间,伯伯的手如鬼魅般一把抓上他的肩头,暴怒道:“为什么




![同性婚姻合法之后,我们离了[娱乐圈]封面](http://www.xxdzs2.com/cover/1/122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