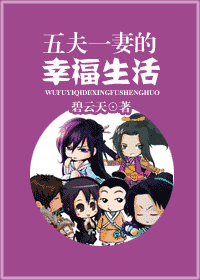你死,我活-第5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拿石头砸了我两次头,我都没避开,知道是为什么吗?”
阿柯心中烦闷,此时正是看谁谁不顺眼的时候,便道:“我哪知道?想是你正在练什么铁头功、秃头功之类,谁砸你脑袋,你都暗自高兴吧。”
辩机微微一笑,道:“非也,非也。乃是因为你都是用心砸的。对于别人用心做的事,无论是什么样的,好的也罢,坏的也罢,在我眼中都是一样带着一股淡淡的香气,弥漫在天地之间,动人心魄而且我也很好奇,想要看看隐藏在后面的心究竟是怎样的?”
阿柯恼道:“和尚,你失心疯了么?这穷山僻壤的,哪儿来的什么花香?又什么用心不用心?别、别人用心拿刀子杀你,你是不是也开心得很?”
辩机道:“开心吗?我不知道。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认真要杀我。或许真有人要我命的时候,我会开心也说不定。”
阿柯道:“废话少说,快做场法事来看看。”
辩机摇头道:“不会。”
阿柯道:“你不是和尚吗?法事都不会做,那化缘、念经这些你会不会?”
辩机道:“你说对了,我不是和尚。刚才我已经跟你说了”
“是是是,你只是碰巧脑袋是秃的,而且又碰巧有几个戒疤,根本与和尚无关,是吧?”阿柯抢白道。
辩机回过身来,头一次正视阿柯的眼睛。他依旧笑容款款,一双眸子精光四射。凛冽的寒风呼啸着刮过他身边,吹得他的长袖列列做响,他却象根石柱般纹丝不动。阿柯隐隐觉得,寒风刮到辩机面前时,竟似自动一转,从他身旁掠过一般凭什么吹到自己身上时就吹得这么带劲?
“你牛个什么劲?”他忍不住傻傻地问“好象风都怕了你?”
辩机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饶有兴致地打量着阿柯,似乎见到一件极为有趣的事。
阿柯给他一双缝眼看得老大不自在,道:“看什么?”
辩机道:“没什么只是在好奇如此平顺的一个人,何以突然间变得如此张扬而愤世忌俗了。”
阿柯眉毛一挑,想要说什么,怔了一怔,却又转过头去,向可可叫道:“可可,收拾一下,我们走了。”
可可道:“谁说要跟你走?你不是说要分么?”转身便走。阿柯忙道:“我我你的东西还没拿走!哎哟!”挣扎一动,牵动内伤,痛得眼前一黑,只得重新坐倒。
可可停下脚步,道:“是了,还有我的东西。昨日被你这混蛋气昏头了,竟然就那么走了,险些便宜了你。东西呢,在哪儿?”
阿柯道:“都在牛车上,我系在山上了。快,我们找找去。”
可可道:“就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想走路么?和尚,劳你照看他一下。”
阿柯怒道:“为什么要他照顾?我、我不要再看到他!”
辩机笑道:“小兄弟还在为我昨日那声断喝生气呢。呵呵,无论我喝与不喝,段夫人已然油尽灯枯,继续挣扎着说下去,对她实在是一种折磨。死后万事皆空,这样的只言片语,又有何用呢?”
可可没由来突然想起段夫人死的时候,脸上神情古怪。似乎欢乐与痛苦同时混杂在内。晶莹醍透的眼珠一转,刹那间,犹如一屡淡淡的青雾蒙了上去,段夫人的脸的轮廓就那样再也看不分明了。她心中一颤,不言语了。
阿柯紧皱着眉,脑海内似有千言万语翻腾,却偏偏找不到一句可以驳斥辩机的话,心中一阵凄惶。呆了片刻,终于脱口说道:“不公!”
“是,不公。”辩机毫不犹豫地接口道:“只是你想过没有,这是段夫人与段念自己造就的不公,所以,他们可算是死得其所了。”
“什么?”
辩机悠然看着天边的云层,脸上露出些许神往的神情,慢慢地道:“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正是如此的不公,如此的死亡才造就了段夫人。若非如此,段夫人也不是段夫人了。”
阿柯听得莫名其妙,抓抓脑门,刚要开口骂他脑袋是不是有问题,眼角一瞥,见到了那座孤坟。矮矮的,凹凸不平的坟头,就象大地上一块无谓的突起,若不是那一圈黄黄白白的石块,谁也不会留意它的存在。新鲜的坟头一片荒芜,咧咧的寒风也拿它毫无办法。或则来年,待野草开始再那地底深处探出头来时,才有一丝活力吧。他心中突然地一痛,那股暴虐之气刹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无尽惆怅。他叹了一口气,觉得这些口舌之争再可笑不过,便住了口。
辩机看着阿柯的脸,因见到他神色忽然暗淡下来,会心的一笑。阿柯再不去理他,对可可招手道:“来,我们一起去找牛车。我我记得我拴在一棵树旁的。”可可看着阿柯的眼睛,愣了片刻,终于不言声的走过来,扶起他,两人费力向前走去。
辩机道:“喂,阿柯,段夫人死前对你说的话,你明白了吗?”
阿柯头也不回地道:“我听见了,自会去办。”他对辩机和尚面对段夫人死时那轻松的态度耿耿于怀,虽然自己心里也知道那是他做和尚的本色,但不知为何,始终是难以压制的愤怒,只想赶紧离开,眼不见心不烦。
辩机笑道:“你听是听见了,可又明不明白呢?段夫人的女儿叫什么?”
辩机此时的笑声在阿柯听来格外放肆,胸口顿时堵得难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可道:“好象是什么王家的,叫王什么。后面可没听清楚了。”
辩机道:“自然是王家的,苏州王家。武林三大家族之一的苏州王家。嘿嘿,可不是姓段的。”
阿柯听见他言语中对段念大为不敬,勃然大怒,回头喝道:“臭和尚,你想怎么样!我大嫂说得清清楚楚,叫王姓王?”
阿柯一口气吼得大了,内息波动,头脑发晕,几乎跌倒。他扶着可可喘息一下,叫道:“和尚,你知道什么?说出来!”
辩机走到一棵歪脖柳树前,抬头望着那千丝万缕的长须直垂到地面,慢慢道:“你的这位大嫂段夫人,原本应是王夫人才对。天下武林本来公认的是四大家族,十几年前,四川唐门因鬼手大侠揭穿了一件公案,渐渐退出江湖,而让王家坐了三家族之首。她原是王府大公子王镜的妻子,她的女儿自然也是这位王镜的。”
阿柯张大了嘴,一时说不出话来。可可道:“啊,难怪姓王。我听见那个沙老大威胁段夫人的时候,好象就提到了她女儿,也提到了王府。”
辩机道:“正是。她自己本姓芩,十六岁就嫁到了王府,那个时候,段兄还在漠北征战呢。”
可可扶着阿柯坐下,问道:“那么说,段夫人是从夫家逃出来的咯?他的丈夫呢?难道就这么忍气吞声,不出来追她吗?你们汉人对这婚嫁之事,可看得很重啊。”
辩机道:“怎会没有?只是段兄的‘鬼影刀’,却是他们比不了的。在下在长安时,就听说王家的人潜伏在山东一带,准备截杀。结果四十几人围攻段兄一人,竟硬是被他二人突围而出,还送了二十几条人命,天下震动。段兄武功固然高强,却有一点致命之处,那就是太轻信人了,不知道人心难测,滥交朋友。昨日那位沙老大,就曾是段兄的坐上之宾,称兄道弟。还有那位给段夫人下毒的‘飞斧帮’帮主,段兄得势之时,与之一道出生入死,拼命拼来的交情,被王家稍加引诱,就下了黑手,嘿嘿,嘿嘿,当真是生死之交。在下日夜兼程赶来,就是想提醒段兄,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唉”
阿柯听到他说这番话,似乎对段念不可谓不关心,心中稍平,刚要开口,却见辩机面带微笑,道:“这大概就是天吧,呵呵。天意如何,终究人力不可违之。下次可不能做这类傻事了。”说着连连摇头,检讨自己。
阿柯一句安慰的话到了嘴边,出口已变成怒骂:“什么叫天意不可违?救人的事,就叫做傻事吗?臭和尚你到底是不是人呐!”就要合身扑上。
可可在后面轻轻一推,阿柯“哎哟”一声摔倒在地,爬不起来。可可道:“你急什么,听人家把话说完呀。就你这身体了,还想多添几处伤是不是?”
辩机依旧一脸灿烂的微笑,毫不动容,道:“在下说过几次了,我不是和尚,下次可要记住了。”
可可道:“是,记住了。和哎,你刚才说段夫哎,王夫人的夫家王镜,后来怎样了?”
阿柯拿手使劲拍地,道:“什么王夫人?段夫人!”
辩机道:“王镜么,他自小身子虚弱,生有绝症,在他们女儿出世后一个多月,就病死了。”
可可“啊”的一声,跟着叹道:“原来王夫人是独身多年了。”
阿柯怒道:“什么王夫人?段夫人!”
可可恼道:“你讲不讲理?人家以前没遇到段大哥时是王夫人啊。大恩你、你接着讲啊,别理他。王夫人又是怎么见到段大哥的?”
辩机道:“这个嘛,在下就不太清楚了。只隐约听说,在王老爷子五十七岁寿辰那天,段兄也应邀参加。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遇见王夫人的。两个月之后,王夫人便被秘密关入王家祠堂,严加看管。嘿嘿,嘿嘿,这两个人还真是干柴烈火,一点就着。”
阿柯深深吸了一口气,双手撑地,费力地站起身来。他面色铁青,却看不出气急败坏的样子,甚至有些怜惜地看着辩机,并不言语。辩机原本嘻嘻笑着,与阿柯对望一阵。慢慢的,他的眼中神色闪烁,脸也僵硬下来。
可可见两人都是木着脸对视,深怕阿柯又扑将上去,忙跳起身来,拦在两人中间,道:“和哎呀,辩大哥,你快讲,那段大哥又是怎么把王夫人救出去的?”
辩机“哦”的一声,转过头,有些心不在焉地把玩垂在他面前的柳树根须,道:“那那就更不清楚了。段兄十天之后就与王夫人一道逃出了祠堂,千里流亡去了。这种事,他们关中铁刀盟守口如瓶,旁人又怎会轻易知道。我曾听说关中铁刀盟规矩甚严,若有人犯了帮规,重到无可挽回的地步时,无论是帮主也好,长老也好,一率要服下一种密传毒药,赶出帮门。武林三大帮派,铁刀、飞剑、玲珑枪,嘿嘿,铁刀盟十数年来都是稳坐的头把交椅,这次破门而出,段兄可说是五十年来江湖中被废了的身份最高的人了。”
可可道:“毒药?段大哥并没有立即死,那是手下留情了?”
辩机回头看一眼可可,重又恢复笑容,道:“嘿嘿,小妹妹,你真是善良。可惜啊,人乃最无情之生灵,特别是对所谓大逆之人,更是心狠。段兄为着王夫人,甘愿舍弃帮主身份,让天下人耻笑,铁刀盟中,早视段兄为无耻叛徒,又怎会手下留情呢?那毒药虽不致命,却比要人命的更为恶毒,除了让人功力损耗大半外,更深入全身经脉要害,每半月一次发作,一会儿是钻心之痒,让人神志癫狂,直抓得全身上下鲜血淋漓,无一处不是伤痕;一会儿又痛彻入骨,似乎四肢骨骼统统折断一般,当真是生不如死。这毒名字叫做‘忘俗’。忘俗,忘俗,当年炮制这药的前辈,还真是取了个名字呢。”
他笑得轻松,可可只觉一股寒气打腰间直入背脊,混身一个激灵,颤声道:“好狠的毒”随即又想到自己身上的‘石素散’,脸色更是变得苍白。
辩机倒没注意到可可脸色不善,叹道:“可惜,这位老前辈取这个名字时,只怕从未想到,即便这般凶残的




![同性婚姻合法之后,我们离了[娱乐圈]封面](http://www.xxdzs2.com/cover/1/122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