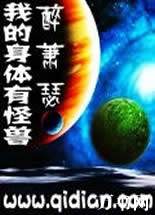谁的身体-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将不懂事的吐回去。她眼睛雾蒙蒙地转着两颗大露珠,满是怨恨。
小石不愿再和米燕作伴,每日赶在娃群前头,赶母牛及两头牛崽上山,当然不是离得很远,远到还辩认得出娃群和米燕为止,并能观察他们的行动,也让米燕可以看见他,比如隔一个岗,离一个坡。娃子们倒乐,不和他们作伴,省得受威慑。
其实,小石挺孤独的,只是他认不得这个词,说不出孤独来。静坐之时,地气抽上来,山里温度骤然而降,那边的笑闹飘荡如歌,他掏出小玩艺儿揉搓,米燕就躺下面了,接下去便重演梦中的情景。不过,他不知道这个叫手淫。
这都是我当初想不到的,山娃子在性方面照样羞涩,或者说恐惧。更想不到的还在下面,小石简直玩蛇成癖,一看见蛇在草间游动,他就激动不已,捉了蛇,左右一晃,伸直手臂,稍稍抖动,做一些小动作,蛇就扭出无数美妙的曲线在眼前,以至于缠上手臂,作盘龙状。小石地地道道是一个野蛮的蛇郎。
这村子的娃子与另一村子的娃子,时常相遇,隔着山头,莫名其妙就骂起来,这边凸肚子作孕妇状,垂手捏住小玩艺儿虚拉出去,再用力吐一口痰,喊:
×你妈妈。
那边也以同样的姿态喊:×你姥姥。
互相往上溯,直×得祖宗十八代头皮发胀,不过瘾,干脆冲过去撕打,以发发其攻击欲。碰到这场面,小石手中的蛇就大有用场了,每每扯衣服揪耳朵踢屁股最激烈的时候,他懵懵懂懂潜回战场,甩开蛇成一根鞭子,不问青红皂白一一鞭去,娃子们看见打到身上的是蛇,吓得魂不附体鬼哭狼嚎仓皇而逃。
剩下小石一人,高高立着木愣,听哭嚎声渐渐消失在山后,嘴角绽一些含意深刻的笑纹,右脚后退做成马步,手臂飞速地旋几旋,心满意足地把蛇扔出去,蛇在空中转几道弧,很快落到坡下,成一条僵尸。
七
玩蛇的事还没有了结,娃子们回去告状,小石阿爸先是红了脸,继而不动声色,叫过小石,厉声道:
“跪下。”
小石不跪,竖立着,合上眼皮。
小石阿爸又喝道:“你跪不跪。”
小石不理睬,掉头欲走。
老头儿着了火,一把扭过小石,按倒在地,弓身一阵拳擂,小石倒地上既不挣扎也不叫喊,默默忍受父亲的拳头击到身体的各个部位,一点感觉也没有。小石母亲见没有动静,以为打坏了,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拉扯着:“小石他爸,饶他一次吧,人谁不犯错,改了就是了,那么大的人还用得着你打。”因为小石没有反应,小石他爸打得乏味,加上他妈的恳求也就将就放了,小石慢慢爬起,拍拍灰尘,冷冷说:
“不打了?”
这一问,老头儿半天说不出话来,可谓气极语咽,最后一字一顿学着小石的腔调:“不——打——了?”说完急急去寻了麻绳,将小石推进房间,五花绑上,走到门口回头沙哑道:“不会走,先学飞,看你犟到哪里去。”随即将门“砰”地狠声锁上。
房间里墨黑一团,角落老鼠刷刷地啮咬着板壁。小石静立着,用心体味着被父亲拳击过的部位,隐隐的酸痛。这时候除了酸痛,一无所有,体内的某种东西潜伏下来,不再折腾得他浑身奇痒,怪舒服的,甚至忘了自己是被绑着,竟想跳跃起来,痛和快的组合实在太恰当不过了。梦遗以来的恐惧被父亲打得干干净净,不留痕迹。他不再害怕米燕,米燕还是老样子,是他的堂妹他的隔壁邻居他童年的老婆,他大可以一如既往又抓又摸的。
门外脚步响连着几声咳嗽,有邻居进来,老头儿连声说:
“坐、坐、坐。”
“小石玩蛇了。”是米燕他爹的声音。
“没说的,阿叔,孽种迟早害了自己,也害别人。”
“蛇是神物,真玩不得。”
米燕他爹咳嗽几声,接着又重复讲起蛇精的故事。大意是一个老头上山砍柴,碰到一条蛇精,蛇精强行要娶老头的女儿当老婆,否则就要吃掉老头。这故事小石听了一千遍,早听厌了,但这时听起来却又别有滋味,他一字不漏地听着,想想自己整日上山捉蛇着实害怕,再想想并未捉着一条会说话的蛇,又放了心。
不一会,隔壁传来凄切的暗泣声,小石吃了一惊,细听是米燕在哭,抽泣声到唇边被手捂着,很低沉,一阵紧似一阵,一阵比一阵短促,并伴有手指抓草席的擦擦声和鼻孔倒吸鼻涕的淅淅声,小石仿佛知道哭声与他有关,只觉得心往下掉,渐渐地抽泣声盖过讲古,在暗中放大起来,如紧锣密鼓,在他脑海里回荡。他真想过去捏住她的鼻子说:别哭,别哭,有我呢。一抽身,发现自己让绳子绑着,动弹不得。绳子在身上扭来扭去有点紧,如蛇。转而想叫一声米燕,让她知道他就在身边,并没有被打坏。等真要叫,却又犹豫了,即便是低低的只有自己听得见,拼足勇气,叫到嘴边,还是哽住。
隔壁的哽咽传过来。
八
小石上山,还是老样子,跟米燕隔一个岗,离一个坡。
可是母牛发情了。
娃子们叫叫崽,叫崽就叫崽,母牛垂着泛白的泡沫,仰头四望“妈妈妈”地呼唤,并打喷嚏奋小蹄去寻去年的情种。小石挥舞竹爪,在后猛追,母牛越发奔得快,一跃一跃的,简直是马。呼叫声一路不断,满山满谷热烈地回应着,娃子们耳里就全都是母牛叫崽的声音。
那边米燕牧的黑牛牯,听到呼唤,也放弃青草扬蹄急急地赶来,米燕见状,也挥舞竹爪,在后猛追。其实她大可不必追赶,无非下意识学小石的动作,脚步由不得自己。山坡上便见一对男女莫名其妙地追赶两头发情的黄牛,大人若见了,肯定哈哈大笑的。
我得补叙一下,母牛叫崽,公牛本来得撕杀一场,这是自然界的规律,我相信公牛长着两只大角就是为了争夺母牛而生的。但小石喜爱米燕的黑牛牯,这家伙高大强壮,肩峰掣在脖颈上如一座山,真正的气势如牛,尽管有点儿老了,可干起母牛来老练自如,确也惹人喜爱。小石是看牛头,不仅管牛娃,还管母牛的配偶,所以黑牛牯就省去一场惊险的角斗,不斗而享有小石母牛的专利。
往年,母牛叫崽,他可乐了,命令娃子们牵住自家的牛牯免得过来捣乱,他和米燕将牛赶进僻静处,母牛翘尾巴等待,牛牯后退几步,一个俯冲,骑在母牛背上。他眼盯着,不禁手心大腿丫痒心里更咯咯痒,三下五除二,按倒一旁专心观看的米燕,滚作一堆。今年境况不同,他非但不乐,反而仇恨,挥舞竹爪猛追。两头牛碰面,正欲接嘴,小石挥起竹爪朝牛头一个劲狠抽,像弹棉花。牛头被抽到的地方很快勃起一溜儿一溜儿的爪痕,即便母牛再有耐性,也是经受不住的,只得掉头而逃。小石不解气,又追;黑牛牯不甘心,也追;米燕乱了方寸,不知自己在干什么,追。两头牛两个人,一队排开一个方向,追。灌木丛前面扑来又向后面弹去,一路啪啪地响,风呜呜地叫,小石越追越急,渐渐觉得自己在飞,两侧闪闪地流过绿的河流,脚下的灌木丛是一片绿云,他腾云驾雾,如覆平地。突然,他感到屁股眼让牛角挑着,急忙一侧身,公牛嘴正好顶住母牛的屁股眼,母牛一震颤,马上就不逃了,尾巴高高翘上是一杆旗。米燕迷迷糊糊的不知牛已停住,也一头撞上黑牛牯的屁股眼,一踉跄,摔了个四脚朝天。
小石见米燕躺着不动,心头一酸,不由自主地过去,拉了拉,咕噜道:“摔着了吗?”
米燕不回答,只拿眼定定地凝他,圆了嘴艰难地透气,小石亦拿眼定定地凝她,身子缓缓地瘫软下去,草木掩过头发。
慢慢地米燕平下气,忽然脸涨得透红,嘶声道:“逃呀,逃呀,你逃呀!”接着两眼汪汪地流下泪水,是两汪山泉,清亮地顺着冷却了的脸孔滚下。
小石心里一阵酸楚,张开双臂,拥过米燕,这回再不是梦中的幻影了。
事情就这么简单,身体一接触,恐惧就消失了,小石不再害怕,真的不怕。第一次激动过后,他探头察看山势,原来他们已经跑得很远,那边山脊静静的,没有娃子追来,阳光从山头上斜照下来,坡上的新叶浮着半层金黄,牛们在一旁摩耳擦鬓热乎乎流着牛泪,却很安详,大概早骑过背了。他心里一阵痒,回头趴到米燕身上,米燕也很安静,好奇地望着他,他抽手去解她的裤腰带,米燕脸上堆出一片绯红,一边呜噜着:“莫啊,莫啊。”双手挡住裤腰带,小石一个手指一个手指瓣开,米燕不再阻止,任小石摆布,并很严肃地望着上面的小石、灌木和枝叶间漏进的天空,枝条在身下折折地断裂。
小石屁股一撅一撅的,不学也会。枝叶的光影投到嫩嫩的屁股上,有规律地游动。米燕躺在下面,一动不动,忽然,“哇”地一声叫出来,带哭脸道:
“莫啊,莫啊,疼,疼。”
米燕弓起身子一看,吓得差点昏过去。自家的隐秘处毛茸茸的殷红一片,懵懵的不知怎么回事,慌得就哭了,看见小石一边呆着,像一段木头,赌气说:
“坏了,你赔。”
九
往后不难想象,一夜之后米燕不疼了,不过,不能不做出些女孩的矜持,一二日内不答理是必须的。早晨,小石在牛栏门前十分庄重地问:“还疼?”
“要你管?”
小石看她只是有点气,其他没什么异样,一头心事放下,忙着去赶牛。
春天赶牛上山,不像前面写的那样轻松,母牛一叫崽,牛队就不成样子了,娃子们一头一头监视,乱得团团转,嘴里老虎扒腿不要脸地乱骂一气,可母牛突屁股儿就是赖着不走,真是又可气又可笑。牛牯嗅到气味,一头一头拼命上前挤,好像只要舔一舔,死也值得。更要命的是不择地形角斗,平日豁达大度和平相处的牛啊,一下色迷心窍,结了九世冤仇似的,一见面就往死里斗,娃子们奈之何?竹爪挥舞得密不透风也无济无事。这地方坡陡壁深,牛牯脚一滑就没命,这些牛牯们十有八九是死在争夺母牛上。好在牛牯都是生产队公有的,死也就死了。春天,娃子们有的是牛肉吃。
米燕的黑牛牯就是这样死的。
黑牛牯死的那天下雨,云头俯到山脚,山上湿淋淋的,爬不得坐不得,娃子们没有去处,闷闷地正要回家。忽见阿旺家未开荤的处牛不吃草,在溪坪上转来转去,翘起尾巴妈妈叫,娃子们知道有戏看,雀叫着又叫崽喽,退一旁静观。
马上有米燕的黑牛牯和另一头黄牛牯横过来,两张嘴同时接住屁股眼,都想独占,各不相让,低头撞将起来,夹尾巴曲脊背正斗得欢,又一头趁机过来捞便宜,径直朝处牛背上爬,二牛一见渔翁得利,随即拆阵联合出击,直把那头撞得狼狈而逃,再赶上一边避去的处牛。争。这样,牛牯越斗越多,你斗一角,我追一步,全乱了套,一直随着处牛斗到坡上,诸牛牯只白拼了力气,谁也无法正式交配。
坡上滑,更有一丈多高岩背突着,险。娃子们本来该赶牛下山,但坡上湿,谁也不愿去,算了。况且摔下来也是活该,谁叫它们争着?
牛牯长久的相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