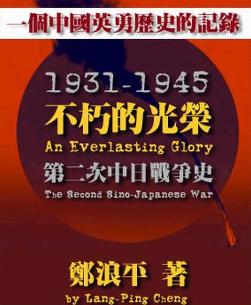第二类死亡-第5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小耿的腿,我怎么会认为是某个动物?然而,他们所有的人,的确都向动物般充满了攻击性,像鬼魅一样的暗藏着杀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让我害怕,我像惊弓之鸟,随时都会吓得跳起来,汗水出了一重又一重,整个上午,我都如坐针毡。
而全公司的人没有一个注意到我。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小耿,出什么事了?”我低声对小耿道,“大家好像都不对劲呢?”
小耿从我面前的桌子上拿起一块橡皮,却对我的话毫无反应,就好像没听到我在说什么一样。
就好像没有看到我一样。
我心中一沉。
余非说过,我们这种人,到了第三阶段的时候,就会被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莫非我已经到了第三阶段?这个想法让我感到无比绝望,我故意在人们面前走来走去要知道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现在,和他们每一次近距离接触,都让我感到由衷的恐惧。然而,即使是冒着这样大的恐惧,也丝毫没有收获没有任何人看到我。
他们果然都看不到我了。
我颓然地坐在地上,冷汗滴下来,地板砖上很快就变得湿漉漉的。我觉得头脑里轰隆隆直响,摇晃着站起来,在公司里搜寻了一遍,这才发觉,所有我用过的东西都已经不见了,原本属于我的办公桌上,也写上了别人的名字
公司里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他们的记忆里也没有我的位置了!
我飘一样离开了公司,飘飘荡荡地在街上走着,躲避着四周熙熙攘攘的人群,既害怕他们,又渴望他们。远远的,我看见爸爸妈妈提着大包小包从超市里走出来,我大声哭喊着朝他们跑过去,可是他们的眼光连扫也不朝我扫一样,我抱着他们的腿抱着他们的腿时,我全身都冒出了鸡皮疙瘩,那种感觉,就好像自己抱住的是什么凶狠的野兽,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恐惧,我仍旧紧抱着他们不放,将眼泪擦在他们身上,跪在他们面前,求他们看我一眼。
他们一个眼光也没有施舍给我,尽管我抱着他们的腿让他们行动艰难,他们却依旧朝前走着,丝毫不理会我,就好像我不是他们最心疼的女儿,就好像我只是一坨粘在他们鞋底的垃圾!
我终于被他们甩开了。
在人来人往的热闹街头,我嚎啕大哭,在地上打滚,将自己的衣服弄得肮脏无比反正我不需要顾及形象了,反正,没有任何人会看到我,没有任何人会在意我。
我持续不断地哭着,直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我叫醒。
是许小冰的声音,她在门外大声问道:“江聆,你怎么了?”
我慢慢地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在大声哭泣着,心头仿佛哽着一团铁块,盘绕着一种坚硬的痛楚,被子已经湿了很大一团。我有些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慢慢坐起来,看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之后,耳朵里听到许小比叫我的名字,感到异常亲切,又觉得无比轻松原来那只不过是个梦!
可是那个梦很快就会变成现实了!我忍不住又哭了起来。
“你快出来!”许小冰擂门擂得更凶了。
我没有理会她,独自哭了好一会之后,用被子擦干眼泪,这才起身打开了门。许小冰询问的脸出现在面前,我亲昵地拍了拍她的肩膀。她小心翼翼地看了看我:“你真的有些不对头,要不要我陪你去看医生?”
我摇了摇头。
我不光想拍她的肩头,还想像小猫一样蹭她的胳膊。忽然之间,能够与人亲密的接触也变成一种幸福,这种幸福在我手中,就像《驴皮记》里的那块驴皮,正越来越薄,薄得透出了亮光。
“我上班去了,有事打电话给我。”许小冰狐疑地看着我,慢慢退出了房门。
看看时间,我也该去上班了,但我一动也不想动,只是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发呆。
假如我永远也不去上班,是不是就永远也不会被人忘记?现在还来得及吗?我头脑里那个功能区,是不是已经将信号发送出去了?想到这个,我站了起来,蹬蹬蹬走到楼下,敲了敲202号房敞开的房门。
余非走了出来,仔细看了看我:“你找我?”
“功能区的信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出去的?”顾不上回答他的问题,我急忙问道。
“什么意思?”他疑惑地看着我,“你哭过?”
“我的意思是说,”我掠了掠额头上乱糟糟的刘海,“现在,我的功能区是不是已经开始发射信号了?”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他摇了摇头,“这一点他们现在还没有弄清楚,谁也说不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功能区就开始发射信号了。也许那些信号在你的潜伏期就已经发射出去了,也有可能更晚,但不会更早。没法确定你的信号现在是不是已经发出去了。”
“哦。”我点了点头,便自己上楼了。
“啊!”我大叫一声之后,连忙捂住了嘴,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四周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失态,他们很快又恢复了正常的站姿。
但我已经恐惧得无法自已。
我发现自己害怕的正是他们,这些包围着我的人们,他们身上有某些东西让我感到恐惧。
那是什么呢?
车子刚一停下来,我便迫不及待地下了车,整整走了两个多小时,才赶到了公司。
公司里的同事们都在埋头工作,我极力压抑住自己心头的恐惧,勉强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对面小耿的双腿从桌子底下伸过来,像树枝一样叉在我的桌子底下,让我胆战心惊,生怕碰倒这双让我害怕的某个动物的脚啊?这分明是小耿的腿,我怎么会认为是某个动物?然而,他们所有的人,的确都向动物般充满了攻击性,像鬼魅一样的暗藏着杀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让我害怕,我像惊弓之鸟,随时都会吓得跳起来,汗水出了一重又一重,整个上午,我都如坐针毡。
而全公司的人没有一个注意到我。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小耿,出什么事了?”我低声对小耿道,“大家好像都不对劲呢?”
小耿从我面前的桌子上拿起一块橡皮,却对我的话毫无反应,就好像没听到我在说什么一样。
就好像没有看到我一样。
我心中一沉。
余非说过,我们这种人,到了第三阶段的时候,就会被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莫非我已经到了第三阶段?这个想法让我感到无比绝望,我故意在人们面前走来走去要知道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现在,和他们每一次近距离接触,都让我感到由衷的恐惧。然而,即使是冒着这样大的恐惧,也丝毫没有收获没有任何人看到我。
他们果然都看不到我了。
我颓然地坐在地上,冷汗滴下来,地板砖上很快就变得湿漉漉的。我觉得头脑里轰隆隆直响,摇晃着站起来,在公司里搜寻了一遍,这才发觉,所有我用过的东西都已经不见了,原本属于我的办公桌上,也写上了别人的名字
公司里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他们的记忆里也没有我的位置了!
我飘一样离开了公司,飘飘荡荡地在街上走着,躲避着四周熙熙攘攘的人群,既害怕他们,又渴望他们。远远的,我看见爸爸妈妈提着大包小包从超市里走出来,我大声哭喊着朝他们跑过去,可是他们的眼光连扫也不朝我扫一样,我抱着他们的腿抱着他们的腿时,我全身都冒出了鸡皮疙瘩,那种感觉,就好像自己抱住的是什么凶狠的野兽,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恐惧,我仍旧紧抱着他们不放,将眼泪擦在他们身上,跪在他们面前,求他们看我一眼。
他们一个眼光也没有施舍给我,尽管我抱着他们的腿让他们行动艰难,他们却依旧朝前走着,丝毫不理会我,就好像我不是他们最心疼的女儿,就好像我只是一坨粘在他们鞋底的垃圾!
我终于被他们甩开了。
在人来人往的热闹街头,我嚎啕大哭,在地上打滚,将自己的衣服弄得肮脏无比反正我不需要顾及形象了,反正,没有任何人会看到我,没有任何人会在意我。
我持续不断地哭着,直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我叫醒。
是许小冰的声音,她在门外大声问道:“江聆,你怎么了?”
我慢慢地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在大声哭泣着,心头仿佛哽着一团铁块,盘绕着一种坚硬的痛楚,被子已经湿了很大一团。我有些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慢慢坐起来,看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之后,耳朵里听到许小比叫我的名字,感到异常亲切,又觉得无比轻松原来那只不过是个梦!
可是那个梦很快就会变成现实了!我忍不住又哭了起来。
“你快出来!”许小冰擂门擂得更凶了。
我没有理会她,独自哭了好一会之后,用被子擦干眼泪,这才起身打开了门。许小冰询问的脸出现在面前,我亲昵地拍了拍她的肩膀。她小心翼翼地看了看我:“你真的有些不对头,要不要我陪你去看医生?”
我摇了摇头。
我不光想拍她的肩头,还想像小猫一样蹭她的胳膊。忽然之间,能够与人亲密的接触也变成一种幸福,这种幸福在我手中,就像《驴皮记》里的那块驴皮,正越来越薄,薄得透出了亮光。
“我上班去了,有事打电话给我。”许小冰狐疑地看着我,慢慢退出了房门。
看看时间,我也该去上班了,但我一动也不想动,只是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发呆。
假如我永远也不去上班,是不是就永远也不会被人忘记?现在还来得及吗?我头脑里那个功能区,是不是已经将信号发送出去了?想到这个,我站了起来,蹬蹬蹬走到楼下,敲了敲202号房敞开的房门。
余非走了出来,仔细看了看我:“你找我?”
“功能区的信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出去的?”顾不上回答他的问题,我急忙问道。
“什么意思?”他疑惑地看着我,“你哭过?”
“我的意思是说,”我掠了掠额头上乱糟糟的刘海,“现在,我的功能区是不是已经开始发射信号了?”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他摇了摇头,“这一点他们现在还没有弄清楚,谁也说不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功能区就开始发射信号了。也许那些信号在你的潜伏期就已经发射出去了,也有可能更晚,但不会更早。没法确定你的信号现在是不是已经发出去了。”
“哦。”我点了点头,便自己上楼了。
33
一连好几天,我都没有去上班。我想,也许他们都还没有接收到我头脑里的信号,也许遗忘的机制还没有启动,只要我永远不和他们见面,他们就永远不会忘记我。在这几天里,陆续有人打电话过来问候,我一边接电话一边凄凉地想:也许今后,我就只能通过电话和网络与这个世界交往了。然而,这样也足够了,总比被人彻底遗忘更好。我像鸵鸟一样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除了许小冰和余非之外,谁也不见。欧阳曾经来过两次,他在门外大声地敲门,我都没有回答。
我最不想见到人,除了爸爸妈妈之外,就是他了。
越是靠近,就忘记得越快。当他敲门的时候,我害怕得发抖我不知道,门外和门内的距离,是否可以阻挡脑电波的穿越,所以我不仅仅关上了自己房间的门,还用棉被包住了脑袋,直到敲门声停止。
余非经常来看我,他常常坐在我身边,看着我抱着自己的身体,被一种强烈的思念所控制,像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