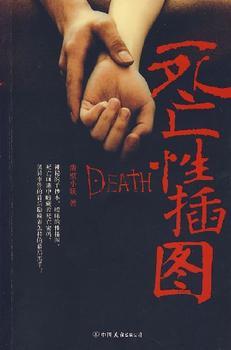死亡飞行-第5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榴霰弹。”我说。
慕尼兹微笑着,点了点头,“那个扔榴霰弹的海军陆战队员显得非常不安,他向我们道歉,并亲自为我包扎伤口。他原以为我们是日本人你们美国人对待我们要比日本人好一些。”
“慕尼兹先生”布迪说。
“萨美,我所有的朋友都叫我萨美。”
“好的,萨美,我想你知道,我们到这里是来调查艾米莉…埃尔哈特与她的领航员弗莱德…努南的下落的。很多像我这样的人来过这里,你们的很多岛民都有着不同的故事但是,每一个看起来都像是,二手货,我们需要目击者。”
慕尼兹叹了口气,沉思了半天时间,然后说:“布什先生”
“布迪。”
“布迪,我能够找到这样的人同你们交谈,但只是怕有些人不愿意谈,你搅起了塞班岛人对可怕的往事的回忆,岛上的每一个家庭几乎都在日本人占领期间失去过亲人。上百年来我们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以求逃脱惩罚,逃避报复。挺身而出,在公众面前做证,即使是现在,也是一件自找麻烦的事。”
“来自日本人的麻烦?”
他点了点头,“他们开始再次统治我们这座岛了——用另一种方式,那些冲撞他们的人会倒霉。而且,在战争期间,本地还有一个由查莫罗人组成的土著警察势力,专门为日本人效力,那些恶棍们折磨、拷打他们自己的同胞,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还活着。”
“像杰苏斯…萨伯兰?”我问。
慕尼兹很惊讶我居然知道这个名字,他眨了一下眼睛,说:“是的。”
“我听说很久以前他被人开枪打死了。”我说。
布迪瞪大了眼睛盯着我。
“这就是他为什么如此可怕的原因之一,”慕尼兹说,“那些枪并没有要他的命是的,他仍然活着,并且比十条毒蛇更邪恶。”
“他现在做什么?”我问。
“在废品收购公司。”
“沿街收购废品?”
“不!他在原水上飞机基地的旧址上开了一家旧货堆放、分类与出售的公司,他雇用查莫罗人收集废金属——丛林里到处都是战争的遗骸——把它们卖给日本人。”
那么说,这个“占哥凯丑”是一个破烂王了。
“他住在查兰…卡诺城外的一幢漂亮的小房子里,”慕尼兹说,“他喜欢独居。”
“他喜欢钱吗?”
“那是他最大的爱好,你对这个男人感兴趣吗,黑勒先生?”
“叫我内特,萨美。我只是听说他知道很多关于艾米莉…埃尔哈特与弗莱德…努南的事。”
慕尼兹兴致勃勃地点点头,“他们说他比岛上任何一个人知道得都要多,以前,他曾主动提出要谈论这些事。”
这对布迪显然是个新闻,“我从未与他交谈过。”
“其他人同他谈过,弗莱德…高尔纳,葛维斯少校,但没有人付过杰苏斯索要的价钱”
我喝了一口可乐,“你能给我们安排一次会见吗?”
“他不会同时会见一个以上的人,曾经有一次,几个男人袭击了他——一个在二战期间居住在戈瑞潘城的调查者同几个关岛警察。”
“啊,他害怕了。”
“是的。”
“好吧,”我轻快地说,“布什先生想去看看那座监狱,而我没有兴趣。也许你可以安排我同萨伯兰先生见一面,当你与布迪还有他的摄影师参观旧监狱的时候。”
看起来大家都同意了这个建议。我们还需要另外一辆汽车,但布迪说那不成问题,他可以给他汽车经销商朋友打电话。
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我们同慕尼兹提供给我们的查莫罗人逐一会面,我们同他们在阳光酒吧的咖啡室里做非正式的交谈,谈得好的就被邀请到摄影机前。我们花了两天的时间做采访前的准备工作,并在糖业大王公园里拍摄了一些镜头作为背景。
两个来自圣洛村的农民给我们讲述了同一个故事,他们曾在坦那帕哥港口看见过一男一女两名飞行员,后来又在戈瑞潘城见到了他们;一位退休的牙医没有见过那两个白人飞行员,但他在给日本军官出诊的时候,听他们谈论过被当作间谍逮捕起来的那两个美国飞行员,那些军官还就美国人使用女人当间谍一事开起了玩笑。
慕尼兹的姐姐,现在已经六十中旬了,曾在那家旅馆,“空拜亚士…罗坎”,做洗衣女工,她说那个美国女人很善良,并举出了几个事例;她甚至认出了阿美的照片。
一个曾在伊士…绍顿商店——空拜亚士…罗坎旅馆旁边的那家商店——作过店员的男人;说他经常在二楼的窗户里看到阿美。
一个举止文雅的中年妇女说她叫玛蒂达…福斯特…阿瑞拉,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查莫罗人,他们一家曾住在空拜亚士…罗坎旅馆的对面。她的英语说得不好,于是她用查莫罗语同我们交谈(这种语言在我听起来如同西班牙语、法语与鸟叫的混合体),慕尼兹来翻译。当她说到阿美帮助她复习功课,并送给她一枚镶着珍珠的金戒指时,我知道她所说的是实情。那枚戒指在战乱中丢失了。她还说无论那个女人走到哪里,身后都有查莫罗保安警察跟随着。
她还注意到了那个白种女人脖子上的灼痕,她认为是油烫的。
我没有纠正她。
唯一一张熟悉的脸孔出现了,空拜亚士…罗坎旅馆的办事员,现在他已经成了那家旅馆的主人。看起来他似乎没有认出我,这有点伤害我的自尊心——难道不是我饶了他一命吗?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许他认出了我,这就是他为什么没有提起那个教士和被打死在旅馆门厅里的那个查莫罗人的原因。
这些人还有另外八个证人所讲述的内容拼凑成如下的故事:两个美国飞行员,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在坦那帕哥港口被带上岸;那个女人梳着短发,衣着打扮像个男人,而那个男人的头部受了伤。他们被带到当地警察局,然后被送进监狱。那个女人在监狱里只待了几天,之后被转送到军方关押政治犯的旅馆。看起来似乎没人知道在这些神秘的白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被判了刑。
布迪很高兴,他为他的记录片找到了几个好证人——几个会说英语的查莫罗人,这非常有帮助。但采访没有什么新发现,这又令他非常苦恼。我说这也许是因为一度来塞班岛猎奇的人太多了。
这个德克萨斯轮噘起了嘴。
慕尼兹说:“你们也许会发现同布莱丝夫人谈一谈是值得的,我姐姐说这个农妇知道一些关于艾米莉的事情,但她不愿到镇上来,她并不经常进城,你们也许应该去拜访她。”
事情依然没有什么进展,到了第四天,再没有其他的采访者了,于是我们开车沿着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土路,去了乡下。路两边树叶茂密,亭亭如盖,我们的篷车如同行驶在绿色的隧道里。然后,土路斜插进大片的庄稼之中,慕尼兹指着一座中型的铁皮顶木屋说:“到了。”
布莱丝夫人是一个小巧玲珑而又显得高贵的女人,大约六十岁左右的年纪,皮肤光洁而微黑,这样的皮肤甚至会引起年轻一些的女人的嫉妒。她穿了一件黑色、白色与黄绿色图案相间的连衣裙,看起来年轻而活泼。在一片随风摇曳的甘蔗园前面,由慕尼兹充当翻译,她给我们讲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
她的开场白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在坦那帕哥港口看到了两个美国人,一男一女,他们被押往位于小镇广场的警察局。但几年以后,她又一次见到了那个美国女人。
“她说当日本士兵驾驶的摩托车载着那个蜷缩在座位上的白种女人经过时,她正在地里干活儿,”慕尼兹说,“那个女人被蒙着双眼,另一辆上面坐着两个日本土兵的摩托车跟在后面。布莱丝夫人说她悄悄地尾随在这一行人的后面,没有被日本兵发现。他们把那个女人带到了一个早就挖好了的土坑前,他们让那个女人跪在坑边上,从她的脸上扯下蒙眼布扔进了坑里。然后,他们向她开了枪,打在她的胸前,她向后仰跌进坟墓里。”
“出事地点是在这个农庄附近吗?”震惊的布迪问。
慕尼兹转译了布莱丝夫人的回答,是在另一个农庄,靠近戈瑞潘。她从那个地方很快跑开了,害怕日本士兵发现她;但过后她又返回到那里,看到坟墓已被填平了。
“布莱丝夫人,”布迪说,句子几乎不连贯,“你还能再找到那个地方吗?”
她说那座坟墓就在岛上最大一棵面包树下,她曾到那树下去过许多次。日本人夺走了庄稼地里长出来的所有粮食,她和她的一家人只能靠这棵树上结的野果裹腹。
很快,我们回到篷车里,布莱丝夫人坐在驾驶员旁边的座位上,布迪坐在方向盘前,他全身都由于期望而颤抖。我不知道应该想些什么,老问题又浮上来了,那一夜日本人把阿美从海里捞出来,只是为了稍后再处死她吗?他们放在摩托车座位上的是阿美的尸体吗?布莱丝夫人在那座无名的坟墓前所见到的一幕是日本兵对阿美遗体的再次亵读吗?
布莱丝夫人指点布迪开车到达的地方是一片开阔的停车场,像恐龙一样停放在那里的推土铲、拖拉机与其他重型设备堆放在那里,它们不应该放在那里的,所有这些设备都被一道七英尺高的保安围墙围了起来,围墙上头拉着带倒钩的铁丝网。
围墙内似乎并没有面包树的影子。
然而,布莱丝夫人一口咬定,她不会认错地方。
“这地方看起来好像是公路维修保管站,”我说,“这就意味着要同官方打交道了。”
布迪点了点头,“我们有一堆繁文褥节要对付了。”
她的嘴唇抿成了一个冷笑,说:“你不是他的朋友,对吗?”
“我是他的孪生兄弟,在出生时就同他分开了。”
她大笑起来,她并不笨,“他在饭馆里,他是你的了。”
我又穿过了一条挂在门口的珠帘,走进了一间低矮的没有装修过的餐厅,餐厅内有十来张桌子。现在距离吃晚饭的时间还早,因此餐厅里几乎没有人,除了一个戴着海军工程营帽,穿着肥大而破旧的士兵工作服的脖子粗壮的胖男人,他正在埋头对付一盘粘乎乎滑溜溜的海苔,像孩子吃通心粉一样吃着它们。
我穿着黑色T恤衫和卡其布裤子,外面套了一件卡其布夹克,在这样的天气里根本不需要穿这件夹克,但我需要把点三八口径的左轮手枪放在右边的夹克口袋里,以免他万一认出了我。
我当然给了他每个机会,当他吃海苦时,我就站在他桌子前,面对着他。他抬起那张布满麻子与刀疤的胡子拉碴的脸,用轻蔑的眼光瞟了我一眼,这种眼光并不是针对一个曾在他小腹上打了一枪的牧师的,对任何人他都这样。
“你就是那个美国人?”他一边咀嚼着一边问。
他大约六十岁左右了,除了头发有些花白,留起了络腮胡子,脸上多了些皱纹外,并没有什么大大的变化。
“是的,我就是那个美国人。”
他从一个没有标签的酒瓶里给自己倒了一杯红葡萄酒,“坐下,我从不仰视任何人。”
我坐了下来,一只手放在装左轮手枪的口袋里,“艾米莉…埃尔哈特的故事你要多少钱?”
“那可是一个好故事,是真的。”
“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