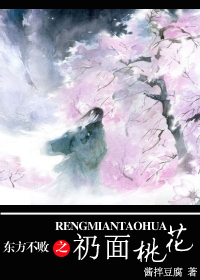桃花婿-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宗一叹口气,看着阿瓶、阿壶满脸委屈称「是」,垂头丧气地离开屋内。
「少爷,如果您要发怒,请对老奴发怒吧。是我让他们──」
「邬总管,你没事的话,请你去别处忙吧。我有许多事要忙,没空。」背对着宗一,萧证悍然地说。
「您为了冬儿的事,感到不高兴──」
「别在我面前提那个人!」
萧证大手一扫,怒将方才刚整理好、整齐堆在案上的成迭书卷,一口气又全部扫到地上。
「少爷……」
宗一从不知道在他温和的外貌下,就像是冰山一角般,藏着这样深沈、强烈的情感。就像是一头不容易被触怒,可是一旦发怒之后,便难以安抚的黑熊,为了躲起来疗伤,不惜伤害周遭的人。
「我不想动手赶你,邬总管,所以你快走吧!」
宗一欲言,又止。还能怎么说?还要说些什么?错误与伤害皆已造成,无可挽回了。
留下将自己囚禁在黑暗里的男人,宗一把独处还给他,遗憾自己帮不上什么忙地离开。
二、
这或许是冬生这辈子度过的冬天里,最严寒的一个冬季了。
那接连冻到骨子里的大雪纷飞,无处可去的漫漫长日,持续了十几天,当天空好不容易告别阴霾,展露难得的霁朗晴空时,奴才们就得急忙铲掉屋顶与街道上的重重堆雪,好让主子们能外出透气。
别以为雪花看似轻飘飘,当它堆积如山占满山头、屋檐与街道时,要想除去它可是个吃力、重度劳动的工作,大部分的奴才都巴不得能不做就不做。
可冬生非但没有面露难色,他一铲铲耐心弄掉那些几乎要压垮屋檐的雪堆,与危险冰柱时,唇畔反倒还漾着浅浅笑意,让周遭的人都能感觉到他明显的好心情。
「冬生哥,有什么好事发生吗?您心情真好耶!」一块儿清着雪堆的马房小厮,忍不住问。
手持着铲子停顿在半空,冬生歪着脑袋。「不不,没什么特别的事呀!我看来心情很好吗?」
几个小厮猛点头。他们从没看过冬生如此眉飞色舞、眉开眼笑的样子。
「那,大概是我见到久未露脸的蓝天的关系吧。今天天气真好,不是吗?」
冲着他们又是一朵璀璨无比的大大笑容,光彩夺目,快把他们几名小厮的眼都闪瞎了。
这时候,底下大门前走出了一个奴才,传话要冬生回到主子房里去,他们有事要找他。
「好!我知道了!」
吆喝回去的冬生,将铲子交给他人,攀着竹梯子返回地面。他步履轻盈、三步并两步地走向「仁永堂」兄弟共享的房间。不一会儿,他已经站在门前,举起手敲了敲。里面很快地传出了「请进」的声音。
「您们找小的吗?」
「嗯,看时候该出发前往萧家了,你准备好了吗?」仁永逢问道。
冬生马上颔首说:「一切都已准备妥当,小的也亲自检查过了。」
「很好,去请车夫驾雪橇在大门前等我们。」
「小的遵命。」
兄弟俩不约而同地看着冬生离开的背影,仁永源先开口道:「哥,看到了吗?他那么样的高兴。」
「我想从昨天我们告诉他,今天要他以随从的身份陪我们到萧府赴宴,他便一直高兴到现在了吧。」
「我们都没有警告他一下,这样好吗?」
「警告什么?怎么警告?」仁永逢拱着眉,望着弟弟。「你要告诉他说,萧证已经完全变了个人、变了个样,不再像你记忆中的萧证?还是告诉他说,这几个月来萧证放浪形骸、夜夜笙歌,已经把你给忘了?」
「呃……不能都讲吗?」仁永源想想。
「你这傻弟弟。」仁永逢弹了下他的额头,道:「两个都不能讲。讲了还叫冲喜吗?」
「可是,哥……」所谓的冲喜是指病入膏肓的人,想借着成亲的大喜事冲掉病魔。仁永源怀疑地说:「咱们只是顺道送冬生到萧家,给萧证看看,这样也叫冲喜?」
「同样的,萧证不也没病入膏肓。」
让现在的萧证与冬生见面,仁永逢其实不太赞成,很显然地,萧证根本没对冬生死心,因此才会以自暴自弃、自甘堕落的假象,试图让自己忘怀冬生。
假使萧证原本忘得掉,如今让他们见面,恰巧毁了一切。
假使萧证无论如何都忘不掉,那更不能让他们见面……因为积习成瘾之人,在戒掉坏习惯的时候,太过苦痛难当,偶有伤害他人倾向的可能。
因此以医者仁心的视野来说,仁永逢非但不赞成,还是大、大、大地不赞成。奈何他一人难敌众口,所有萧证的友人都看不下去,都来要求仁永逢将「邬冬生」吐出来,还给他。
「吐」,说得好像我吞掉他了。
当初可是每个人都赞成,他才让冬生来做仁永家的奴才,怎么才多久的光景,是非就颠倒了?
早知道他就坚持一个旁观者的立场,别蹚浑水就好了。
以后他学聪明了,这种事他再也不碰、不管,免得沾上一身腥。
见到许久不见的萧府大门,冬生一时之间近乡情怯,袍内的双膝不住地打颤,握着雪橇缰绳的手,更是抖得快把持不住这十来只的大型狼犬──幸好他们性格温驯。
冬生把雪橇车停在「仁永堂」兄弟搭乘的马车后方,立刻看到了个熟悉的身影。上前,两人相互拥抱。
「爹!」
「冬生。」宗一急忙拉开点距离,看了看儿子。「你是不是瘦了点?」
「呵呵,爹才是,发福了吧?」
「爹这个年纪,发福是正常的。」
「你儿子这个年纪,瘦一些也不奇怪。」
「你这小子喔……」宗一宠溺地眯了眯眼,摸着他的发,问道:「在仁永家一切还好吧?吃、睡都正常吗?」
「孩儿很好。爹回来萧家当差,还习惯吗?希望孩儿留下的摊子,没让您累坏了。」
「呵,傻小子。别看扁你爹爹了,我可是宝刀未老。」宗一再次掐掐冬生的脸颊,遗憾地说:「爹很想再跟你多聊一会儿,可是今儿个有太多要忙的事……爹得走了。」
每年年末的冬狩季开猎的首日,萧府奴才们都得总动员,上从厨房、下至负责擦鞋的门童,除了要迎接交游广阔的萧炎所邀请来的各界友人外,还要准备上百桌的流水席,招待左邻右舍,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
「我知道,爹去忙吧。我得陪着主子们到宴会厅去。」
「好,我先走了。」宗一走了两步,忽然回头。「对了,等会儿你要是见到证少爷……」
冬生竖起耳朵等着,却等不到爹的下文。
邬宗一张嘴张了半天,最后却将到了嘴边的话又吞下去。
「……没什么,你去吧。」
爹怎么怪怪的?他方才究竟想说什么话,怎么不说清楚、讲明白?冬生纳闷地转过身,不期然地,看到萧证颀长的身影,就站在离自己约三个马身长,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地方。
呼息梗在心口,闷痛着。
四肢跟着僵硬,脚底板彷佛被冰黏吸在地面上。
双瞳固定在他的脸上,四目遥遥相对。冬生心里头又急、又慌张,心想着自己要极其自然地,像过去那样喊「证少爷」,说声「好久不见」。可是越是紧张越是缩紧的喉咙,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
短暂,又看似永恒的一刻,他们互望着。
率先别开眼的,是漠然而面无表情的萧证。接着他转身掉头离去,彷佛这里没有值得他驻足的东西。
「啊……」冬生忘我地跨出一步,却没有勇气追上去。
证少爷看来好像……有些不一样了。
黑瞳里有着过去没有的闇云;不再微笑的唇抿成刚硬讥嘲的曲线;下颚蓄着薄薄的胡渣增添了不羁;以及……眉宇之间的杀气。
关于自己逃离他身边的事,少爷还在生气吗?或是少爷为了他到仁永府上服侍别人而生气?所以少爷适才明明看到了,却又装作没看到他,移开了眼?
自己有机会能向少爷道歉吗?
他想告诉少爷,自己在这两个月里想了许多事,也有许多心得……
「冬生!」
仁永逢在主厅门前,朝他招了招手,要他快点过来。冬生点点头,自己必须以奴才的本分为优先。
……如果等会儿,还能再碰到证少爷就好了。
在他随着「仁永堂」兄弟进入宴会厅时,冬生祈祷着,希望老天爷能再给自己一次挽回一切的机会。
冬狩季是天隼皇朝中,不分贵贱最热衷从事的一项冬季活动。
当然,皇亲贵族们不分季节,想狩猎时就可狩猎。可是对于平日忙于农作、游牧的百姓来说,只有农田休作的冬季是他们唯一可以参与的季节。大伙儿享受着放下日常工作,追逐猎物的刺激感,以及猎得过冬肥狸、鼠猪加菜的成就感,兼丰富过年菜肴的好手段。
这种一举多得的快感,让人们乐此不疲,年年越办越盛大,最后成了冬狩季开猎日一到,就举国欢腾。有钱人争相开设流水席炫耀财力,贵族们则夜夜举办歌舞宴自诩风雅,处处宛如举办着一场天下规模的大型祭典。
天下第一首富的萧家,自然无法置身事外。
──适度的炫耀是必要的。
过去冬生曾因为冬狩季的开销过大,而向萧炎建议,是否考虑减少一部分铺张的流水筵席。但这个提议被否决了,理由也很简单。
──倘若今年的规模小于去年,外人就会谣传萧家财务不稳,大大影响了萧氏商行的信誉。令人担忧的不是一场流水席的赤字,最让人不安的是接二连三将银两从商行中提走的连锁行为。
结果,就这样……明知浪费,还是照样年年举办这规模盛大的筵席。
「一会儿开猎之后,咱们要不要来赌,谁会是第一个捕到猎物的?」
「这还用说,当然是我呀!」
华钿青与郎祈望又斗了起来,一旁的茅山辉则打了个哈欠道:「真是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好争的?头号赢家非我莫属,你们两个只有在后头吃瘪的分。」
没想到连一向允文不尚武的茅山辉,也不敌「狩猎」两字诱发的雄性猎物本能,跳下来竞逐。
霎时间你吹我嘘、你亏我损,好不热闹。
至于各家随从们,则守在自家主子的后方,听着这些主子们唇枪舌战着谁强谁弱,赌着谁胜谁负,偶尔还被主子们诙谐逗趣的言词逗笑,边细心地替他们送上菜肴、添酒加饭。
冬生也知道,自己现在的主子是「仁永堂」兄弟,萧证并不归他管,可是他就是会不小心瞟往坐在主位上那个一声不吭、顾着灌酒的男子。
甚至忍不住白了萧证的随从一眼,为什么会让萧证净喝酒不吃饭?为什么不帮萧证端碗热汤,好垫垫底?
最后他实在看不下去,招手吩咐跑堂的奴才,弄一碗萧证最爱喝的清炖黄鱼汤给他。
──汤,很快地送上来了。
但是看到那碗汤,萧证却做出了彷佛活见鬼的表情,双眼瞪直。
「怎么,你汤里出现神迹了吗?瞧你瞪的!」一旁的郎祈望不知来龙去脉,见他神情诡异,好奇地笑问。
萧证一语不发地抬眼,往后方的随从群扫去。
虽然这并不叫做错事,可是当萧证瞅着自己时,冬生却有一种犯了错、被抓包,想跑的冲动。
萧证突地端起那碗汤,起身来到冬生的面前。
「这汤,你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