驼峰航线"-第5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大约在20秒钟时,我们认识到使用自动驾驶仪飞行是极大错误。Hull拼命抓牢各操纵杆的同时,我拼命地关闭在控制台下的自动驾驶仪。我们的飞行速度原来指示在正负50英里/时范围内,而异常突然地超过红线,爬升率表不稳定,陀螺地平仪难持续动作,整个仪表板抖得厉害,以致不能读出各仪表的读数。报务员打听发生什么事,他试着跟地面站联络,但未能如愿。他的面孔难看得像生婴儿的样子。我确信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这回可能永远不能再返回阿萨姆了。我们开始看见飞机外有相当数量的电光,我们过去从未看见过。对此我们烦恼不安。我探身从侧窗向外望,右侧螺旋桨在黑暗中非常剧烈地旋转着,被大量的闪电断续地点亮。我们看见机翼上积雪相当多,以致连挡风窗都像着火一样。我俯身向前,想看看前面的云是否有任何变化,当我轻按挡风窗时,机翼梢的电光出现闪烁现象,这使我骇怕而不得不放手离开。当我回身就座时,我的头撞到后面舱壁上的高频控制箱而头皮裂开。我暗自诅咒自己像飞行学员整天忍受这些气象的教训。这时我们竭力保持飞机处于正面朝上状态。最后,当我们向云层中心靠近时,赶上上升气流。我们把各电源切断,汽化器加热,驾驶盘推前,爬升率限制在6000英尺/分钟;在13000英尺高度时,我们穿出了云层进入晴朗空域。
空速超过警戒线。
对于最终脱离这鬼地方的感受,确实难以描述——直到过后我们观察周围环境,我们处于50…60英里宽的晴朗空域,透过云层上面的月光照耀着。看到四面都是高耸的积云,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再穿入云层才能逃脱。最糟糕是,对这山脉不熟悉,某些山峰隐藏在下面的云层中,而有些又被积雪覆盖着。我们今天一早就飞过这条线,现在还在这条线,这说明我们已经完全迷航。报务员正紧张地企图与我们的地面高频台联系。最后他终于得到某种联系使我们赖以确立方位。我记不得他是否通过无线电定位或依靠高频信号。那时不管什么,只要有所帮助就能接受,我们的处境犹如溺水的人抓住救生圈一样。“只要耳朵听到,我就遵照服从”这句短话一定是某一位迷航飞行员所创造的。
地面站报务员的声音(地球上任何声音没有如此甜蜜)告诉我们的航向和离他的站的距离。当我们靠近另一堆积云屏障时,特别谨慎。我们关闭自动驾驶仪,打开交叉供给的燃油阀,开大油门至富油位置,调节螺旋桨至高距的同时,我们俩控制住各操纵位置。这时我们已经被振荡到麻痹不堪;飞机像要破裂,但是我们保持镇静。
经过30分钟倾盆大雨、冰雹、颠簸和闪电,我们终于冲击到阿萨姆山谷上空。我喜欢得几乎哭出来。我们看到下面就是“雷多”,远处就是“苏卡里汀”;“汀江”的灯光照耀着“雅鲁藏布江”。我们结束与地面高频台的联系,下降在“雷多”着陆。这时天下微雨,飞机在跑道滑行到装卸区的护墙之后,副驾驶关闭油门停车,我们三人打开机舱后门准备装货。当卡车上的货物装上飞机准备第二天启运时,我们在外面欢笑,叫喊并相互拥抱。我们俯身吻着那炎热而潮湿的柏油路面:多好的路面,下次再见!
自那夜之后,三十四年已经过去。我们的报务员已经消失在历史中。毫无疑问他救了我们的命。我深信他在某些地方一定会告诉他的子女或孙儿们关于“我们两个白痴在雷暴雨之夜几乎使他死在缅甸”。副驾驶后来成为高级飞行员服务于航空公司。
我飞行了约一万五千小时,于1977年从空军退役。几乎各种货机直到C…5型我都飞过,这是我的特殊荣幸。我怀念这架老爷C…47,那夜的经验教训,我们永志不忘。
飞越“驼峰”场景八:与卡尔·H·弗雷特斯契的通信——我们度过风暴的一天当我听到某人唱着“黑暗之中总有一线光明”这句谚语时,我会站起来高喊:“你撒谎!”“你撒谎!”
为什么对这歌词如此激动?因为我的机组成员和我在云层中逗留了45分钟,这期间仿佛受到神话中的复杂女神千年的折磨。
第二十章 威廉·H·滕纳是员干将(6)
甚至现在,在晚上当暴风雨撞击我的窗格玻璃,空中闪电交加之时,我有时凝视着黑暗的暴雨,透过白雪,冰块和雨重现喜马拉雅山峰的景象。我想起并看见我的机组成员在狂乱中跳伞,也看见我的飞行仪表在我面前跳动给出读数,使我突然流出冷汗。我转身离开窗户,我意识到,在这次最难忘的飞行中,我是惟一的幸存者。
那是在1944…1945年的雨季期中,我的B…24轰炸机机组成员和我被指派飞一架其炸弹舱不带炸弹而是装着高辛烷值汽油的庞大油箱,从印度飞往中国东部某机场。
到达目的地卸下汽油后,再装载无线电设备及人员运往中国内陆,然后飞回印度。这次孤独的航程是从中国飞回印度达卡,途中遭遇了热带风暴。
我们启程飞往印度这天早晨,一阵蒙蒙细雨在机场上空落下,从空中的雨和积云看来,我们对它有了思想准备,希望一切顺利。尽管以前我来回飞过这条航线次数相当多,而且多数时间都采用自动驾驶仪飞行,但我仍有不安的感觉。在我内心中促使我坚持做一些经常做过的事。我知道飞机上汽油足够我们飞回印度基地,可是我不放心,必须为额外飞行时间考虑,增加汽油储备在飞机内。
飞机滑行至跑道起飞时,大雨倾盆,机场上空的云层高度低至300英尺左右,以致从低云层出来的倾盆大雨使我看不见跑道的尽头。我把飞机摆正,向前推大油门起飞,四台引擎怒吼不久,我们离开地面飞进密布的阴云中。
在昆明朝上空盘旋至16000英尺高度,然后平飞全力向正西航向飞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们穿越汹涌的乌云飞过荒芜的喜马拉雅峰顶时,雨点如机枪发出啪哒声敲打着挡风窗。面对这堆乌云,不知何时才可以摆脱它。
大概飞了200英里,导航员告诉我,自从起飞之后,由于雷暴雨和山脉的影响,无线电受到静电严重干扰而发现不了地面检查点,不能找到无线电方位。我知道这里没地方可着陆,因为我们在敌占区上空,所以我要求他对我们现在的位置作个大概估计。
在暴风雨带来的气流越来越猛烈,汹涌的暴风雨使得手上掌握的飞行操纵杆都抓不住。我打开自动驾驶仪,觉得稍为缓和,而且运作正常。我正想休息放松一下,突然雷电大作,冲击非常猛烈,我想这飞机会被撕成碎块。围绕着我们的乌云,黑暗如地牢,这情况使我意识到我们已经陷入“驼峰”著名的热带雷暴风雨中。
强大的气流像要抓住飞机来回摇动,犹如狗挥动老鼠一样,把飞机一松一紧摇动得越来越厉害。落雪和冰雹纷纷拍打着飞机,垂直的气流把飞机抛高一千英尺后又抛低一千英尺循环往复。
我的副手呼叫着:“机翼上有积雪。”我连忙向外一看,心情沉重起来。白雪和凝结的雨水在两侧机翼前沿上形成巨大冰块。我开始感到如此下去不知我们能活多久,因为我们所有战机原来安装的除冰系统,通通已被拆除掉。我连忙关闭自动驾驶仪,改用手动操纵飞行了一段时间。各操纵装置活动呆滞,手控困难,飞机几乎没有反应。
因此我又打开自动驾驶仪。我稍为意识到使用自动驾驶仪来度过这段时间可以挽回我们机组成员的性命。
我反复注视着各仪表,留意它们的指针动向。从指针的回转动向知道暴风雪使我们动荡颠簸,随着强烈的气浪浮沉犹如在惊涛骇浪中的软木塞一样。我总觉得我们被下压降至低于喜马拉雅山峰的高度。我急忙从衣袋里翻出小地图,察看这周围山峰的高度为一万二千英尺。
我看一下高度表,它的指针回转一圈又一圈指示着我们的高度是在这崎岖山脉的上面。在飞机里正当指针指示出我们的高度时,强大的雷电轨迹靠近我们飞机外面;雷声和闪电轰鸣,在我周围好像天空将要爆炸。
飞机突然东倒西歪颤动起来,仿佛巨兽脱离控制不受约束。我立即意识到,我们正在被推下降而且非常迅速,我急忙把机关向上推足马力以恢复所失去的飞行高度。
飞机引擎雷鸣怒吼作出反应向上爬升,但已完全不起作用。雷暴雨云的巨手把我们的飞机向下压至1。4万…1。3万…1。2万英尺。当飞机被压到一万英尺高度时,我们的飞行高度已低于周围山脉的高度。这种情况下随时都可能会出事。如果飞机上的积雪能松散掉或者云层消散,那我们就能在高耸的山脉之间按我们的航迹飞行。
强烈的颤动使飞机从头到尾受到破损;高度表指针像酒店的电梯指示器慢慢下落,然后停止向下冲。这会儿我萌发了希望,祈求保佑我们能最终走出这场灾难。但目前的处境只是个开始,糟糕的事还在后头。
我们正经受着雷暴云的强烈下降气流,飞机开始受到风暴的强烈向上气流的控制而发抖。风暴把我们的四引擎飞机托起,以可怕的速度把它推向高耸的雪峰顶,像喷泉把乒乓球喷发到顶点一样。尽管可怕的气流使我们在飞机里跳动颠簸,但飞机上的积雪块毫无松散迹象,这些雪块像嵌牢在两翼和机身上一点儿都不松动。
高度表已指示到1。8万英尺,然后升至1。9万英尺的标志,但我们仍被强大的风力举得越来越高。当指针越过2。2万英尺的标志时,我的头发都竖直了。我注视着各仪表的动作时,心情沉重,它们的指针开始抖动,继而环绕旋转;空速表指针从160英里/时越过红线达到365英里/时飞机的危险速度。当时的高度表指示在2。4万英尺标志,其他各仪表有的凝结,有的滚转。当我看到陀螺地平仪缓慢转向一边而停止不动时,我冷汗直流,没有陀螺地平仪和其他仪表的指导,我就不能判断飞机的飞行状态,如俯冲、爬升或侧滚等等。驾驶室的挡风窗铺满厚层冰雪,看不见窗外暴风雪中的事物。我反复进行紧急处理措施以求恢复各仪表的作用,但仪表的指针凝结在一定位置不动。在我们飞机可能会骤然落下地面之前,我知道时候到了;我立即抓住机内电话,呼叫我们的机组成员,“做好跳伞准备!”在疯狂拼命找降落伞和准备跳伞期间,我听到随机机械师说:“上帝帮助我们!”“上帝帮助我们!”
我脑中闪现出这些事情,想起听说过有些人从机上跳进风暴中心。当他们身体落地时,有些人被冻死,有些人被强烈的风暴扔出云顶几千尺高,高过从飞机上跳伞时的高度。此外,还有许多人今天还活着,他们虽然受到暴风雨和冰雹的冲击,但在紧急跳入云中而脱险。我相信不久,我们这十位机组成员很有可能经历上述情况之一,这要看他们的命运。
当全部机组成员已做好准备时,我告诉他们坚守岗位,没有我的命令,不得离机跳下。在气流强烈冲击期间,尽管我们的飞行没有仪表指导,我们仍然按照自身驾驶的程序运作。各仪表失效之前,如果没有打开自动驾驶仪,那现在我们的困境更为糟糕。
自动驾驶仪的机械“臂和腿”,其作用在于我不能做的它能做到,电动陀螺仪像小孩的



![[综漫]](http://www.xxdzs2.com/cover/noimg.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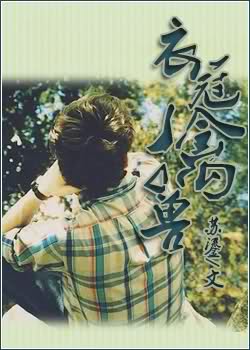
![[综漫]](http://www.xxdzs2.com/cover/3/3472.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