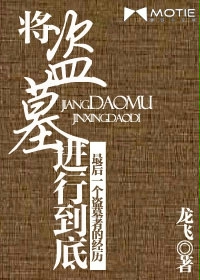行到水穷处-第4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外守着,一个时辰后带楚何氏来见本官。”说着带人退了出去,关上牢门。
牢中只剩下楚翔母子二人,楚翔又叫了声“娘”,仔细端详。母亲不但满头白发,额头上也多了许多风霜痕迹,自己虽曾多次梦回母亲身边,却没想到母子竟会在天牢里重逢!“娘,他们没有难为你吧?孩儿不孝,累母亲受苦了!”楚翔话没说完,已是泣不成声。
“翔儿!”何氏紧紧地抱着楚翔,一面拂去他脸上的乱发,“娘想死你了。让娘好好看看你。”
楚翔忽想到自己身上的刑伤,忙裹着薄被尽力往角落里缩了缩,但何氏已看到地上被子上到处染了一团团的暗红血迹。一把扯开被子,楚翔伤重。无力抗拒。何氏早见他两只腿的情形。气得浑身不住颤抖:“这哪里是天牢,胜过地下地阎罗殿了!”
楚翔忙道:“母亲不必为孩儿难过。孩儿自作自受,并无怨言。”
何氏面现诧异神色:“自作自受?翔儿何出此言?你不是被人陷害的么?知儿莫过母,不管你做了什么,为娘死也不信你会投敌卖国!”
楚翔自身陷囹圄,被严刑逼供要他自认叛国罪名,楚翔虽问心无愧,但想到在秦国这一年多的复杂经历,若要当面向母亲解释,当真是有口难辩。今日听母亲说死也不信自己会投敌卖国,积压已久地无限酸楚一时涌上心头,楚翔再也忍不住,“娘!”扑进何氏怀里,顿时热泪纵横。
何氏轻拍着楚翔的后背。楚翔忽想起小时候,每次受了委屈,母亲总是这样安慰自己。他身为长子,从小乖巧懂事,怕给父母增添麻烦,若遇到什么不顺心地事往往都埋在心里不说,但母亲却一直都相信他,理解他。待楚翔稍稍平静下来,何氏压低声音问道:“翔儿,娘虽不信他们所言,但其中经过,翔儿是否愿意讲给娘听听?他们陷害你究竟意欲何为?”
楚翔面有难色,踟躇道:“此事一言难尽,儿子在秦国时,确实行了些铤而走险之策但母亲大人在上,孩儿可对天发誓,绝无一丝一毫卖国求荣之心。孩儿回国之前,已收到警告,明知前途艰险,儿不愿埋骨他乡,仍决定渡江南归,所以孩儿说今日是自作自受。而他们系我在此,要我认罪还是其次,怕是朝中有人要趁此置安澜于死地,以报私仇。”
楚翔虽未明说是何人主使,但母子间均心知肚明,也知迫供不出,如今是要用何氏的性命为要挟,一时陷入沉默。半晌,楚翔又问:“母亲可还安好?我听小弟说母亲生了重病,孩儿好生担心。我被捕时,曾见到母亲的银钗,不知他们怎生待你?”
何氏摇摇头道:“娘没事,只是挂念你。还有小栩,你可知道他的消息?”
楚翔道:“渡江到了金陵后,我没见着安澜,就安排小栩秘密离开,去给他报信。现在既没见着他,想是还未落入他们手中。”
何氏低叹口气:“这样也好,只愿他听到风声,已逃得远远的。”从头上拨下银钗,握在手中,道:“你看,银钗我已找他们要回来了,这是你父亲留给我地遗物,无论生死,都不能落入旁人手中。”又道:“我料想得不错,果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难怪薛大人带我来见你之前,要和我说那番话。”
楚翔问:“什么话?”
何氏道:“他要我告诉你,叛国案中你不过是胁从,只要你肯供出主谋,便有转机。”忽问,“翔儿,你还记得你父亲临终前那封遗书吗?”
楚翔一怔,随即记起,父亲临终前,曾在前线写了一封血书,交给一员帐下亲兵,那人冒死突围,将书信带回,那勇士自己却伤重不治。楚朗在信中写道“秦兵数倍于我,围困日久,弹尽粮绝,救援不至。明日吾将率残部与敌决战,誓战至一兵一卒,死而后已。余死无憾,唯愿膝下二子承吾之志,光复中原,重归虬关之日,焚此书以告吾,吾当瞑目矣!”当时母亲看完血书便哭昏了过去,醒来后却拉着自己和弟弟的手,流着眼泪道:“孩子,你爹死不瞑目,你们要为你爹报仇啊!”兄弟二人皆含泪起誓,必牢记国难家仇,尽忠以报!
四十 磐石无转移(上)
想到这里,楚翔忙道:“父亲遗言,儿子纵死不敢忘却。”何氏颤巍巍地从怀中贴身的小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信纸,摊在地上,仔细展开,便是这封血书。事隔多年,信上的鲜血已转为暗红,信纸四角都已磨损。楚翔用手指一笔一划描摹着那信上的字迹,追想父亲当时情景,满面愧色,低头道:“儿子辜负了父亲期望,无颜见他老人家于九泉之下。”
何氏安慰道:“翔儿,娘知道你从没忘记你父亲的遗愿,不能光复中原,是天命如此,你已尽力,不用难过了。”停了下,又道:“我听到一些风声,安澜也已入狱,眼下情形怕和你相似。生死事小,节气为大,为人要讲道义,不能背信弃友。不然活在世上,也如同禽兽,楚家决不可出这种小人!”
楚翔听了这话,即正色敛眉:“母亲教训得是,孩儿绝不会贪生怕死,违心画供,辱没列祖列宗的英名。”心中却想:自己倒不怕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但倘若他们以母亲为质,又该如何是好?
何氏点点头,声音转为温柔:“娘本不用多嘱你,生子若此,娘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你父亲在地下,也必欣慰不已。翔儿,你头发乱了,娘帮你梳一梳。”楚翔乌黑的长发已沾满了血污和杂草,蓬在一起,凌乱不堪。何氏用十指分开发丝,一点点理顺,却无法挽成发髻,只能松松地拢在脑后。端详着楚翔,何氏轻叹道:“今天是大年初六,可惜娘不能再为你做顿年夜饭。包顿水饺了。1…6…K…小…说…网”
楚翔听母亲这些话,句句都是生离死别,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见面。自己固然死罪难逃,母亲怕也会同遭厄运。身为人子,终不能承欢膝下,颐养天年,也未生下一男半女,延续香火。到现在害了母亲性命,还要母亲为自己伤心难过楚翔心如刀割,想安慰母亲,却又找不出什么话来说,喃喃地道:“儿子实在不孝,害了母亲,只求来生结草衔环,报答母亲养育之恩。”复暗自叹息,这一生欠了这么多债。来世又怎么能还得完?
何氏爱惜地摸了摸楚翔的头,满足地微笑道:“若有来世,娘仍愿你是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往后退了两步。又深深地看了楚翔一眼,眼中尽是慈爱:“你父亲走了这么久。娘常常思念他。今日先走一步,去陪他了!”忽然右手手腕一翻。将银钗往咽喉插去!楚翔大惊失色,猛扑过去:“娘!”但他手脚不便,到底慢了一步,那银钗已没入咽喉,鲜血喷出,何氏闭上眼睛,缓缓跌倒,神情安详,脸上犹自带着笑容。
楚翔连滚带爬扑到母亲身边,眼睁睁见母亲倒下去,已是救之不及!银钗插入咽喉要害,何氏微微挣扎几下,便已气绝。鲜血漫开,顺着脖颈流下,染红了银钗,染红了落在地上的遗书“娘!”楚翔声嘶力竭地惨叫一声,胸口一窒,眼前发黑,昏了过去。
守在外面的狱卒听到动静,撞开门冲了进来,见室内血流满地,母子二人倒在地上,吓得魂不附体,牢头上前一探,何氏已没了呼吸,忙命人飞奔去请薛大人。少时薛大人急急赶到,牢头慌忙跪下,连连磕头道:“禀禀大人,小人一时疏忽,何氏趁机自杀了!”
薛大人见何氏已然无救,气得狠狠地扇了牢头一个耳光,一脚将他踢倒:“全是些没用地废物!连个女人都看不好!死了重犯,你不想要命了?”指着楚翔问:“他呢?”
牢头爬过去探了探,道:“他只是昏过去了,大概是一时惊痛,应该没什么大碍。”
薛大人不住跺脚,来回走了几步,本想以何氏为人质,要挟楚翔招供,不料却被这女人哄骗,上了大当!她这样死了,犯人顽固不供,丞相又催得紧急,这案子该怎么了结?薛大人彷徨无计,只得下令道:“先将尸首抬出去,找张草席卷了,葬到城外的乱坟岗。”两名狱卒得令拖走了何氏。薛大人看见地上的血书,拾起来瞟了一眼,团成一团扔在一边,又对牢头下令:“你带着人日夜监视楚翔,他是朝廷重犯,若是再出什么意外,你自己提头来见!”
牢头慌忙跪下道:“小人一定日夜看守钦犯,确保万无一失。”
变故陡生,原定计划成了竹篮打水,薛大人一时无策,只得先去回禀丞相,再做打算。离了天牢,薛大人急急赶往丞相府。此时已近三更,王允本已歇下,听到通传,忙披衣起身,命人将薛大人请到书房。薛大人未及行礼,王允已站起来,问道:“牢中出事了?”
薛大人不敢隐瞒,将这几日地情形大略讲了一遍,道:“大人英明。卑职无能,今日带楚何氏去见楚翔,那妇人先满口答应劝其子招供,但不料她早有准备,卑职一时疏忽,竟被她乘隙自杀了!”
王允顿时沉下脸来:“哦?堂堂大理寺寺卿,连这点小事儿都办不好?”
薛大人见王允面色不善,吓得直冒冷汗:“丞相恕罪!丞相恕罪!”
王允不置可否,只问:“安澜那里呢?”
薛大人擦擦汗,道:“人犯也不肯招。”
王允脸色更加难看,冷哼一声,却不说话。
薛大人在下首站了半晌,鼓起勇气试探道:“有了那块玉锁,难道还不能将其定罪?”
王允摇头道:“没那么简单!要定罪也只能给楚翔定罪,有什么用?安澜毕竟曾大破秦军,皇上仍犹豫不决,如果迟迟问不出犯人口供,怕会日久生变。”
薛大人又道:“那安澜奏请朝廷重金赎回楚翔,两人同谋岂非已是铁证如山?”
王允道:“这你有所不知,皇上曾就此事垂询于我,当时我并未反对,皇上才派出使团,献上重金,赎回楚翔,并与秦国盟约,划江而治,互不侵犯。现在仅以此定安澜之罪,说不定会弄巧成拙。”
四十 磐石无转移(下
薛大人这才明白,原来皇上是用重金去买偏安局面,而安澜和王允皆力主赎回楚翔,却是各怀心思,复道:“秦国野心勃勃,纵得了黄金,未必肯就此罢手。”
王允笑道:“我听说符陵自去年兵败后不思进取,这一年来坐享太平,醉生梦死,就连早朝都缺了十之七八,已非当时意气,不足为虑。何况我们还有长江天险,北人不识水性,要渡江怕没那么容易!”
薛大人忙恭维道:“丞相说得极是。”
王允话锋一转,沉下脸道:“少说闲话,审讯之事你得抓紧,七日内不得结果,我另换人审,你留下乌纱帽回乡下去吧!”
薛大人惶恐无地:“下官遵命!”
薛大人从丞相府出来,回到家中,即派人连夜去请张、李二位大人过府商议。薛大人将二人请到密室,讲明情况,苦着脸道:“事情紧急,还请二位大人救救下官!”
张、李对视一眼,皆道:“大人说哪里的话,你我同审要案,都是绑在同一条船上,审不出结果,自然谁也脱不了干系。”
张大人忽问:“楚翔有一兄弟,现在何处?”
薛大人尴尬地道:“朝廷已发出紧急通缉令,悬赏捉拿多日,尚无消息。”
李大人若有所思地道:“既然无法再行胁迫,那仍只有用刑了?”
薛大人叹了口气,面有难色:“用刑倒是容易,但犯人本已伤重,若再动大刑”
三人沉默了一刻,李大人轻叩案几。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