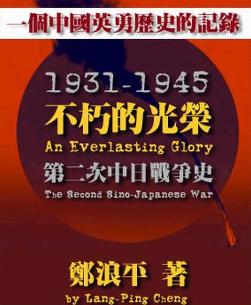日德青岛战争-第5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厉害。还是师爷有一套,他不知从何方打听到崂山的狐仙与黄鼠狼家族是远亲,只有求得狐仙出面疏通调解,这黄鼠狼精才肯罢休。
其实,活在世上的人,很多都是这样——嘴硬。家中不摊事都自诩自己不迷信,一旦家中遭了难出了问题,背地里烧香烧纸,那头磕得比谁都急!郑板桥也是这样,他是人,不是神,家中有了难解之事也得求神求仙来化解。
郑板桥坐船从胶莱河进入胶州湾,然后从胶州湾进入那条北营子河。下船上岸就是村,他倒省事省力气,一步也不用多走就到了楼山狐仙洞下。
这个东夷偏僻小村,自古以来的皇室版图上是不会标出的,秦始皇虽然统一了中国,做了始皇帝,但他肯定不知道这里有个北营子村后来改名叫了板桥坊?末代皇帝溥仪在退位前肯定没有来过这里。这个自从有了人居住的小村庄,自古以来就没有哪个达官显贵来过,村子里也没有出过秀才进士。我在考证时有人对我说也可能出过?也有人说不会,如果出过,保准就修牌坊了。如此说来郑板桥进入北营子村是历史上最高级别的人物了,那还了得,虽不是皇亲国戚、皇上的钦差。他自己偷偷摸摸,但毕竟是父母官亲临。村上的人想借郑板桥的士气和才气,巴望着村中以后出个人物什么的,所以决定要改村名。并在河的渡口处,郑板桥上岸的地方立一牌坊,名扬千古,以鞭策自己的后人争取上进以求光宗耀祖。哪知村小人穷,改名简单,立牌坊难。村中有个教私塾的老学究,肚子里有点文墨,脑瓜子来得快,便道:“这牌坊没钱立,咱们也得立,不立实的,咱们立个虚的,就立在嘴上,这村名不能叫板桥村,得叫板桥坊。让咱们的后代心目中有郑板桥这座牌坊。”村民们在河的渡口处立了一块木版,上书板桥坊。那些不识路的过客认为在这个小村子里有过板桥作坊,更有后来者认为在渡口处搭建过独木板桥而得名板桥坊。这是不明真相的浅陋见识。
有了板桥坊这个村,咱才好说板桥坊村的故事,有人要问了,你说点别的不行?非得说那板桥坊?因为青岛港上的板桥坊牵连着郑板桥,牵连着崂山里的狐仙。这也跟咱们的香格里拉一样,英国人不说咱们永远不知道,也开发不出来。即使另起个名开发出来,那也不是今天的香格里拉。板桥坊也是这样,我不去考证,不去说,有人未必能知道?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实际早以把它忘却了。
在那久远的年代,板桥坊村里有一个光棍,家里很穷,真是家徒四壁。但他很敬业,敬业就是扎实地干,扎实干怎么没有富起来?那年代除了种地没什么副业,充其量有个家庭作坊,那手艺也是传子不传女。别人要想学点,大概是比登天还难。
光棍家里穷,没有钱,没有学得什么手艺,仅靠家里的半亩山地生活。光棍身上有的是力气,就是没地方使上。这家伙还有个晕水的毛病,晕水跟晕车差不多。在船上船那么一摇晃,那水茫茫的一片看了着实让人眼晕,他便哇哇大吐,动弹不得。在这临海小村,有道是靠海吃海,靠山吃山。看起来这海他是吃不成了,村中有船的主,知道他有这个毛病,人家谁敢雇佣他?他呢也不去抄弄这个麻烦,除了帮人家出个大力什么的,就安心上山种他的那半亩地。半亩地对个勤快的庄稼汉来说那是小菜一碟,活没等着干就干完了。闲下来的工夫他也不肯闲着,总想找点营生干。他见有的村民到崂山里去狩猎,心想:下海捕鱼没了自己的缘分,上山打猎还是可以的吧!
那年代工业不发达,钢铁是没有的。只能用木头做个夹子,用竹坯做套弓箭,挖个陷阱下个地套什么的。用这些土制的打猎工具来狩猎,那禽兽多半很难猎到,眼睁睁地看到了,它就是不上套,你一有个风吹草动它就溜之乎也,你干着急!守株待兔那是宋国人干的事情,两千多年来再没听说过。那野兽也有心眼,很多都懂人性气,你下的地套、夹子,它们多半都能识破,不上你的当。
这个光棍子心还挺软,村上有人说他的心眼不够头。他下的地套或是夹子,有时套着或是打着动物了,他看着那些没死的,可怜巴巴的样子,就忍心把它放了。自己穷得要命,心还挺慈善,还时常打付个要饭的。那年冬天下着大雪村上来了个乞丐,看那乞丐穿得单薄,破烂不堪,看样子眼看就要冬死了,别的村民没有管的,或许他们不知道。光棍子开了怜悯之心,忘了自己得寒冷,把身上仅有的一件破棉袄脱下来给乞丐穿在了身上。有的村民看不明白他要干什么?对光棍子道:“你脑子有尿啊!傻乎乎得缺心眼哪?你把棉袄给了要饭的,你还不冻死?”光棍子感到确实很冷,冬得够戗,在村民地劝说下又去把破棉袄从乞丐身上扒了回来。也有的村民说,光棍子心肠好,反正褒贬不一。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光棍子又去崂山里狩猎。他下的地套子,夹子和挖的陷阱都没有收获。便背着弓箭漫山遍野得乱转。忽然他的眼睛一亮,在对面山坡上不知哪位狩猎者下的夹子夹住了一只狐狸。狩猎者的眼睛在灌木丛林里,看野兽看得是入骨透彻的。他有感觉了,那虽不是自己下的夹子,但他断定下夹子的猎人今天肯定不会来收猎。那只狐狸属于他的了。大冷的天狐狸的皮毛是很值钱的,足够他度过这个冬天的。他欣喜若狂,心旷神怡,心里煞是高兴,嘴里哼着《窦蛾冤》一步三跳地往那对面山坡奔去。
宁绕道十里平地,不爬一里山路。这山路爬坡下崖,绊绊磕磕,怪石林立,陡峭崎岖。当他左转右弯来到夹狐狸的山坡上时,在他眼前的却是一位很老的老妪。只见那位老妪被木夹子夹住了双脚,鲜血从脚脖子上流了下来,大概天冷时间长,那血迹有些发暗,但新的血液象是还在流淌不止。光棍子心肠好,没那么多鬼头蛤蟆眼的鬼心眼。有道是:人老实,心眼好,三分痴。光棍子也不寻思,这山前山后的没人家,陡峭的山壁上年轻猎人爬上爬下的都费事,狩猎人下套子,下夹板的地方,哪来的老太太?他顾不得去多想,见夹板伤了人,先救人要紧。立马找来树棍把夹子橇开,看着老太太双脚伤得挺重,随便问了一句道:“老人家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老妪道:“这不,孩子他爹病了,儿子上山来挖药,我怕有些药他不认得,所以出来寻他,告诉他,谁知被这夹板打着了,唉!”老妪说完叹了口气。
光棍子见老妪不能行走,便背起她问她回家的路,然后向山下走去。说来也怪,光棍子背着老妪行走如飞,那沟沟坎坎,嶙峋怪石他一越而过,如同草上飞。只听耳边呼呼的风声,他还以为自己是在逆风行走。不多时他背着老妪就来到了镇上,找寻了个药铺子,坐堂郎中给老妪看了伤,把双脚都上了药。告诉老妪伤筋动骨一百天,得慢慢养疗,天冷不能把伤脚冻了。当让他俩交钱时,光棍子傻了眼,他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家里穷得叮当响,哪来的钱给老妪付药费?有钱在家里的热炕头上喝着个小酒,暖暖和和地过冬天,谁还跑到这崂山里头来狩猎?当时光棍子就支支吾吾地道:“我,我……”他想起了自己身上的这件破棉袄,棉袄虽破但能御寒,好歹还不值个三俩的。于是他把破棉袄脱了下来,放在坐堂医的长条书案上,道:“先生,我家里确实没有钱,这破棉袄能折合几个算几个,如若不够,差多少?来年春天我到崂山里打了猎换了钱再来还你,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坐堂医坐在那里愣了,他看那老妪穿戴得不错,不象是个穷家付不起药费的主儿。眼前的这位汉子脱棉袄顶药费,这十冬腊月的他怎么过?再说这草药也不值什么钱,开百草堂,坐诊行医为的就是治病救人。治病救人,救死扶伤,名扬天下,这是行医者的座右铭。行医行善,普济天下,替天行道这是做人的根本,总不能治好一个老妪,冻坏一个壮汉。那叫缺少医德,害人庸医。坐堂医对光棍子道:“汉子,你虽然壮实,但也抵不住这十冬腊月得冷天,这棉袄权且算我的,先寄在你身上。来年春天冰雪融化,春暖花开,万物盛出,那时你能活动开来,挣了钱再把这饥荒还上,你看行不?”
光棍子当然满意了,哪有不行之理,满口应承道:“行,行!”光棍子为人太实,其别人早就趁机溜了,他不,他没有,他反而觉得过意不去,站在那里两手在自己身上摸索,想摸出点值钱的东西来作为抵押,好等有了钱再来赎回,以示自己的诚信。然而他穷得早已身无分文,他摸来摸去也没摸出个所以然来。坐堂医看出了他的心思,道:“汉子,别掏了,你心诚就行,心诚则灵。人心诚了干什么事都灵验,背上你的老母回家去吧!”光棍子无话可说,只得道了谢,背上老妪出门来。
这时天已暗下来,十冬腊月的傍晚可想而知,滴水成冰啊!光棍子听坐堂医说老妪的脚怕冻,是啊!大冷的天好脚都能冻坏,何况这受过伤的脚。光棍子心想:救人救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医生给治好了,又被冻坏了,到头来还是我之过。他想到这里放下老妪,脱下棉袄把老妪的双脚包了起来,然后背起老妪便走。奇怪的是光棍子并没感觉到寒冷,他觉得全身热乎乎的,象是进了六月天,那刺骨的西北风象是立秋后得小北风,让他感觉到了丝丝得爽意。他并没感觉到事情得跷蹊,反而问老妪这是怎么回事?老妪回答说:“你这是发善心做好事,感动了上苍,老天爷在保佑你。”老妪又道:“为人得心实,不能长弯钩心眼。做人不能贪,人不怕穷,就怕心不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做事为了寻报应得好处,往往得不到。善举做多了,有人会涌泉相报。”
光棍子与老妪说着话,在嶙峋得怪石中,在崎岖的山路上,如同在春暖花开的庭院蹊径中漫步。老妪在他的背上,他一点也没觉出累,反而他更加心情舒畅,心旷神怡。半夜时分他背着老妪来到了山腰的一座庭院前,这座山是他常来打猎的地方,但他从来没见过这里有过这么大的一座庄园,他并不奇怪,以为是自己夜间看错了方向记错了地方。一个老丈早已在庭除上等待着,见光棍子背着老伴回来了,高兴地向光棍子一个劲地道谢,老丈也不知从哪里来得那么大的力气,把老伴接过去后,并没让光棍子进去,只是又道谢了几句,便关上了庭院门。光棍子拿着老丈递出来的破棉袄裹在身上,站在庭院门前呆了一会,便云里雾里地回了家。
等他醒来时已是大半个头晌了,他围着被子坐在土炕上,脑子里时隐时现地想着昨日的事。是梦还是真事他有些拿不准了,他用手敲了敲自己的脑袋,摇了摇头,感觉有些疲乏,身子有些疲软,大脑思维不振作,全身疲倦。他打了个哈欠,那瞌睡虫又爬上了他的脑门子,他有些昏昏欲睡。只当是自己不舒服,心想:大概是病了。正想着那瞌睡虫又袭来,他又打了个哈欠,自言自语道:“睡迷了,睡迷了就再迷糊会吧。”他又躺下了,他躺在那里迷迷糊糊地想刚才想的事,他竟弄不清自己是昨晚睡的觉还是前天晚上睡的觉?自己是不是睡了一天两夜?他有些不敢肯定,拿不准,忘了。心想:马瘦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