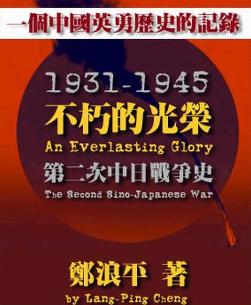日德青岛战争-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老儒腐知道这些富家小姐出手大方,掏出银洋往他手里扔,就象扔垃圾一样。这次又叫他估摸着了,丽娜从兜里掏出一块银洋扔到他手里。他心中暗喜,高兴之余还忘不了生哥那茬子事,他站起来叮嘱道:“你俩找到了那个叫生哥的一定要来告诉我,你俩以后的事我再给你俩指点。”
芳芳和丽娜被这位老儒腐知半年彻底忽悠住了,以为他是神人,满口答应着向他道谢告别。
“嗳,咱俩不急着回去,在马路上遛遛,看看能不能遇着你的那个生哥?”丽娜被老儒腐知半年忽悠迷了,心里高兴,故意跟芳芳逗乐子。
芳芳经老儒腐知半年昧着良心地开道,还真信了。老儒腐知半年的话象一把笤帚伸进她的心里,把她对生哥的但忧一扫而光。她觉着生哥就在附近,象上次那样很快就能相遇,她的心从上次与生哥离别后,直到现在从没这么舒心畅快过。她见丽娜跟她逗乐子,便也高兴地说道:“还想嫁阔佬吗?阔佬可没年轻的!他们的年龄都很大,大概尽是些老头子,拄着拐棍当文明棍,那摸样越看越像老爷爷!”
“谁说我嫁了?我谁都不嫁!你的那些乡巴佬穷光蛋,你自己嫁去吧!我才不嫁呢!”丽娜打趣地道。可嘴上虽这么说,但心里还是想着老儒腐说的那桩子事,她对芳芳又道:“咱俩到火车老站去遛遛,看看生哥能否在那里?”
多遛达会散散心也是芳芳的心意,她的心情比刚才平静了些,问丽娜道:“咱俩坐不坐黄包车了?
“不是说好了遛遛吗?坐那东西干吗?怪颠人的。”
俩人从霍恩措伦路向火车老站广场漫步踱来。
第十二章 破秘盗鸦片 疤根摈酒娘
自从疤根与德国酒娘云雨一番后,他的心思都用在了这上面,忘了为家里人复仇的事了。有机会就一个人偷偷地往啤酒吧里溜,挣得那几个钱不够用的,就跟工友们借,借了也不还,引起了工友们得不满。
工友找他理论,他支吾不出个字曰来。惹得工友暗暗与他背离,背地里都躲着他。
强子在啤酒吧喝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喝的德国皇家红酒,威廉红葡萄酒,这酒与别的红葡萄酒不一样,劲大。因特殊加工与樱桃白兰地的度数差不多。强子醉了后才知道不但中国得老白烧醉人,外国的红酒也醉人。
他本不喝酒,实际也没有钱喝酒;这次醉了后他认定:酒,和外国人一样都不是好东西!
疤根从啤酒吧把他背回来后,他睡了一天一夜才醒过来。他问疤根:“酒娘叫你到里面干什么去了?”
疤根装做啥事都没有的样子说:“酒娘叫我到她房间去看了几样小玩具。没什么看头,就是陶瓷烧制的水鸣鸟之类,和两把紫沙茶壶,也不知她从哪里淘换的。她当时想叫你一起去的,见你愿喝酒,正在酒头上,所以就没叫,谁知我俩出来你就醉了。”疤根这谎撒得天衣无缝,强子当时什么事也没往心里去,也就信了。
但从那以后疤根似乎不再与强子密谋刺杀德国人报仇的事了,这使强子觉着有些异常,且疤根每次外出都是单独一个人。强子几次想问,又觉着他俩的几次行动,都因德国人防范很严没机会下手而搁浅。有可能是疤根单独出去侦察摸情况,强子把疤根净往好里想。可这几天工友们的怨言使强子感到这里面有些跷蹊?他决定跟踪疤根,看他到底在捣能什么?
一日开了工钱,疤根就跟监工请了假,说他这两天闪了腰,要到药铺去抓药。强子知道后就悄悄地跟在后面盯梢,强子盯他不费事,疤根这小子性子直,做事不拐弯抹角,头也不回地径直就从啤酒吧的后门进去了。强子看仔细了,不敢在那里久留,怕惹来巡捕找他的麻烦。
晚上强子把疤根和众兄弟召集到一个废弃的破仓库里,让兄弟们往前围了围,他道:“兄弟们,咱可都是生哥的人,生哥带着咱们攻打完总督府衙门就没了人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但我估摸着生哥肯定没死,我们现在正在找他。我早就看了,在生哥周围的人虽然穷,但我们都是正儿把经的人,我们之间没有一个吃、喝、嫖、赌、抽五毒缠身的人。家中都有老小,挣分钱不容易。我知道疤根兄近日手头有些紧,借了兄弟们不少的钱,看起来他一时半霎还不上。我呢,家人已被德国人杀害了,没了什么挂连。他借兄弟们的钱从此以后由强子我替他偿还。咱们这帮人从今晚起宣布解散,等生哥什么时候回来了,咱们再聚起来……”
“散不得啊!”一个工友道:“咱兄弟们聚在一起谁不怕咱们啊?你们没看出?只要咱们不去惹那些监工,他们都让着咱们,如果散了伙,兄弟我就不在这港口码头上干了。”
“对,不能散!疤根哥借我们的钱我们可以不要了,这伙不能散,我们还等着生哥回来呢!”
多慷慨!穷兄弟们得慷慨言辞把疤根感动了,尤其是强子说的那句:家人已被德国人杀害了,没了什么挂连。自己的家人不是也被德国人杀害了吗?怎么就忘了呢?本来是去寻找机会报仇的,怎么就稀里糊涂地进了德国人女人的怀抱,进了这个臭婊子的圈套,被她玩弄了那么多的钱去?他娘的!真是拿着大奶子哄孩子,糊弄我这个没脑子的蠢货。这时他才想起外国女人的臊臭,远不及中国女人的清香。如果他们这伙人散了,在生哥回来之前,很难再聚集起来。他寻思再三,服软地跪了下来,道:“各位兄弟,疤根对不住大家了,疤根一时犯糊涂,错了。借用的兄弟们的工钱,疤根一定在很短的时间内还给大家。”
“疤根哥,不用你还钱!”疤根的话刚落一个兄弟开了腔,道:“你和强子哥的家人都被德国人谋害了,我们都知道。你带我们干点活,搞德国人一家伙,我们大家得了钱,你和强子哥又报了仇,我们又得了实惠,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
“对,说的对!”大伙齐声应道。几个兄弟把跪着的疤根拉了起来。
“不知兄弟们这活要怎么个干法?”疤根问道:“大家发现没有?从船上卸下来的东西少,装船运走的东西多。卸下来的尽是些日用品,那东西一大包换不了几个钱,戳弄那东西恐怕给咱们惹来的麻烦多,兄弟们得来的利钱少。”
“疤根哥错了,这里面的事你就不知道了。”一个兄弟道:“过去他们偷运鸦片都是夜间单独偷着干。现在他们改变了方式方法,他们几方互相勾结联合起来偷运。有德国人、有日本人、还有大把头、二把头参与。他们每次做得很秘密,真是汤水不漏,万无一失,我不说大家谁都不知道!”
有些工友一听等不及了,忙说:“兄弟,别卖关子了,快说吧!难道他们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干这种事不成?”
“对啊!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就夹在我们卸的货物中,而且还是我们给他们搬运的。”
有些工友不服气了,道:“兄弟,你是在指山卖磨吧?这么大的事情,大伙都在等着这活干,你可千万不能打纸麻花隔山照哇!”
“这是哪里的话?那能呢!这不能怪兄弟们。”这位兄弟并不急噪也不上火,他笑着道:“兄弟们不了解我,我也就这点本事,平时不用,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我。今天用得着兄弟了,我就给兄弟们解释一番。”
原来这位兄弟是满族人,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父辈的另一枝子人。努尔哈赤定国号为金,他的祖上因跟努尔哈赤同宗,也弄了个大臣级的官做。金国改国号为清入关进北京后,他家的祖辈们,一代一代与一朝一朝皇帝们的亲缘关系越来越远。三百年下来,远到与宣统皇帝没了任何挂连,只是姓那个皇姓罢了。当年三国时的刘备和皇帝刘协论资排辈还闹了个皇叔当当。他给宣统当重孙子,宣统都嫌他窝囊。宣统朝他家完全败落下来,便举家跑到了天津口做起了贩卖大烟的营生。
捣弄大烟这营生,多半是捣弄地都抽,没听说开大烟馆掌柜的不抽大烟的。他的祖辈与父辈和别家烟馆的掌柜的不一样,就是光卖不吸,吸是为了鉴别大烟的真伪。他们凭什么技术来鉴别大烟的成色呢?那就是用鼻子闻,这对开大烟馆的人来说是闻所未闻的事情。要不人家爱新觉罗家能统一了民族,建立了国家,这说明爱新觉罗姓能啊!从这位老兄的爷辈开始,鉴别大烟的成色,就靠鼻子来闻,天长日久,一代一代积累了经验。到了他这一代从小就跟长辈们学习那闻的技能。功夫不负有心人,再加上天生长就了那双闻大烟的鼻孔,在他十二三岁时就练就了闻大烟的绝招。
训练的稽毒犬知道吧?稽毒犬在嗅闻包有包裹的大烟时,得趴在包裹上慢慢嗅问。这个工友可以在五步开外就能嗅到那大烟的味儿,且能辨出大烟的成色。这一点绝非夸张,算是有特异功能吧!大烟这东西从道光帝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以来,历代政府也都在禁烟,然而他们禁而不查。也该这位老兄家倒霉,大概是在当时的天津口商号太大,太出名的原因吧,也许是北洋政府为了搞钱的原因,也许是烧香没烧到点子上得罪人了。北洋政府对他家以禁烟的借口突然进行了查抄,当时这位老兄正在关东山购烟进货,才躲过了杀身之祸。他带的账先生及一干人马见他家遭了难,知道干的买卖是害人的营生,早晚不是坐监就是被人弄死,于是私下里各自带了钱财偷偷得溜之乎也。这位老兄没了家,没了钱财,光棍一根,成了穷光蛋。也不敢姓他的那个爱新觉罗了,便改名换姓隐藏了下来。为了生计他从关东山跑到了青岛港上干起了苦力。
他见兄弟们都不相信,道:“我这鼻子是天生的,街上的大烟鬼我不是看,而是闻,离我十步远近,我就能嗅到他身上的鸦片气味。”
“这话当真?”
“绝不会撒谎。”
“在那么多的货包中,夹个一件两件的大烟,你能全知道?”有的兄弟确实不相信这事,仍不放心地问。
“我不用趴上嗅闻,离包五步远就能闻到烟土味。”他解释道:“如果大家不信,等有了货咱们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
疤根见时候不早了,在这破仓库里的时间长了怕引起德国哨兵的怀疑,他见望风的兄弟蹲在高处没动,知道暂时没有危险。在黑暗中,他又往圈内凑了凑低声道:“这位兄弟……。”
“你就叫我胡四吧,”胡四打断疤根的话语道:“兄弟们都叫我胡四。”
“好,今晚这事就这么定了,咱们什么时候干这个活就看胡四兄弟的了。”他压低了声音道:“撬箱开包兄弟们听强子哥的,其余地看我的手势行事……”
时间过得很快,几天后他们在卸一艘日本货船时,胡四发出了暗号,二百多件有十箱子是鸦片,疤根他们也做了暗记。箱子面上虽然尽是些日文和德文,但在胡四的指点下,疤根和强子也都看到了暗记。他们把早已偷带进船舱的铁锹拿出来,悄悄地撬开了木箱子,哇!好家伙,胡四真够格,一点没搞错,满箱子都是黑油油的用防潮纸包裹着的拳头大小的鸦片,足有二百来斤。他们码定这一箱货,又原封封好,从外表看不出动过的痕迹,但实质轻轻一揭盖就开了,便于夜间盗取。这时传来甲板上监工催促劳工快干地叫骂声,这些监工从来不下到又脏又臭的货舱中来,货舱里面不但空气不好,且鼠患成群,看了令人咋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