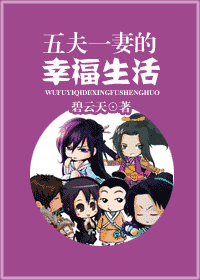�������-��102��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δ֪����Ҳ�������ˡ���
�����������꣬�Ϲ����Ʋ��½ף��������Ǵ�������
��������˾�������������������𣺡���ҹ��ɫ���ã�������Я����̨�;�����
����������ԭ����ˡ���
���������Ϲ����ӽ���������
������������˫������������ֻ�����Ϲ����������ڹ����н��������������¹��Ե�ʣ������ޱ߾��Ʒ���˿˿˪����ɫ������˫���ˣ�����һ����
��һ����ʮ���¡����ˣ����ˣ�
���������Ϲ�����Ŀ�⳯����˫ɨ�˹�����ȴ�ֲ��źۼ������˻�ȥ���暏���
�����������գ���ȴ������˵�˾䣺����ǡ���
�������������Ϲ����ذ����δ�����˫���Ծ��������������ij�ּ����е���Ϥ��Ϣ��ȴ��˲�䲻���ˡ�
���������O�@�ĽŲ�����˾���������嵲ס������˫û����������ȴ����һ˫��ͫ��Ŀ��
���������Ǹ���ֱֱ����������˫��ʼ��δ��һ�ԣ�������ȴ����̽���硣
�����������գ���������澵��֣�������ǰ��������ֻ���������ײ����������ҹɫ��������Զ��
��������������������Զȥ������˫���������
���������ղŵ�һ��������һ�㣬ͻ�������������ݼ��š�һʱ�䣬����˫������Ժ��У�ֻʣ���Ϲ�������ƮƮ����Ӱ����İ�����˵�����θ
����������̨�ϵķ���ź��ⴵ��������ŨŨ�������ҷ�������˫��������һ�ڣ�������������ҵ�˼����
��������ͻȻ��������һ����ȴ��˾����������������̤�����ϡ�
��������̨�������ĵ�����ڳ�������ǰ�����������Ļ���Ծ����ܣ���̨�ϣ�ҹ��¶�أ������Ƿ磬Ҳ�����������������͡���Щ�����������ϵ���¶�����̵�ð�����̣�������ǿ���������衣
��������˾�����IJ��Ӻܿ죬����˫���ֱ����������ۣ���ֱ���ظ��ܵ������������������ı�ŭ��
������������������
������������˫��������������ͼ���½Ų���
��������˾����ȴ��ȫ��Ϊ��������ȴץ�ø����ˡ�
������������˫���ֹ��۵���Ҫ��������һ�����������̲�ס�������յش����ȵ�����˾��������
����������������ǿ����˾�����IJ��ӣ�����������ȥ���ǽ��Լ�߬������������
��������˾����ͻȻͣ��������ȴû�зſ�����
������������Ȼת����һ�ѽ�����˫��˫��������ס��Ŀ���������˵�ŭ��������Ҫ����βŲ�ȥ����������
������������˫�������������۾���������
������������ʱ��˾������������������˫��������ȴ����ѹ�ֵ�ʹ�ࣺ���Ҳ��ں�������������Σ���ں������������ã�ֻҪ��һ�Ĵ��ң����Լ������ˣ���
������������˫�־����������ϱ����������ۡ����Ļ������統ͷ���µ���ˮ��Ƭ�̼䣬���ŵ�˿˿�������⣬�����û������ƣ�ʣ�µ�ֻ�б�������ӿ�ų������У�ײ��������ʹ��
�������������֡���
����������ǧ�����������ں�ͷ������˫һ������������˾������������ǧ��������������÷�����
��������˾�����������������ý�����
�������������֡���
������������˫����أ�һ��һ�ֵ��ظ���һ�顣
��������˫�۵�����������˿δ����
������������˫ͻȻ��������������һ�У�ʹ�������������ƻ���ȥһ�㡣
����������ʱ��������ؽڴ����Ѹ��ܲ�����ʹ��
����������Ϊ�����ؿڵ���ʹ����������Щʹ��ʵ��̫������ˡ�
��������˾������Ȼ������ץ���š�
������������˫�Ʒ���һ�㣬�ֽŲ��ã����ӷ��˺ݵ���Ҫ�ƿ�����
������������˫����
��������˾�������һ������������ס����˫�֡�
�������������֣���
������������˫ŭ������ƴ�������Ľ����ȴ�ǽ���һʱվ�����ȣ�������˾����һ��������ŵ����ڵ��ϣ�����һ���ʹ��
������������˫��
��������˾�������������ž��š�
���������������ɿ�����Ѹ�����ֹ����鿴��
������������˫��ͷ����ɬ������Ҳ���Ʋ�ס����ӿ���ۿ�����һ�ѻӿ�˾������������֣������ȵ�����˾��������쵰����
��������˾������ס�ˡ�
������������˫���ύ����ģ�������ߣ�ȴ����һȭ�������ļ��ϣ�����Ҫ����Σ�������֪����������������������֪����ͬ�������������㡱
�����������ʽ����│ס����ͷ���ۣ�����˫˵����ȥ�ˣ�ȴ�Բ�ͣ��������������
��������˾����û��˵������ĬĬ�س��ܣ���������������Щ��ȴͻȻ���ֹ�����������˫ӵ�ڻ��
������������˫���������뿴������ͷ������䣬��ƾ��ˮ������ʪ�½�
��������һ����������ҹ��Ϯ�������������˼���ʱ����ֱ��������
�����������߰���������˫���ű������ڴ���ϣ����������������ˮ����
����������ҹ����һ����
��������ֱ�����ڣ��Ǿ�������ͷ�ģ����������ѽ�ķ��ҡ�
������������ҹ��������Я��̨ʱ���Ǻεȵ��������㣬Ȼ��ȴ�������Ϲ�����һ��һ˲�䣬һ�ж����в�ͬ�ˡ�
������������˫����֪���������Լ��������Ϲ���ʱӦ��������
����������Ӧ�ô���������Ȼ��Ц������ȥ��Զ�����ĵס�
�����������ǣ��������������εľ����£������Ϲ����������ߵĸ���ʱ������ȴ��������IJ�ͬ��
������������һ�У�����˾����������ֳ�����һ����ζ
����������̨������������ɢ��˾�����Ծ���������������̨�ص����ϡ�
��������ҹɫ����ʱ��Ũ���������ٶ�ȴ��������Ļţ������У�˾�������ֱ�ӲӲ�ģ��ѵ�����˫�������ۡ�
����������ʱ��·�ϣ���ˮ�����ڷ��и�ȥ������˫��ͷ��ȴ�������侲����������������Ȼ����
��������ֱ���ػ���ݣ�˾�������������������˶����ţ���Ҫ���ȴ��һ��ĬȻ��
���������ڼ䣬˾�����ĺ��ʱ����������ȴ������Ȼת����
������������˫�����к���һ����գ����ֳ�ס�������ǣ���˾������
�����������������ˣ�ȴ�Ǹ�ɬ���ѡ�
���������������Ȼ�أ�������ʱ��ͷ������
������������˫����ͷ�����������з�����ȥ��߬�ŵĽ��������㣬һ��һ���˵����˾���������꣬��ִ��Ҫȥ�Ϲ�������Ϊ��ȥ���������˶ϵġ�������������̰�����Ը���֮��Ϊ����������������ģ��ұ���Ҫ��һ�ݵģ������ģ��������˷�����㡣�ҶԷ���������ˣ����Ҿ���������鵽�ϣ���Ȼ�����Ĵ���������������������������ǽԳɹ��������Ծ�����㣬�������⡣��
��������ʱ���ƾ�ֹ��һ�㣬˾�����Բ����
������������˫���ٲ���Щʲô�����ſڣ�ȴ��˵��������
��������ͻȻ��һ˫�ֱۻ����������صؽ���ӵ�뻳�У���Ϥ��������Ϣ���������
������������˫���ң���ʵ�˾�֮��
��������˾�����Ĵ��ָ������ķ��䣬���ȵ���Ϣ���ŵͳ���ɤ������������డ�
������������˫�ı���ͻȻ����һ���������������������ָ����ץ��˾���������ۣ���ͷ����������䡣
��������˾����һ��֪�������Ϲ����Ĺ�����������˫����֮��������δ������ǰ����
������������˫������Ϊ����ʱ��ԭ��������ˡ�
���������������
���������Ӱ��������������͵�ʱ������������ô��ȥ���⣬�������Լ����ߵ�������ˣ���֮ǰ����������Щ�����أ�
����������������������Ҳ���������Լ��и�˾���������ı�Ҫ����֮˾����Ҳ��δ�ʣ����������ڲ�����䣬�Ϲ����ƺ��Ѿ���������֮�䲻�ɴ����Ļ��⡣
��������ֱ�����ڣ��ƺ�˾������������Խ�����Խ�������Ϲ���������������������С�
����������֪��ʲôʱ��ʼ���Ϲ�������ʼ�պ�ب������֮�䣬���Ժ���ȴ����Ĩȥ��һ�����֣����Ǽ��������ĺ蹵��
������������˫�ڽ������������˾����һ���������dz�����̾�˿�����
����������Ȼ����̨�ϣ����˶��й���֮������������ȴ�Ǻ��¡�
�������������ڸ��Է�й֮���������ǽ�ԭ��С����������Ҵ�ŵ��ǵ�С��˼����Щ�����Σ������չʾ�������Է�֪���ˡ�
�����������������˵��������˾����֪�������ﲻ����װ���Ϲ���������������˫�����ټ����Ϲ�����Ҳ����Ϊ˾�������ϵIJ������������ˡ�
����������������������磬����˫��֪������˾���������Ƿ�������ˣ�
�������������˾����������շ�������齽�������֮���ڱ�����ʱ�������Ǹ���æµ�ˡ�
����������������������Ϯ���ӣ���Ȼ������֮����
������������Ƶ���ټ�˾����������С��Ҫ�����������������˫���Ǵ�����˾�����������ս������д������������ʵ����η��
��������ͬʱ��Ҳ�淢ȷ�����˴����˶���֮�£�Ҳ��������������Ϊ��
����������Ȼ�����������˹��������ܣ���ô����һ�ֿ��ܱ��Զ����ˡ�
������������������η�ģ��������˱����ǿ����������֡�
�������������˾������æµ���������е÷��ŵ�����˫��Ȼ�е���ʱ��ȥ������ĥ���������˱���ģ��������ĸ����ҡ�
����������������֮������˫���ȱ��뵽�ˣ����Ұ�����֮��Ĺ��ң���һ������Ȼ����ǰ���ڹ���������֮�С�
����������������ڽ�����ǰ���ڹ������һ���Ĺ��ң�����������ȻҲʮ��ǿ��ǿ����������ͬʱΪ�У�
��������������������ҵľ�������Ȼ���Dz�ͬ����֮������Ϊ���˼����۴�ı����ִ�У���һ�����֣�������ҵľ����Ǹ������Ϊ֮����
�������������ǻۣ�����ͬѰ����Ұ�ģ�һ���ӹµ֮��������������ǰ����֮�ߣ�
������������ȷ��֮������˫�㽫�Լ������鷿�У���δǰ���ڹ�������������Щ���ҵľ�������һ���˳�����Ȼ����ϸϸ�Ƚϣ����ս����п��ܵ������������˳�����
��������˾��������ʱ������˫��أ�Զ��Ų������г��������������ط�����
������������������������Ҳ��Ȼ������
��������˾����������������˫������ȴ���������ÿ��鹤����д�š��ࡢ�⡢�š��������֡�����������һ��˼������������˫��˼�����ˡ�
������������һЦ��˾����������˫�������ֽ��Dz���ȡ�����У���Ŀ�ʵ�������˫��Ȼȷ�ţ����˱�������֮�ˣ��������������е�һ�ˣ���
���������������������
���������Ȼһ��������˫����������˾����֮������һ�ɣ�����Ц�ʵ���
��������˾�������������£�����§�ڻ��У�Ŀ����ȴ��ף�����˫���������е�����Ȼ��������е���֮�������Թ˲�Ͼ������֮�£�Ӧ�÷���������Ϊ���Ź�����ǿ��Ȼ����������������ʵ����Ҳ��������������ڹ�֮�¡��������ô��
���������������ˡ�
������������˫�����ֵȣ�ȴ������������Ϣ��������Ȼ̧ͷ�ʵ����������Σ���
��������˾�����������ǣ���Ŀǰ�����Ȼ���п��ܣ��������ԣ�����ȴ���Զ϶�����
����������������˴��⣬Ī���������֮�ʣ���
������������˫��������Щ���㲻�����Եس�ڶ�����
���������ɻ�һ���ڣ������������Ķ����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