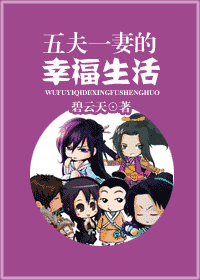�������-��100��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ȴ�������;�����
����������Ц�����䣬��˵�������Ϲ����������Ǵ��ɣ�ͬ�����岻�ʵ���������ȻҲ�ڴ˼��ͻ�����ô����
��������˾�����Ļ��ﻰ�⣬ȫ��ŨŨ�IJ¼ɣ�����˿�����ο��ԡ�
������������˫��������һ�£����Dz��á�һʱ�䣬ԭ����Ҫ���͵Ļ���Ҳ����˵�ˡ�
���������������Ϲ��������ı����ʱ��Ȼ�ظ�������
����������������̹Ȼ�ؿ���˾������
������������������
��������Ƴ��һ�����Dz��õ�����˫���Ϲ������ڻ�Ӧ˾���������ʣ������������̣���������ˡ������ڴ��;�������������й����˰��ˡ���
������������˫�Ȼ�����Ϲ�����
�����������������������Լ��˵صģ��������������˵����ȴ��Ϊ�����Լ�֮���ˡ�
��һ����ʮ���¡�����
������������˫���ģ��ٴα����ص�ײ����һ�¡��暏���
����������֪������˾�����ı������Ѳ��ܿ��������������Ѿ����м�϶��
�������������Լ��Ѿ����࣬������������˵��˽⣬ֻ��˾����Ҳ�����ǰ������ͻ��������������������ͨ�죬����Ȼ�������˵أ�����˭����˭�������������Ѿ������ˡ�
���������Ϲ��������ͣ����Ǻ��⣬������ȴ��Ū�ɳ��ˡ�
����������ԭ���Ѿ�û��ʲô�������ˣ�����������������ź��˿��֮�����衣
�����������ǣ������Ϲ�����˽��ͣ�ֻ����˾������������������˫ȴ���㵱�������淴�����Ĵ�����Ϊ�����ף���϶�����������������ͣ�ֻ���������������ڡ�
��������ͬʱ��������Ҳ����ŭ�⡣
���������DZ��Ƕ�˾���������IJ����Σ�������������
�����������ǣ��վ����������Ҳ�գ�����Ҳ�գ�ȴҲ�ɲ�����������ȥ��
�������������Ϲ���˵���������ڴ��;�������������й����ˡ�ʱ��˾�������ǿ���һ������������˫������Ҳ��������ɷ�˵��������������·��ȥ��
����������Ю������ŭ��IJ������úܴ���߬������˫��������������
������������˫�������ŵ���ײײ������̨�ס�
����������ǿ�����������ľ�ʹ��ֱ���Ϲ�����Ҳ���������ˣ����ŷ��˺�һ�㣬������˾�����Ķ����У����صس��˳�����
������������˫�����Լ����Ǻ���һƬ�����������������ʹ����ؽڴ�����������˫�����м�ʱ����һ��������
������������֮�£�����δ���˵������ػ���˾��������������ʵ�������ϣ���������˾��������쵰����
��������˾��������ԭ�أ�˫Ŀ��ס�������ע��������ȴû��˵����
��������ֱ������˫��������ֱ�����������������Ǻ���һƬ����ȴͻȻ������ǰ������һ����������˫���ص�Ȧ���Լ��Ļ��С�
������������˫����
�����������͵��Ժ����³�����˫�����֣���������Щ˻�ƣ��ƾ����¡�
����������������������������˫�ľ��Ѵ��������ȶ������������䴫�����������Ħ����
�������������ڿڱǼ佻�ڣ�����˫����������˫��Ӱ����������ɫ�紿ī��Ũ�û�������
��������������˾���������أ����ȥ������ȫ������������˫����ŭȫ���ˡ�
������������˫���ε�������̾����ԭ�����߲�������˾����������Ҳ�е��ĺ��µ�ʱ��������Ҳ�л��û�ʧ��ʱ��
������������������֮�����֣���ɹ�ȥ�������ֺαض���˫���ɣ������ѵ�����ô���Դ��Ժ����ҿ���Ҫ��ͬ����ͬѨ�ġ����Ƿ�������˫��˲����Σ���������ο����ð���֮�ã���
��������һֻ�ֽ�����˫�IJ������£�ת˲�����Ĵ��ݼ��ٴα����͵Ĵ��о�����
������������˫����˾���������ǣ���ִ���ʵ����������Դ˲����ٻ�����˫����ĸ��飬�ɺã���
��������˾��������һ����Ŀ����������֮ɫ��
������������˫������Ť�����ߣ�����ȴ��һ˫���۰Ե���Ȧ�뻳�С�
�����������á�
��������˾���������������������漴��ʧ�ڷ�������������֮�С�
��������ҹ����˯���кܿ����š�
���������ڶ��գ�����˫�ڴ��������ʱ�������û�����ͬѰ������⡣
���������������������������ֽŴ���֮����˿����ˮ��������
�����������л��罥����ȥ�����յ�һĻĻ�ڼ��������֡�
�����������Ϲ���������ط꣬�����Ե���˾���������ӱ������
������������˫һ����ס������ͣ�ڰ�����漴�������Լ������֡�
�����������չ���֮��˾����������ȡ����ҩ��ϸϸ����Ϳ���������ĺ���֮����
��������������̨�Ϸ���֮�£���û�����ʣ�����˫ȴҲ�������ᡣ��Ȼ��֪����˾�������ж��Լ����Ϲ�������֮�£��������н�٣����ǣ����Լ�����Ľ��ͣ������������ж���Ƶġ�
�����������ԣ�������ȥ������˫�����Բ������ˡ�
���������������������һ�������������Ϲ����Ⱳ�ӣ�Ҳ���������֮���ˡ�
����������Щ���齻��ʱ�䣬����������Щ�����Ľ���Ϊ��Ч��
�����������������ˣ���
������������ڴ������ʡ�
�����������š���
������������˫��Ӧ�����˴���������齡�
�����������ף���
�����������ͻȻ�չ������������IJ��ӣ����澪�ȣ������ڹ������������������������Ե�Ƭ�̣���ū�ȡЩ��¶��Ϊ��Ϳ�ϡ�
������������˫���㶣��漴����������ָ֮�������ϲ���һ�ȡ�
����������Ȼ������̨֮�£�˾���������Ʋ������ˡ�Ȼ������ҹ���ȴ���˺ݵ��뽫����˫������������һ�㣬������������һҹ��
������������˫��֪�ǰ���֮�µ�Ե�ʣ�ֻ�����������Զ�Ϊ�������Լ�����һ�ش�ˮ��������������л���
����������������ȫȻ������������˾��������Ϊ���ģ�����˫��Ȼ������ġ�
�����������ԣ����������Ľ���������Լ�һ�������Ͻ�����
���������ۿ��������Ҫȥȡ��¶������˫æ��������ֹ��������¶�㲻���ˣ�������齰ա���
����������������ˣ���ҹū�Ϊ���˵�ЩѬ��֮����ڹ����ײ������DZ�����
��������������������������������
������������˫���ȵ������װ������������������ȥ�˺δ�����
�������������ϣ���
�������������˵���������ˡ�˵�������������������顣������ȥʱ�����ҵ�С���̺���ˣ�˵�����ڹ�������˶����ӣ����ҵȲ�����������ҡ����ϻ�˵�����Ƿ���������ʧ�������ҵ������ء���
�������������˵�꣬�ֲ����ֺõز��������ū澻���δ�������϶�˭����Ž������ɼ����϶Է�������֮�ʵ��ǰ��δ�С�
����������ū澻������������˫ȴ���̲�ס������Ц��˾���������Լ��վ�����ȱ�����Ρ�
�����������ܾ����ģ���������������룬����Щ�������ζ����
����������Ϊ����δ��������˫һ�����ܻ��Ǿ����˯��
�����������볤����ȥ���Լ��ı���ɢ�ˣ�����˫����֮��������ڵı�Ժ��ɢ����
����������˵���洺�����ã���һ����������£�����˫��ȥ�ĵ����¶�û���ˣ��������Լ����ڱ���С�����ݵ��鷿������Ķ࣬��������˫�����ǰ���֮�ˣ����ϱ����������£����㰲�ĵش����鷿�ڣ�����һ�����ۣ���������������
���������ſ�����ʱ������˫�����ѵ�˯�⣬���ڰ���˯�˸�����ڵء�
��������˯�����ʼ䣬���ƺ������ϯ�Ϲ�Ӱ���������������ڶ��߷���
�������������ϡ���
����������Ȼ��ֻ���̴�����������������������Ӽ��٣�����������빬����
������������˫�����̧ͷ��˯������俴��˾�����ı۰������ߣ�������ţ����ڰ����
�������������Ǹջ����գ����Dz�ȥ����������ô����ô��ô���ּ��������빬��
������������˫���Dz��⣬����˾������Ŀ�������ѯ��֮�⡣
��������˾������Ϊ���ε�̾Ϣ��һ�����������ȵ�����֪���ˡ����ȱ������������������
���������գ���ת������������˫һ�ۣ�С����������������֮�£���ͷ��������ϸ˵����
������������˫��ͷ��˾��������������һ�ۣ����ת����ȥ��
���������ù�Щ��ʳ֮������˫һ���ǰ�ڱ���ʱ�������ҪС��Ƭ�̡�
�����������Ժ����в�֪���˶�ã����ܾ�����Ƥ�����ģ���̧���ӣ�ȴʹ���Ͼ����ֹ���һ�ᣬ��ϸ��Ĵ��������쵽���ߣ���������
����������ʶ�������ѣ������������۾���
��������һֻ�ָ�������˫���°ͣ���ãȻתͷ��˾����������˫��������ǰ��������������һ����
������������˫���㶣���־תΪ������
�������������ˣ���
��������˾�����������͵ͣ��ƺ���Щ����Ȼ���ջ���ָ��
�����������ֲ���Ȼ����������̨֮�º�һֱ����������֮�䡣�������˼����ֲ�����ĸı䣬����˫��Ϊ������
�������������˶�������Ӧ�������š�
��������˾����û��˵�����Ӵ���������
������������˫��ŷ�����ͷ�Ͼ�Ȼ����Ƥ�ͣ����ϴ�����������
�����������˶٣�����˫�����̲�ס��������������ʱ�����ģ���
��������˾����һ���������ۣ�һ�߿��������Ӧ�������Żز��ã�ֻһ��ʱ������
��������һ��ʱ��������
������������˫�������ƣ�һ�����ȵ���Ϣ���������Ϻ�Ȼ���ֱ�Ȧ��������ʶ�أ�����˫Ҳ���ַ���������ֻ���Dz������棬�����۽�������
��������˾����Ҳ��˵����ֻ�������ø�����
�����������������ҷ���ǰȥ���£�������£���
�����������˻ᣬ����˫̧ͷ������
��������˾����һ���ص������Ķ�ͷ��ȴ����
��������ֱ���˰��Σ��������ص���������ڹ�������Ʋ���֮ʱ������ǰ���μӴ������������֪��࣬��������Ȼ���ǿϾ����ġ������ҵȻ������뿪����������ǰ���������ꡱ
��������˾����˵������㲻�������ط����������͡�
��������������ǰ����������
������������˫�����룺�����������������ڣ���������ʱ��ǰ�����������£�������������ô����
��������˾����������˫���ߵļ�˿�ҷ�����šü���������µ�Ȼ���Ρ����������Ϊ������������У�����Ҫ�����ˡ���
������������˫��һ��˼��������˾��������˼�ˡ�
������������ʱ������ǰ���������������������û���ƭ������ٶ��Щ������������Щԭ����Ұ�ĵ�����Ҫ����������ᣬ����ǰ���μӴ�����������У������ж�����ӵ��������Ϊ����֮���ġ�
�����������˲������ն������˺���Ĺ��ң�����������Ұ����Ҫȡ�������ҳ�Ϊ����֮���Ĺ��ҡ�
������������������֣���������������˶���֮�£������ڹ�����֮ʱ����������Щ���ң�Ը��Ϊ֮��ͷ���ˡ�
�����������������������
����������֪ԭί֮������˫�������ǵ��ġ�
�������������а��룬�����˾��������������ˣ�ֻΪ��ƭЩ������Ҳ���ˡ����ǣ������Ǻ����أ���ô��Щ����Ը��Ϊ�����ҳ�ͷ�������ǹ��ң���Σ���ˡ�
����������Ϊ��Щ�����ǰ���ڹ�֮ǰ�����������ļ�ʿ�����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