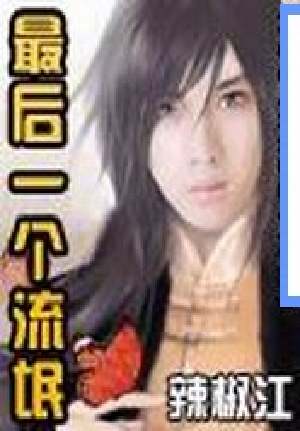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更值得指出的是美国的农场报单显著提高了所有美国农产品的补贴。在这里,请看加征紧急关税和进行补贴对别国带来的后果,饱受危机折磨的巴西出口的近75%的产品不能进入美国市场。巴西人惊叹道:原来这就是“贸易不是援助”啊。墨西哥的情况更糟糕,尽管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严格的限额使墨西哥的大部分白糖根本进不了美国市场。现在,墨西哥的糖业工人失业,墨西哥软饮料的用糖已被得到大量补贴的美国的甜玉米产品取代了。
与贸易一样,全球气候变暖一直是过去20年来大量谈判的课题。美国作为使世界气候变暖的最大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源,一直是这些谈判中的关键角色。大家对气候变暖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对其产生的原因、可能的程度和影响却有不同看法。由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美国对此表示了谨慎的关注,但在讨论的问题没有得出明确结论以前,反对规定数量指标。1992年,美国保证按里奥条约采取措施延缓气候变暖,但仍坚持超出协定规定的减少排放量的定额或特定指标。后来,到2001年3月,布什政府拒绝批准关于制止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从而退出了制止全球气候变暖的一切条约。
这一行动虽在国内受到欢迎,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却遭到广泛谴责。大家特别指出,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仅因为可能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就不愿与其他国家一道用减少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的办法来延缓严重的环境恶化。
2001年6月14日,布什总统前往瑞典的哥德堡,参加与欧盟15国元首的会面,在当地受到数百名示威者的抗议,瑞典首相约兰·佩尔松代表欧洲领导人对记者讲话时说,美国正在推行一条“可能危害环境的错误政策”。
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任何问题上的隔阂都没有在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上的隔阂那么大。对美国人来说,以色列是亲密朋友和盟国。千百万美国人作为旅游者到过以色列,数十万美国人——如果不是数百万的话--原来就住在那里或者有朋友和亲戚住在那里。对许多犹太裔和信基督教的美国人来说,以色列是上帝许给犹太人的地方。美国许多科技公司在以色列的尖端工厂中有大量投资。近40年来,美国是以色列主要的武器供应国、保护国和财政支持国。不仅如此,“9·11”事件后美国人开始把以色列人反对恐怖分子自杀性爆炸的斗争看作如同它自己反对基地组织的恐怖活动一样重要。布什总统要求结束巴勒斯坦的动乱,举行新的大选,以便取代已经当选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即亚西尔·阿拉法特),这种做法在美国是十分正常和合法的。然而,美国的一些盟国却表示,根据他们对民主的理解,他们应当在必要时与巴勒斯坦人民选举出来的包括亚西尔·阿拉法特在内的任何领导人打交道。其他国家尽管也谴责自杀性爆炸,但同时指出,巴勒斯坦人遭受了近40年的占领,在过去10年中,以色列在占领区的定居点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增加。许多人讲,这就招致了一种普遍的内心的不满。有些人还将此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美国拓荒者建立定居点时美国对待土著美国人的做法相比较。2002年夏天,一些外国领导人在与我交谈中强调说,布什总统要求结束巴勒斯坦动乱,却只字不提以色列定居点问题,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会起反作用的。
这一问题远远超出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它涉及美国外交政策关注的更大范畴。在最近去东南亚旅行期间,我发现有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态度在迅速地走向激进。战略上重要的和传统上是自由伊斯兰的国家当中,没有一个国家与中东有重要的联系。几乎没有哪次交谈能够避开巴以纠纷。每天晚上,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美国领导人与以色列领导人一起出席鼓舞士气的集会和以色列人用美国武器攻打巴勒斯坦目标。结果,美国的许多老朋友得出结论说,美国自己在攻打伊斯兰。在欧洲,形势不那么感情化,然而巴黎的一位外交官对我说:在法国大量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看来,“美国的中东政策是在让我国政府拿安全去冒险”。
有些国家,其中许多是美国的朋友和盟国,在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几乎完全与美国的观点相反。他们是傻子?是懦夫?是腐败分子?真要是那样倒好了。可是事实却是我们是常常和大家合不来的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是局外人。我们经常认识不到这一点,因为我们自身块头太大,挡住了自己的视线,使我们看不见别人,还因为我们很强大,使我们觉得我们的标准或者我们的观点是主导全球的或者应当主导全球。因此,眼界狭隘,抱着英里、英寸和华氏温度不放,而世界其他国家早就采用了更简便的度量公制。这种现象的真正原因是我们太强大了,世界其他国家惟美国马头是瞻,结果就使我们的眼睛被蒙住了。
世界其他国家小心谨慎地看待美国,并重视美国的观点,而美国人却经常觉察不到世界上还有其他观点存在。即使觉察到了,它也不在意。最使外国人受刺激的是,美国的单边主义不是我们有意识的政策决定,而是隐藏在政策背后的东西。
而且,正如我下面将要谈到的,我们的使命感和自以为是使我们很难听进去别人的观点。一方面,我们不认真听,因为我们没有这个需要,我们一向认为没有谁有许多值得对我们讲的东西。另一方面,其他国家也不告诉我们会令人不愉快的真情,因为害怕惹恼我们。我们是何等的闭目塞听,只要看一下2002年由“皮尤人物与报纸研究中心”所做的全球性大规模民意测验的结果便会一目了然。这一结果证实了我在旅行和采访中所听到的东西,形象地说那就是,对美国抱有良好印象的大水库依然存在,只是其中的水浅多了。具体说,有两点发现对我在本书中的论述十分重要。当问到美国在制订政策时是否考虑到别国时,75%的美国人说“是”,而在几乎每个其他国家,大多数人却说“不”。第二个问题是要求被询问者给出他们对美国人作为一个人的看法和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看法。答案表明,对美国人的看法比对美国的看法好一点。例如,在约旦,25%的被询问者对美国的看法较好,53%的人说他们喜欢美国人。在整个中东,民意测验的统计数字与此类似。这似乎说明,外国人比较喜欢美国人,而不大喜欢美国的所作所为。
所以,每当我们觉得我们的用意高尚的时候,我们就可能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9·11”攻击事件是个最好的例子。回想起来,当时没有一个夏洛克·福尔摩斯式的大侦探去从周围的蛛丝马迹,甚至是摆在国家安全顾问办公桌上的材料推论出迫在眉睫的危险。即使有,我们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因为我们不认为我们应当听别人的意见。或者拿越南来讲,法国人在我们之前遭到惨败,但他们是法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在德国进攻面前失利后,不是没有放弃吗?此外,我们并不打算重建什么帝国。我们的动机是纯洁的,我们是为反对邪恶的共产主义而战,并企图阻止失败的多米诺效应。这里仅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不明白,民族主义和独立是与共产党毫无关系的问题。我们大家本应当明白这一点,但因为我们不关心它,所以也不明白。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我在日本攻读研究生时有亲身体验。我学了两年日语,成绩尽管不是顶尖的,但也不错。有一天,在东京羽田机场我用日语询问问讯室服务员一个问题。她用英语回答说她只能讲几句英语,所以无法回答我的问题。于是我转向我的中国夫人(她不会说日语),告诉她对服务员说些什么。当我夫人用日语重复我刚才的问题时,服务员立即用日语作了回答,给了我们所要的信息。我在这里的意思是想说,该服务员知道外国人不会说日语,于是当不像日本人的人说她的母语时,她就听不懂了。同样的道理,我们美国人常常对某些事情不明白,是因为我们将自己置于这种处境之中了。
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总是错的,别的国家一贯正确。就拿京都议定书来说,我们本可以拿出很好的理由来说明布什政府的立场,然而我们不是说明自己的观点或者甚至承认其他国家的正当要求,而是企图发号施令,这常常坏了我们的事,即使我们有正确的理由也是枉然。在京都议定书问题上,我们的单边主义做法可能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使我们几乎不可能在修改后的协定上签字,而这个协定现在看来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在其他更重要的问题上——如伊拉克和反恐问题——寻求支持与合作的努力遇到了困难。实际上,正是因为不可避免的会有这样的时候,即我们必须采取单边行动,我们才应该矫枉过正,只要有可能,就要采取多边行动,以便将我们不能避免的阻力减至最小程度。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要顾及别人的想法,反正他们也不能伤害我们。这正是问题之所在。他们能够伤害我们,办法多的是:例如,在提供有关恐怖活动的情报方面不合作,不为美国的远征部队提供中转设施或飞越领空的权利,或者抵制美国货抑或推销其代替品。实际情况是,世界变得如此之小和如此之危险,美国完全不能忽视自己在全球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真实情况,或者误解别国的作用。里根总统重复约翰·温思罗普的理念说:现在是清醒的时候了,要像别人看我们那样来认识我们自己,并要做出决定,我们是真的希望成为“不亲、不恭、不受制约和不负责任的国家”,还是希望成为我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的人。
您在阅读以后各章时要记住,所做出的选择,不仅对美国的对外关系,而且对美国自己,以及对维护我国的驻外使馆在“9·11”事件后淹没在鲜花丛中的那种理想有何意义。还请记住第二点,也是温思罗普训诫中常常难以说出口的话:“如果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我们对上帝不诚实,上帝就会撤销它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就会成为新闻报导的题材,就会嗅名远扬。我们将会给敌人以口实,让它诽谤上帝和所有信仰上帝的人,我们将会使许多上帝的信徒丢脸,使他们的祈祷语句成为对我们的诅咒,直至我们无地自容。
第二章 不被人承认的帝国
引言
我们美国人是上帝特殊的选民——我们时代的以色列人。我们负载着世界自由之舟。——赫尔曼·梅尔维尔
波托马克河从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山间狂奔而出之后,河面豁然变宽,舒缓地弯向汇入大西洋前的最后一个航段。美国最美的城市之一华盛顿,就坐落在这个航段的岸边。它宽阔的街道由中心向四周呈放射状延伸,环形交叉口、雅致的纪念建筑物和城市广场星散其间,给这座城市平添了些许欧陆风情,展现出了它的原设计者,法国城市设计师皮埃尔·朗方的美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