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婚姻进行曲-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俊�
“噗”一声,我立刻笑翻了:大老婆——李冰,靠,还真是忒有冲击性和幽默感。
对面那位脸色登时难看起来,本来还是一阴天,现在已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很快就要狂风骤起、要劈人了。
第22节
菲德考得不错,心情大好,叫上李冰、带了我去他租住的地方。
大概是收拾过了,屋里比我上次来时干净了许多,窗帘和床单也换了新的,图案挺可笑的,是忒幼稚的斑点狗和机器猫。问他,他说前几天他姐来看他给换的。菲德的姐姐今年上大二了,年纪有二十岁吧,我在菲德的相册里见过她照片,是个温柔纯净、忒有气质的大美女,听说还特别地疼菲德,经常过来帮他收拾卫生,买衣服给他,甚至把自己的生活费匀给菲德做零花。那时我就忒不服气地嘟哝来着:这么好的姐姐咋没让咱摊上呢。
“给你俩看个忒他妈刺激的片子,是我跟一朋友淘换的。”当菲德从床底下最里面位置,拽出破旧不堪的黑白电视机和台六七成新的VCD机时,我便猜出他意图,可那时再逃已晚三秋了,就只好硬着头皮坐在床上,看他一人在书桌那儿忙活来忙活去。越看,我越觉蹊跷:那家伙技术太他妈熟练了,一瞧就不是生手,看来平时这种事没少干。
等电视出来影儿,菲德一屁股坐我旁边,用力搂住我,冲我笑笑,露出口白牙,还顺势在我胳膊上捏两把。我没吭气,只斜了李冰一眼:他坐在床的另一头,手里端着饮料,漠无表情地盯着电视屏幕。
等看完那部再恶心不过的男男三级片,我身上早不知被菲德吃了多少“豆腐”,他意犹未尽地还问旁边那位呢:“咋样,哥们,有感觉没?要不要去厕所消消火。”那位更他妈牛,冷冰冰地丢过来一句:“屁感觉。”我立刻对李冰肃然起敬:靠,你看看人家,那叫一个正人君子,一点儿禽兽的龌龊心理都没有。
“假的吧?”菲德说着,摸一把人家裤裆,然后不明意义地笑声,去厨房拿饮料去了。
我摇摇手里的瓶子,雪碧剩的不多了,就举到嘴边,打算一口气干掉。下一秒钟,一大片阴影突然投过来,在我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时,脸已经被人亲了。
手里举着瓶子,保持那姿势,我呆坐了好久。摸摸脸,湿湿的,还真有口水印。不可置信地向李冰望去,他冷冷地、静静地回望着我,眼里没有一丝暧昧不清的影子。
“砰”地把瓶子掼在地上,我“噌”地站起,恶狠狠地举起了拳头,就要挥上。
“宝贝儿,没饮料了,你喝啤酒成不成?”关键时刻,菲德从厨房门口猫出头来问我,我一怔,气势全无,答到:“不喝,让我妈闻见酒味打也得打我个半死。”
“哦。”菲德答应着,又缩回去。我也不看李冰,径直进了厨房。菲德还在地上的纸盒里扒翻着什么,见我站在跟前,就说:“又脏又乱的,你进来做甚。”我一伸手,扯着他衣服领子把他从地上拽起,接着忒野蛮地勾住他脖子,狠狠地吻上去。
犹豫了下,菲德猛地回抱住我,揉也似的把我用力按在怀里,……吻了好一会儿,他气息紊乱着松开我嘴巴。我不依,又硬凑上去,他连忙做个打住的手势,而我那时已几近着魔,红了眼,把手搭在他裤带上就要解。“你他妈疯了啊!”菲德面色大变,强压住我手不让我动,我急了,挨在他胸膛上,一味地用脸颊死命摩擦,疯了似的喃喃叫着哥,哥。
“哗啦”,一杯凉水把我浇得清醒过来。菲德叹口气,放下手里的刷牙杯,趴在我耳边悄声哄道:“宝贝儿,是不是看片子看得上火了?别急,等我把那碍事的打发走,咱们再来过好不好?”
眼里突然蒙上了层水汽,我也不晓得自己为什么有点儿想哭,菲德温柔地摸摸我头,拿了两罐啤酒出去,丢给李冰一罐。
李冰倒也识趣,放下啤酒,说他有事走了。他前脚走,菲德后脚就把门反锁上,然后靠在门板上呆呆地看我。
“朝歌,你刚才太不正常了。”
“对不起。”口吻淡淡的,我无力地笑下。要跟他说明状况:李冰那厮背着他吻死党的男朋友吗?不,决不——这么龌龊的事打死我也说不出,我就把它当作垃圾埋在心里沤烂拉倒好了。
真是一冗长难熬的假期。
刚开始:是拼命睡,把脑袋都睡扁,睡得不知时日时辰;疯玩,把平时捞不着玩的都尽情玩个遍,玩到彻底厌倦,再没胃口;看电视,遥控器几乎被按坏掉,却发现节目大都没营养还超级烂;出去闲逛,天气酷热难挡,恨不得干脆整天泡在有冷气放送的超市、商场里得了;去姥姥家,被抓住昏天黑地地打了整天麻将。
后来,收性儿了,老老实实做起作业,没几天又腻了,开始怀念上学、跟同学朋友在一起的日子。于是,又找几关系不错的哥们凑一块,打了一整天篮球,晚上还吃了羊肉串。
就这样,暑假莫名其妙过去了一半。
有天,我正吹着电风扇呼呼大睡,突听有人敲门。稀里糊涂地爬起来,可脚刚落地,就象失去双腿般,重重跌在了地板上。靠,准是整夜吹电扇的恶果,我那儿正憾恨呢,外面的敲门声却更急切了起来。这他妈谁啊,小腿使不上劲,我就在地上努力地跪着爬,等好容易爬到防盗门那里,我强拽着门把手直立起身来。
立马粗鲁地拉开门,我准备着如果是搞推销的,就臭骂他一顿,一照面,却是背着双肩背旅行包的老姐。我一愣,接着想起:中考结束后,老姐跟着舅舅一家出去旅游,昨天打电话说今儿个回来的。
“没带钥匙啊?”我瘸着腿往卧室走,看一眼钟表,竟中午两点多,连睡了十几个钟头,眼睛又涨又酸,脑袋疼得厉害,昏沉沉的还是想继续睡。
“你猪啊,睡到现在。”老姐丢下书包就奔厨房去了,听见里面锅碗瓢盆一阵乱掀乱翻的声响,我从床上坐起来,边揉太阳穴边没好性儿地喊:“别捣鼓了,老妈没给你设投食点儿,我这儿吃饭也没着落呢!”
老姐有些火光,跑我门口下了命令:“我坐了一整天火车回来,命都丢了半条,你下去给我买点儿饭吃。”靠,你是我祖宗啊,这么该你的!我也蛮火的,但仍是忍气吞声,套上T恤,穿着大裤衩,奉命下楼给她买吃的去了。
卖饭的离我家很远,得走到外面大街上。顶着烈日,我左手提一兜山西凉皮,右手提一兜朝鲜冷面,打着哈欠,迷迷登登站在路口等信号。
从大地升起的滚滚热浪,无情地灼烤着裸露的皮肤。乍然间,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从身后飘过,我忍不住回头看,是几个穿花连衣裙的漂亮女孩,她们在说什么开心的事吧,脸上漾满着清纯可爱的笑容,然后,象群百灵鸟,转眼飞离了我的视线。
花一样的少女,多么迷人的生物……我正赞叹着,有人在我后面猛按自行车铃,我斜斜地瞥过去,不认识的家伙:个子挺高,皮肤黑得象炭,戴顶黑鸭舌帽,帽檐压得低低的,脸上架了付宽墨镜,嘴唇干干的满是裂口,跟一快渴死的鱼似的,操,本来人就黑吧,还非穿一黑T恤、黑短裤、黑运动鞋,斜挎一黑书包,这回可好,黑得更没边了。
我看看那人,没搭理他,继续悠闲地等信号。却听有人阴森森地在我背后说:“操,装不认识老子啊!”
这时,信号转绿,我头也不回地快步通过路口,迅速转进一繁华小街,在拥挤的人群里大摇大摆地钻来钻去,回头再看时,忍不住笑了——街口,跨骑在车子上的家伙摘了墨镜,正无可奈何地望着我。
第23节
“几日不见如隔三秋,哥你怎么成一非洲人民了。”我打趣菲德,他站在树阴里,拿帽子拼命扇着风跟我说:他前阵子都在游泳、打篮球,今天天不亮又跟人爬水库边的卧虎山,下山时走错了道,差点儿就困悬崖上,上上不去,下下不得的,最后多亏几人互相鼓劲,才艰难地返回山顶,从上山的道回去,结果到了山脚下,几个人饿得要死,渴得要死,还虚脱得要死,就把所有钱凑一块,吃喝了个痛快。
“送你的。”他给我块石头,我看看,嗨,不就一普通的山石嘛,亏你大老远背回来。
“这破石头,干嘛用——拍人啊?”我在手里掂着,分量还真不轻。
菲德笑笑:“这是燕子石,上面有三叶虫,我好容易从山顶上敲下来的,你拿着玩吧。”
我默默看他一会儿,这人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够率性,他要做的就一定要做到、一定能做到,他就是有这样的魄力和勇气,够努力,也有卓越的能力,争强好胜,决不认输。
假期快要结束前,菲德约我去“零点”酒吧玩,我长这么大了,头回看见女人跳钢管舞,真他妈煽情,够刺激。震天响的迪士音乐,沙发座上嗑药的瘾君子们,妖魔般在扫射的激光灯下乱舞的人群,吧台里又帅又另类的调酒师,浓妆艳抹的风骚女人……一切的一切都那么堕落,却吸引你不断沉沦下去……
菲德中途丢了我去跳舞,他跳得实在太帅太酷了,立刻招惹了大帮爱慕者,围着他又是吹口哨又是鼓掌欢迎。我躲在昏暗的角落里,冷冷注视着发生的故事……夜如果是无边无际的海洋,我们是不游泳就会缺氧死去的鱼,那菲德一定是周体都会发光的最耀眼夺目的那条。他太有资本疯,太有资本胡闹了,他肆意挥霍自己的青春,却从没留下一丝遗憾。
菲德回到座位时,眼里混杂了过于狂乱的兴奋,他趴在我耳边大声说:“宝贝儿,去跳舞。”然后把我从座位上拉起,心底里突生出厌恶来,我用力挣开了手臂。
怎么了?他的眼睛里透出天真的疑惑,我大声告诉他我讨厌。
“真他妈一神经病。”菲德恼怒着跟我出了酒吧,他把书包扔给我,就拿出了烟点上。
书包里的东西沉甸甸、硬邦邦的,我从没完全拉上的拉练位置看进去,竟是把如假包换的钢制砍刀,不由顿生寒意。“那个是防身用的,这酒吧都出好几条人命了。”菲德扫我一眼,漫不经心地说。
深吸一口烟,朝霓虹灯照亮的夜空喷去,他淡淡一笑,把头侧向一旁,不知怎的,我总觉得他那再冰冷不过的眼神里,露出几分狠毒的颜色,锐利得如同他藏在书包里的砍刀。
那天晚上,菲德发了邪,说什么也要我留宿在他那里。我可不想犯下弥天大祸,就坚决地说不。他强调不会真发生啥,还扣了车钥匙不让我回家,以此胁迫我。我没办

![同性婚姻合法之后,我们离了[娱乐圈]封面](http://www.xxdzs2.com/cover/1/122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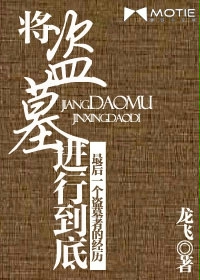

![[家教同人] 剧情崩坏进行时封面](http://www.xxdzs2.com/cover/noimg.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