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婚姻进行曲-第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数学题,就见前位坐着的腾坤捂着鼻子站起身,拿一大课本来回地扇,嘴里含含糊糊骂着:“操,哪来的臭鼬?”
这一扇不要紧,四周的同学都严重受害,各个苦不堪言,从座位跳起来就闪。我憋足了气跑到窗跟前,一把推开了窗户:“散散味,散散味。”
腾坤那里还幸灾乐祸呢:“都来尝尝,都来尝尝,还很新鲜,还很新鲜。”可下一句就冲林如去了:“林胖胖,是不是你中午吃撑了啊?”林如心情不好,埋头写英语单词呢,一听马上不干了,脸气得通红,跟那红灯照似的:“妈的,欺人太甚了吧你,我跟你又不一行坐,怎么会是我?说不定是你自己放的呢!”
上午结下的梁子,再加上这回的,眼见这二位就跟斗鸡似的支起了架儿,旁边的人赶紧地上来劝:“二位哥哥,二位哥哥,消消气,这么点儿破事何必呢?”
腾坤有些理亏,决意退步了,说声:“算算算。”林如却象吃了枚地雷,忒壮烈地瞪着眼,死活不松口:“不道歉,我他妈跟你拼了。”
情势向人预料不到的方向迅速发展,我急了,过去劝架。可没等走跟前,他俩就动起手来,书本、铅笔盒、饭盒什么的满屋乱飞,眼花缭乱间,有个东西猛地照我额头砸来,把我砸得钝疼钝疼的。教室乍然死寂了下来,好多人都傻傻地看我。一道热热的血,以飞快的速度,“唰”地从我裂开的眉骨位置滑下,然后血越流越多,竟顺我下巴滴答滴答的,把校服褂子的前襟染得一片鲜红。
没有擦脸上的血迹,我只默默地从地上拾起不锈钢的酒精炉,随手放在手边的课桌上。
酒精炉底轻磕在桌面的声音,和自习结束的铃声恰时重叠,我抬眼看看那两位“故事主人公”,冷冷地从牙缝挤出一句:“都给我肃静了!”
腾坤心虚着后退一步,林如却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拿一布冲过来要往我脑袋上按,我淡淡笑着推开他:“你还真他妈的笨——拿抹布给我按伤口,想让我得破伤风啊!”
林如呆住了,啥话也说不出。我慢条斯理地脱下校服,卷一卷,用力按在满是血的头上,从他身旁过去,往教学楼后面的医务室走。
我这付鬼样子,把沿途遭遇的学生、老师都吓得不轻,我倒满不在乎,笑着对他们解释:不留神给撞门帮上了。
笑归笑,我这心里却怒海滔天、一片阴霾:妈的,赶明儿出门一定得看黄历!瞧这倒霉催的,什么“飞碟”都降落到俺脑袋上了!
菲德也瞧到我了。快走到医务室时,正碰见他和几个不三不四的家伙围一起说什么事。见我那情形,他脸立马黑了,跟一陈年不刷的锅底似的,之后不但跟了我进医务室“疗伤”,还非打破砂锅问到底,要我“卖”出是谁干的,我从没见过他那么狠毒的劲儿,真的是太糁人了,不寒而栗。
为防止日后腾坤和林如遭他暗算,我陪尽了笑脸和吐沫星子,就差给他跪下了:大哥求求你,做人做得别太绝了行不行!
到最后,菲德终于软下来,答应这事过了不再追究,我才算彻底松口气。
第12节
校服沾满血迹,额头青紫,还顶着条创可贴回家,老妈非常火光,揪着问我:是你打劫人家了,还是人家打劫你了,瞧弄得这熊样。我嬉皮笑脸地说:光顾看帅哥,脑门子撞门帮上了。老妈不信,还对我抄起了鞋底子,我马上递他手里一只软泡沫塑料拖鞋:“妈,还是用这个吧!”然后……哎吆,这顿好打,快把我打出脑震荡来了。
这次受伤,竟把我跟菲德的距离拉得贼近,那个什么什么的热度噌噌地直往上走。
早上,他非在校门口候着我,说要一起进去。他一“名人”,长得又极扎眼,冷冷酷酷的,往那排光秃秃的丁香树下一杵,立刻成道“亮丽”的风景线。而我撞见他,恨不能立时找个地缝钻进去,再有就是找堵墙撞死拉倒。
中午,他见天介给我买饭,然后俩人在小树林一块吃。他看我时,眼神忒他妈大胆、火辣、勾人,好象要化目光为手爪,把我身上衣服一层层都扒了,再剥掉我皮,数清我到底几块肌肉、几条肋骨,最后再把我开膛破肚喽,查查肠子、心肝、肺是不是都在。我挺怕他那样的——那哪象在吃饭啊,倒象要把我给剁巴剁巴了给吃肚里去。
放学,他送我回家。我纳闷着问他:你们高一不上晚自习啊。他说:送下你我接着回去。我说我怕我家里看见,尤其是我老妈看见(上小学时,有回我妈翻我书包,翻出来过别人写给我的情书,不分青红皂白把我一顿猛削,且罚我挽起裤腿跪半小时搓衣板。体罚结束时,我起都起不来,小腿上印满了竖条纹的血印子,只能四肢着地、手脚并用爬回了屋。末了我妈还放下狠话:敢早恋就打断你腿)。菲德说:没事,我只送到植物园东门。后来,我才迟钝地发现上了鬼当——他那哪是送我,明明是想着在植物园里找个荒僻角落跟我亲热亲热。
他对我这么露骨,我真害怕那个他妈的“公众舆论”又升级。果不其然,不久就听有人嘁嘁喳喳地议论:朝歌还真把菲老大追到手了,那么一难追的人,还真有两下子呢。恐怕是对人家下“伟哥”啥的了,还拍了照片什么的做证据。要不人家能给他捏手里,又接又送,还附带陪吃陪喝的。当时,我真想破口大骂来着,可一想,谣言这东西是越抹越黑、越洗越臭,除吃哑巴亏没甚好办法,所以也只能当只“忍者神龟”了。
周五下午只两节课,我们早早放学了。
三月初,天气还挺冷的。菲德照例在校门口的丁香树下等我,这回他穿一黑色长外套,露着纯白色毛衣领,头上压了顶鸭舌帽,鼻梁上还架着付忒猖狂的小圆墨镜。操,干嘛这种打扮,更他妈象流氓了。我推车子出来,远远地闪开他,低着头溜边儿走。
正在心里念叨呢: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他就骑着车慢悠悠过来,横挡住我道。“地上有钱啊?”他使劲吼着,还按两下车铃。
等骑到植物园东门,菲德又把我硬拖进去。我说:你大冷天跑那里头吹风,真有病。他马上蛮横地堵我:欠削啊你,哪来的废话。
强拽了我书包肩带,菲德带着我在两旁是茂密竹林的小路上七拐八拐,最后来到一山坡。山坡上枯黄的草皮既厚又软和,还零零星星种了些矮灌木。菲德把我扯到山坡的向阳面,找一隐蔽处,把他的书包跟我的往草皮上一丢,脱下外套铺地上,自个坐下后,又命令我也坐。操,选这么个兔子不拉屎、鸟不生蛋的地方!我边环顾寂静无人的四周,边暗声诅咒,却也没办法,只好挨了他坐下。
气氛有些僵……菲德一言不发着就地一躺,我疑惑着看一眼他:妈的,这人戴着个忒深奥的墨镜,什么狗屁表情、心思也看不出。算了,不理他!我无聊地一把把揪着草皮玩,突然,他的手就搭上我的腰,把我惊得一跳,赶紧地往外挣,他一把拉住我衣服,死死的,不放手。
“过来。”他柔声招呼着我,悚得我寒毛一起立正,直觉告诉我:危险正慢慢逼近,而我却无处可逃。“别。”我的声音因害怕都颤抖起来,他嘴角上挑,露出不明意义的笑容。
手臂被使劲一带,我重重倒向菲德,他一翻身把我压在下面,一手把墨镜摘下,远远地扔了出去。
呼吸在墨镜除去的瞬间一滞——我得由衷地赞叹这混蛋几句:他穿纯白的高领毛衣还真好看,又精神又帅气,浑身透着股迷人劲。菲德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又黑又深的眼睛里流露出梦一样的色彩,象要把我给勾进去般。他长长的刘海直直地垂下,轻轻搔着我脸庞,我嫌痒,把他头用力推到一边。
“怎么,不好意思了?是不是哥哥我太帅,把你眼给晃了!”他闷笑着说。
我一边推他一边说:“见过不要脸的,还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你那脸都赶上解放阁的城墙厚了。”
“操,挺损啊你,欠收拾对不!”他突然起身,同时扯着我胸前襟,把我也提溜起来。“跟哥亲口。”一胳膊搂着我脖子,一胳膊固定了我腰,象举行什么隆重仪式般,菲德阂上了眼帘,慢慢地勾下头,错开脸,把嘴压下来。
不知哪来那么大劲,就在他灼热的呼吸喷来,两人嘴巴就要接一块的危险时刻,我把他推了个大跟头,跟受惊的兔子似的蹦跳着逃窜了,一边逃我还心有余悸地一边回头看,菲德也吓一跳,他正呆坐在草地上,不可思议着望我。
地形不熟,再加上慌不择路,我在那边竹林里转悠了半天,才摸出来。等出来,菲德已经守着我俩的车子等好久了。他痞痞地叼支烟,得意洋洋地跟我招招手,那意思说:小样儿,跑得了你跑不了车,你还得乖乖地回来。
第13节
护城河边柳树泛出了淡淡的绿色,迎春花吐露金黄,过一阵,粉粉白白的桃花,绚烂的蔷薇将把河岸装扮得分外华丽浪漫。春天又悄悄地来了,冬天收起它寒冷的外衣,已经走远。
站在教室外的走廊,看这个城市,雾蒙蒙的,很脏。一些风筝高高、远远地飞着,象人的一些心情。这时候的田野会是怎样的景象呢……金黄的漫野油菜花,绿油油的麦苗,欢快流淌的小河,嬉戏的白鸭,辛勤耕作的农民……尽量想象着,可思想还是太贫瘠。
春天,是有着恋爱味道的季节。春天是激情的艺术家,在沉闷灰色的图画涂抹上鲜艳的颜色。
可是,伴随着绿叶鲜花,春天还将夹携沙尘来到城市,所以,从不觉得这是个让人愉快的季节。因为……春天实在是太短暂了,往往还没回味出,它已为炽热的夏天所代替。
菲德吃饭速度奇快,几下就把米饭、菜什么的扒个精光。看我饭盒里菜还不少,又劫了几筷子。完事,他把饭盒往我身边的青石板上一撂,心安理得地说声:“我买饭你刷饭盒,这叫分工明确。”然后从腰后别着的随身听那儿扯出两只耳塞,塞进耳朵,闭目养神地听起磁带来。
你别以为这人耍派耍酷——在听流行音乐,他那是在听英语磁带,而且天天中午如此,也难怪他从来成绩优异,根本不象个混混的水平。
过一会儿,我拿手指戳戳他,他皱皱眉头没理我。我接着戳他,他烦了,张了眼瞪我。我朝他左边指指,他看过去,笑了:有只又肥又大的灰毛老鼠不怕死地在那儿溜达呢,它找到只苹果核,就用爪子捧了拿两只啮齿啃。
靠,早听说食堂和厕所里的耗子多得到处散步,而且不怕人,今儿个也让我看眼看见只。菲

![同性婚姻合法之后,我们离了[娱乐圈]封面](http://www.xxdzs2.com/cover/1/122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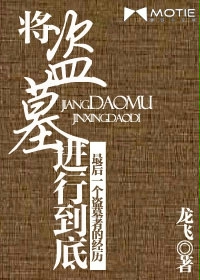

![[家教同人] 剧情崩坏进行时封面](http://www.xxdzs2.com/cover/noimg.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