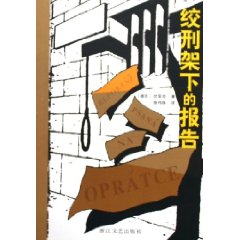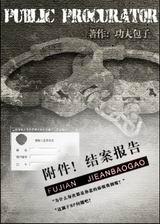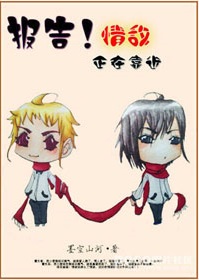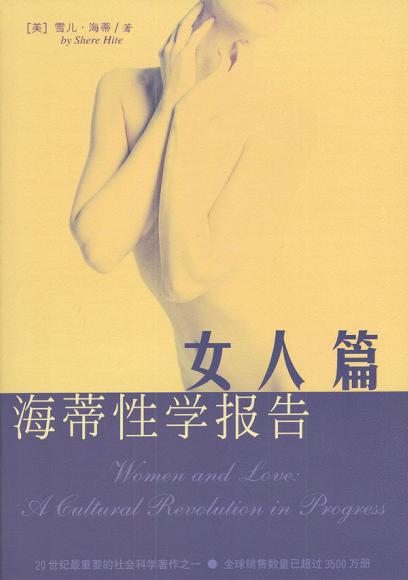食相报告-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虽然便宜,虽然方便,虽然也不乏营养,但很少有中国人爱吃美国鸡。
“人人都说美国好,只有吃鸡忘不了”,一直是旅美华人对于美国鸡的难以下咽的记忆。网人图雅曾经煽情地写出了这种他乡吃鸡的心情:“圣诞之夜,无亲无朋,一人独坐,两眼苍茫,鸡肉入口,如嚼木屑。几大口伏特加之后,只觉家国万里,鸡翅,鸡腿,恍如机器零件,难以下咽。”
孤独无朋以及家国万里之悲情,恐怕一般是由鸡肉的“如嚼木屑”所煽动的。换言之,但凡那鸡肉好吃一点,哪怕只是略得了白切鸡或德州扒鸡(此德州不是得克萨斯州的简写)的大致,这个圣诞夜也许就不会如此难过了。
顺便一提:图雅在上文中说到圣诞夜担挑的那只“如嚼木屑”的美国鸡,极有可能是阉鸡。按照美国农业部对加工鸡肉的分类,这种去势公鸡,约十五周大,去毛后重量为二点七二至四点零八公斤。在美国,阉鸡也被称作“圣诞鸡”,常用于节日大餐。
啊,阉鸡!说到阉鸡,这正是华佗大师在研制药引时无意发明的一道人间美味,今天的广州人对它尤为垂涎三尺。粤垦路那一带的湛江大阉鸡(又名骟鸡),白生生,油光光,用加了蒜和香油的酱油蘸着……可怜的图雅。
中国鸡馔的令中国人怀念,除了鸡种的不同,更在于它的繁琐——正是美式“效率”的反面。只有异常复杂的鸡才能唤起如此复杂的情感。复杂和繁琐不仅包括了鸡的种类,料理的方式,鸡馔的滋味,甚至还涉及到吃鸡的形态——不知还有没有人记得王景愚当年表演的“吃鸡”?天才的王景愚几乎调动了身上的每一条肌肉,才把一个人吃一只鸡的场面演绎到接近于惟妙惟肖,淋漓尽致。至于那次经典的“吃鸡”何以竟开了“小品”的风气,就是后话了。
虽然繁琐并不是通向美味的唯一途径,不过,就鸡的个案而言,美国鸡之所以不如大部分的中式鸡馔好吃,换句话说,就是明快输给了繁琐。
德州扒鸡(又名德州烧鸡),可能是中国北派鸡馔的代表作。配料的繁杂是怕级成功的关键:花椒、口蘑、丁香、砂仁、桂皮、豆蔻、草果、白芷、大茴香、饴糖,还包括十多种中草药。用两斤左右的生鸡,从脖子下开口取出内脏洗净,把两只翅膀编插进去,稍稍脱水便下油锅炸一炸,取出后再加配料进行深度的熏制,最后以大锅蒸透。
上等的德州扒鸡,据说用手提起来略一抖,但见鸡骨徐徐脱落,皮肉却依然保持完整,端的是神乎其技。
除了制作方法之外,北派名鸡还有一个极为相似之处,就是美味皆经由铁路传播。事实上,德州扒鸡一开始并非德州特产,而是德州以南一百里开外的山东禹城县老字号“德顺斋”的出品。禹城扒鸡后来之所以改做“德州”,盖因后者地处津浦路枢纽,客流量极大,经营者因而迁往该地。与德州扒鸡相比,同样是色重味浓,但味道逊一筹,制作上也略嫌粗糙的河南道口烧鸡,也是因京汉铁路而得以将美名远播四方。
这样一种诞生于多重复杂工序之下的美味,最后却以近似于快餐的方式卖给了火车上那些南来北往的旅客,在快餐时代的铁路旅行者看来,这是多么奢侈的旅行,何等奢侈的年代!
发源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叫化鸡,相传最初系乞丐所为,本来应该算是中国鸡馔里最仓皇、最苟且的一种烹法,但是,在饭店里所能吃到的叫化鸡,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鸡要嫩鸡,泥需“药泥”,腹中酿入多种佐料,体面裹上荷叶一张,别说是叫化子,美国人见了大概也会落泪。
在“生猛”之前的粤菜,并不是以海鲜立足,而是得力于对材料的高度精致化处理,“金华玉树鸡”就是这个方面的杰作。
与北方的那些吃起来不脱豪爽之气的“啃的鸡”相比,南粤诸鸡在餐桌之上皆显得意态安详,雍容华贵。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始创于广州酒家厨房的“金华玉树鸡”,不仅有美名,而且卖相极好。制法是:先用上汤将海南文昌鸡浸至仅熟取起,冷后起肉去骨,切成方长形片,然后再把鸡肝浸熟,连金华火腿一并切成鸡片大小,与鸡片相间排置于碟中,放入蒸笼回热,再将芡料淋上。
上桌时,有碧绿的油菜竖直置于正中,“玉树”即得名于此。吃法也很有讲究:鸡肉、鸡肝、火腿,此三片须同时夹而食之。
这道广州酒家传菜,又名“广州文昌鸡”,半个世纪以来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至今仍见于台、港以及京、沪等地的传统粤菜馆。不过,在广州酒家、即使是在文昌路的广州酒家总店,出品却令我失望,虽然把鸡肉、鸡肝和火腿一并送进嘴里,倒也真能吃出一番陌生感来,但是,我肯定没有得到文昌鸡应有的味道,因为我曾在海南的文昌县吃过真正的文昌鸡,因此,我很怀疑这里的“文昌鸡”是不是因酒家所在的文昌路而得名。
我发现,大部分以繁复取胜的菜式其实都在悄悄地淡出主流,不仅是“金华玉树鸡”。一方面,高成本的劳动导致了昂贵的售价(金华玉树鸡在广州酒家售价每只一百四十元),另一方面,盘子里的那一派“洛可可”风格亦不合于现今的审美风尚。
好在,我们还有清平鸡、市师鸡、盐焗鸡以及新近加盟的粤西大骟鸡等二十多种技术难度中至偏高的粤式名鸡,使鸡的传统和美味得以“鸡啄唔断”地永延。否则,可真是“玉树凋零,鸡何以堪”了。
在会吃鸡的人看来,洋鸡的不好吃,除了烹饪方式上的简单直白,还包括了鸡种以及高度机械化的饲养过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是一种宿命性的失败。
虽然中国市场上绝大部分的鸡的生活环境都与美国鸡无异,不过良种的土鸡依然受到某种程度上的个性化保护。广州参观标榜的所谓“走地鸡”,并不表示其它的鸡都是终日翱翔在天空或游弋于水面,指的是在半集约化饲养方式下成长的鸡,生前过着一种半个人主义半集体主义的生活。
以文昌鸡为例,其祖先据说居住在海南岛文昌县的谭牛镇天赐村。村里有几棵大榕树,树籽满洒在地上,成为鸡只最爱的食物。从光绪年间开始,在一代代的生化作用之下,就逐渐养成了今天这身材娇小,毛色光泽,皮薄肉嫩,骨酥皮脆的优质鸡种。现代化的养殖,虽然没有那么多的榕树籽可喂,却也令其时时置身于山场树林之中,给它一个空间,让它自由活动,采食到充足的野果以及螺、虫等动物蛋白和青绿饲料,一早一晚,还得补喂小量大米、糠和番薯之类的农作物。放养约八个月后,就开始将鸡只集中起来置于安静避光处,不使其随意走动,强行连续育肥三十天以上。这个过程,类似于公司上市前的“静默期”。反观美国的肉鸡,从出生到上市一般只要六至八周。
这是一种从生前就开始酿造的美味。北京“谭家菜”的白切鸡,也是自己养鸡,从娃娃抓起,并且喂以酒精、虫草等营养饲料,使八个月后方能宰杀。上桌前,还要用老鸡煲成的上汤淋熟。
中国的养鸡、烹鸡乃至食鸡,大多是复杂而“慢”的。上海“荣华鸡”挑战“肯德鸡”的失利,实在是犯了知彼而不知几的错误。
拉灯谈吃
聊天一般被认为是一种轻松但是缺乏建设性的休闲活动,因此往往又被称之为“闲聊”,因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闲聊的结果往往就是无聊。
然而,在如恒河沙数、漫无边际的聊天主题当中,我认为唯一可以称之为比较“有聊”并且具有建设性的主题,恐怕就是谈论吃喝,因为这是一个聊着聊着容易把人聊馋甚至聊饿的危险的主题,每到这个临界点上,聊天者通常都会忍不住将该话题自动中止,转而采取若干解馋疗饥的实际行动。
上学的时候,学生宿舍晚上十一点准时熄灯,不过熄灯只造成上床,并不能导致睡觉。一房六七个“早上八九点钟的”男生,就这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黑暗中有一搭没一搭的瞎聊着。聊得最多的,是吃。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各自家乡的吃食都有各自的美味。要知道,在黑暗中谈吃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聊天,当然聊女生也很刺激,不过在夜里十一点以后聊女生这个话题通常都不会有即时的结果,最快也得等到天亮。谈吃就不同了,这个话题之所以不仅刺激而且危险,是因为他比女生更具有操作性,因为聊着聊着,各人的肚子就开始感觉到饿了,黑暗中甚至听得到从空洞的腹中传出的咕噜咕噜的声音。正如作家老鬼在小说《血与铁》里写到的那样:“六零年大饥荒饿伤了我,太怕饿了,一饿就完全垮掉,毫无意志力。我是这么的矛盾,一方面热衷于看英雄的书,贪婪地读有关反修的文章,满脑袋革命,一方面又偷别人的水果吃。因为饿,就骗家里的钱,就偷吃偷拿……”
“有时真想大哭一场。我要能在母亲肚里该多好呀,永远不用发愁挨饿,干鸡鸣狗盗的事。初一初二年级,就是在这样的日子下度过的。吃是脑子里最经常盘旋的念头。当然也关心着中苏关系,关心着反修大业,关心着革命和进步。但一天到晚最主要琢磨的是吃。对女生的兴趣大弱,流氓思想几乎没有。吃饱饭比想女生更重要。”
虽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馋痨之夜于四十年前的饥荒岁月在起因上绝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结果却高度的一致。女生就在楼上,家里的美味则在千山万水之外,只有饥饿在自己心中蠢动。
钱钟书先生尝言:“大抵学问,乃荒江野老屋中,两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作为学生,我们只是在日间被培养,并且在吃饱之后也研究研究学问,到了熄灯之后的黑夜,这些饥馁的“两三素心人”于远离市区的荒江野老屋中所能商量的,似乎也就剩下吃喝之事了。
躺在床上谈吃的结局往往是这样的:黑暗中终于有一个人忍不住从床上坐了起来,接着,就有更多的人也从床上相继坐了起来。正所谓坐言起行,坐起来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偷电,这时,有人负责点亮蜡烛,有人从床底下抽出校方严格禁用的电炉,也就是说,形而上正在转化成形而下,虚拟即将演变为实干,一顿扣人心弦的子夜大餐就要开始制作。
所谓大餐,通常也就是偷偷摸摸地煮上一锅面条(那年头,快食面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奢侈品,经常需要泊来),豪华一点,也无非是煎上几个鸡蛋(那些鸡蛋都是白天在校门口用粮票跟乡下人换来的)。当煎鸡蛋的香味在潮湿的空气中从二楼的阳台袅袅飘升到学生宿舍的三楼和四楼,除了平底锅里的那一阵阵愉快的“滋滋”声,还能听到从楼上陆续传出的一些动静——很显然,煎鸡蛋的香味正在像传染病一样发生着连锁反应。
接下来,就开始听到四下里此起彼伏地响起了一些锅碗瓢盆间的互相碰撞,如果是白天的话,定会见到一派“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喜人景象。
事实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大学生的一日三餐,基本上是以不同地区的标准按照定量供应的。吃饱喝足当然不成问题,只是这种吃饱喝足想来也只是负责至晚上十一点之前。从这个钟点之后到第二天早上六点之前,按校方的规定是集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