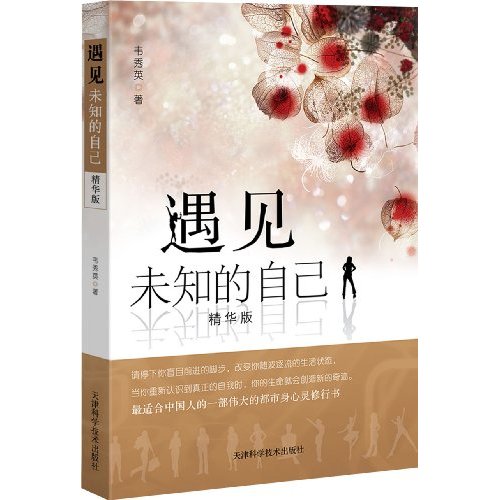当种马男遇见种田女-第9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最高,他原先给你三间缎庄也只是担心你没做过生意,先让你从小生意做起,练练手,你爹爹其实名下另有产业要赠给你,只是你连番让他失望。”二老爷打开那楠木盒子的夹层,又取出几张契纸,道:“谦儿,这些你先收着,代你爹爹保管,等寻回你爹爹,再问问他,要如何决断。至于你,尚谅,把缎庄契纸拿来。”
尚谅自是摆手不愿,可二老爷虎着一张脸,步步紧逼,尚谅只得步步后退,莫氏则忽然又哭喊道:“圈套,圈套,这都是你们的圈套!我家谅儿本就该继承缎庄。”
尚谦再回头和众人看那张莫氏说尚侯爷要将缎庄都交给尚谅的书信,果是右边已被人截去一条边,并无年月日,怪不得尚谦当初初看时只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如今真相大白,都只觉尚谅有些自作自受。尚谦蓦地想到一件事,冲上前去,抓住尚谅的衣领,道:“你盗了此信,满心以为自己有胜算。可你这般做,首先得让爹爹不在,你才能鱼目混珠。快说!你是不是知道爹爹在哪?”
尚谦这一喊,大爷和二爷也回过神来,只他们原先没敢想尚谅和莫氏会为了缎庄而做出类似“弑父”的行为,此时都怒目而视。尚谅咬牙道:“你胡说,我怎知爹爹在哪里。爹爹是自己同那些道人去寻仙的。”他又转头看了莫氏一眼,莫氏此刻又哪顾得上她,她听说如今连手里的缎庄都飞了,早已六神无主。
待到莫氏略微回过神来,见几人逼近着尚谅,便哭喊连天:“你们欺侮我们母子俩就算了,还要冤枉我们!我和侯爷同床共枕这么些年,怎会遣人去害侯爷。”她哭得凄惨,众人一时倒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时候又有家丁急急忙忙跑来,喊道:“三爷三爷,侯爷寻到了,在同福客栈,正昏迷不醒。”
“快,派人去接侯爷回来。”
“侯爷已在马车上了,我们也寻来了大夫。”
“那两个道士呢?”尚谦急问道。
家丁苦着张脸,道:“三爷,这可真不知了,那二人只留下了一封书信,上面写着让三爷您亲启。”
尚谦这下可是脑袋一个犹如两个大,这几日的书信格外多,一封接着一封,每封都关系重大。
如今莫氏正强撑着身体,冷笑道:“也不知是谁和那道人勾结,连信都是亲启的了。”
尚谦不去理会她,拆开那信,上边写着:三爷,吾二人不过是江湖过客,他日收人钱财来此,原本实存不善之心,只吾等也知三爷与顾夫人乃儿女亲家,我们自不敢得罪。只是我们收人钱财在先,江湖之中行有行规,万不可取财而不办事,且所托之主吾等亦得罪不起,只得作此权宜之法。但这半年以来,我们从未给侯爷服用过药丸,只是传授些养生吐纳之道。然此番主顾要求我们将侯爷带走,吾等断然不敢真将侯爷带去寻那飘渺无依之物,只得将侯爷藏于客栈之中,这几日,听闻顾夫人的八门已经开始寻人,吾等只得先行告辞一步,侯爷不过服用的一般迷药,睡上几日自然便能醒来。吾等不过是取人钱财,当时实是进退两难,还请三爷宽宏大量,饶吾等一命。
这信上虽只字未提究竟谁是他们的主顾,但侯爷忽然不见对谁最有好处,自是不言而喻。二老爷看了信后,竟忽然狂笑,又悲道:“你们真以为大哥是个被蒙骗的么,大哥早间便同我说过,他虽明知那道士是有人故意安在他身边的,只他说再如何自家之人也不会害他性命,他得了隐疾,只得姑且一试,若是为此丢了性命,便是他此生可悲,也无脸再苟活于世。说到底,他不过不愿相信有人会害他。”
二老爷一步步走向莫氏,莫氏吓得哆哆嗦嗦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讷讷道:“你看着我做什么?那两个道士又不是我请的。是……是侯爷自己结交的……”
“你可敢看着我等再说一遍?你若不认,我便去寻证据,若被我寻出蛛丝马迹,而且大哥回来了,只要他醒来,我等去问上一问……你这妇人……你这妇人……”二老爷气得早已说不出话来,他是武人出身,两眼圆瞪,不怒自威。
莫氏挺起胸,强辩道:“我是侯爷夫人,你待如何?我也不过是为了侯爷好,侯爷说他身体不适,需寻些秘方,我一心一意为了侯爷,又有何错。”
二老爷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只得抖着手道:“你……你好……你好……若非那两个道人有所顾忌,我大哥吃过什么,如今身在何处都未可知!”
尚谦忙扶住二老爷,道:“二叔,您莫气了。这些都应怪我,明知那两个道士有些蹊跷,却没有细细盘查。我以为……我以为爹爹是真心喜欢……那些修仙之术。”
二老爷叹了口气,道:“子侄本就不得过问父辈之事,这倒也不是你的错。罢了,罢了,还是等你爹爹醒来再说。”
尚侯爷是被人抬回侯府的,虽然并没有受伤,却是昏迷不醒,形容憔悴。虽然大夫说并无大碍,那般神色却也极为让人忧心,只那两道士像是掐好了时间似的,第二日尚侯爷便悠悠醒转了,可尚侯爷却是两眼无神茫然地望了众人许久,才缓缓吐出几个字:“没想到……没想到……”
下人们忙给尚靖递上参汤、鸡汤,可尚靖却一口也喝不下,只将就地喝了几口小米粥,似乎也不太想和众人说话,只淡淡地说他倦了,让二老爷陪着他说说话,便歇下了。
二老爷阴着一张脸走出了尚靖的房间,只淡淡地说:“侯爷没事,你们都歇了吧,让他静养几日。”至于别的,一概也没说。
可那天半夜,莫氏仍是想了个法子偷偷溜了进去,在尚靖的床头又哭又跪:“侯爷,我们夫妻感情多年,我将尚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谅儿,您莫生气,都是我出的主意,其实我也是怕家产被他们败光,才想让谅儿收回来,好好管着缎庄,以后他们兄弟有难,谅儿定能相帮。但倘若谅儿就此倒了,只怕他们也会接连着倒了呀。侯爷,谅儿绝对不是不忠不孝之人。”
尚靖本就在咳嗽,被她这一哭一跪,就咳得更加厉害,怒道:“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莫氏却跪着抱着床头,哀泣不止,道:“侯爷,至少您不要收回谅儿手里的缎庄呀,都是我这做母亲的错,与他无干,若他没了营生,以后该如何是好呀。”
尚靖见莫氏的脸在烛光映照之下都已扭曲了,心中只觉厌恶,可又想起尚谅那张酷似自己的脸,一时不知该如何决断。那两个道士,是那日莫氏非要让他陪着去白云观时遇见的,他当时病急乱投医,也未及多想,待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打坐,觉得身体果是有所好转,就更加信任那二人,至于自己当日为何那般凑巧遇到那二人,他虽略有疑惑,却也不曾深思,只他觉得家里人即便再如何争家产,也断然不会去害他性命。
他虽然长期修身养性,可那般病也不是一时便能治得,那二人说东海仙山有医仙能妙手回春,又有圣药,他虽将信将疑,却也觉得即便不成,当作散心也是不错,况自古以来便有文人寻那东海蓬莱仙山,他就当是附庸风雅一番罢了。哪知到了所谓的寻仙山的时辰,刚启程未多久,他便被人下了迷药,扔在了客栈,尚靖一开始还有些意识,后来才渐渐入睡,醒来后也迷迷瞪瞪,只有追悔莫及。他心里头正乱,莫氏偏这时候来烦他,句句说的又是他最为烦恼的事。
可这时正逢半夜时分,外边的人多半听不见,听得见的那些人又都是“放”莫氏进来的人,因此即便尚靖喊了无数遍“你给我滚”,莫氏还是在那头哭闹不止。尚靖突然觉得极是悲哀,身边的人竟然都这般不可信任了,而最为不可信任的便是自己的枕边人,只觉自己此生已尽。
尚靖缓缓闭上眼,一摆手,道:“知道了,他暂且就先留着吧。等过后我再做决断。”
莫氏如蒙大赦,披头散发地就跑了出去,只一跑出去就想到自己这回又白费了心机,不但没让尚谅拿回应拿的缎庄,反而让尚靖更加不信任自己,便愈发觉得气恼,认为尚谦太过碍眼。
尚靖这一夜无眠,他原只是因为在外边几日未曾饮食,感了风寒,可昨夜禁不住情绪一激动,竟然病上加病,就此昏昏沉沉了好几日。这一日精神头好上一些,方把所有人都喊了进来,儿子儿媳孙子孙女满满当当地跪了一堂,尚靖这才感觉有些安慰,道:“前些日子发生了些事,你们便都当做没发生过,照旧过你们的日子。”
他刚说完,二奶奶便有些不喜,扁了扁嘴道:“爹……”
二爷忙拦住她,使了个眼色。二奶奶这才不接口,尚谅则有些喜上眉梢。尚靖将他的喜色看在眼里,蓦地心里又是一痛,又道:“只一条,你们记住,待我百年以后,你们便分家吧,这侯府,只应住着一个定远侯。”
几人又连声应了是,尚靖扫了一眼道:“谦儿留下,别人都散了吧。”
尚谅盯了尚谦一会儿,方百般不愿地走了出去,刚一走出去,便被二奶奶甩了个眼风。二奶奶掐了掐二爷的胳膊说:“你为何不让我说。爹这几日都病着哩,只怕还闹不清楚,有些人多么卑鄙无耻!”
二爷忙跺脚道:“你小声些。方才秦大夫说了,爹有心疾,禁不得气,他再如何也没把天掀了,等爹身子好些了再说。况且,我看爹那般说话,也不是不知,只是他不愿提罢了。”
二奶奶撇撇嘴,高声地嚷了一句:“偏心!”
这声“偏心”虽是在屋外说的,却钻进了尚靖的心里,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儿子尚谦,便苦笑道:“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偏心?你虽是嫡子,我自幼便最疼谅儿,若不是他惹了事,如今你又懂事许多,只怕这侯位我也会给他。这回即便他犯了这般大错,我却还想着给他一个机会。”
“人人都有所喜好厌恶,偏些也是正常的,况儿子以前实是不懂事,爹爹偏疼四弟,也属正常。这回的事,儿说句实话,虽有些不满,但也觉得再如何血溶于水,爹爹也不是那狠心之人,断然不会绝了四弟的生路。”
103
103、临终重托。。。
尚靖重重地叹了口气,道:“当年我不喜你,便是因为你母亲日日在我面前说你调皮捣蛋,可我那时年轻,没想着管好你,却只是苛责你,久了你便愈发不可收拾。我虽不知道后来你身上又发生了什么,忽然间你又变回了那个温良谦恭的好孩子,但我知道,如今的侯府,最为宽宏仁厚的便是你。我这回病得不轻,只盼我有生之年你们兄弟都能在我身边,若这回我不偏心些,只怕是鸡飞狗跳,我只求安宁,你们心里怪我便怪我吧。”
“儿子不敢。”尚谦也跟着叹了口气,尚靖老了,他看得出来,和最初见他时那个神采奕奕的俊美儒雅的中年男子不同,如今的尚靖不过几年时间便开始像个真正的老人了,尤其是这几天,犹如忽然间老了好几岁一般。
尚靖握着尚谦的手,道:“你以后,要好好,好好管着定远侯府。我再嘱咐你一事,其实我这段日子也看出来了,你四弟是聪明,可是并不是做生意的料,又心胸狭隘,只怕在生意场上也做不了多久。我虽明知他可能失败,却还想着磨练磨练他,也许会转好。尤其是,我还想再给他一次机会,看他是不是……是不是真的那般不堪……我这里还有些银子,你暂且收着,若我百年之后,他的缎庄还是不景气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