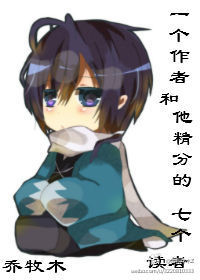七个不自由的地方 完结-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一天若斯塔和几个学生——其中一个就是吉萨家的男孩,去某个湖心小岛上练习塑石类的法术。湖并不在魔索布莱城里,而是位于穿过好几条幽暗地域隧道后的开阔巨大岩洞内。湖水其实只是一片广阔的水洼,很浅,大约只到大腿,法师学徒需要到开阔的地方练习魔法,而又不敢走得太远,所以经常来这里。而幽暗地域隧道的巡逻队也经常在这里驻扎。
“格尔,抱我过去。”若斯塔微笑着,对身边的混血奴隶伸开双手。那时候格尔觉得自己的心跳一紧,差点忘记在主人说话后应该立刻回答。
他很奇怪为什么若斯塔要这样……明明卓尔们用魔法就可以渡过河面。但他还是他点点头,横抱起若斯塔的时候胳膊几乎有点发抖。
“幸好有你在这里。我想尽可能节省法术,哪怕再普通的小法术也一样。”若斯塔搂着格尔的脖子说。
抱着主人趟过水时,格尔只敢目视前方,连低头看河里的石头都不太敢。他怕余光看到若斯塔的面孔,更怕若斯塔听到他的心跳声。也正是因为这份可笑的惊慌,让他一时没留意到刚才若斯塔说的那句话。
来到湖心高地后不久,一队卓尔战士的巡逻队从某个岩洞走来。领头的是一个女性战士,看到她,若斯塔和几个学生都拢起手欠身行礼。
“薇汀教官。”若斯塔站在最前面,微笑着对她低下头。
这是若斯塔的妹妹,家族中目前最小的女儿。她和两个姐姐不同,虽然她也在蜘蛛教院修习过,但她在格斗上的天分远高于神术,她现在任教于格斗武塔,同时偶尔会带领巡逻队。
旁人都看得出来,薇汀爱死若斯塔这个谦和的态度了。连她的弟弟耶吉尔都学不会这种应有的尊重。她得意洋洋地随便问了几个问题,然后搂过若斯塔的肩,指着蹲跪在湖边的格尔:“那是个什么?”
“混血奴隶,长得很奇怪对不对?我用它做魔法实验。”若斯塔他们都是用高等卓尔语对话。格尔能听懂,而且他觉得若斯塔说话时的神情还有点顽皮。
接着,他们又走开去谈别的,虽然能听懂语言,但很多事情格尔依旧听不明白。
巡逻队员在休息,法师们噤声站在一旁。可是格尔却发现,在和薇汀说话时若斯塔单手背在身侧,做了几个手势。
格尔看不懂那其中的意思,但明显有几个巡逻队员和两个法师看懂了,并且有所反应。
后来格尔才明白,这是一场早已计划好的袭击。目标是薇汀,而若斯塔就是主导袭击过程的人之一。
吉萨家的孩子和另一个法师与若斯塔一起负责施法对付女卓尔,早已被收买的几个巡逻队员则突然暴起对其他战士们灭口。这件事本来应该做得很完美,他们甚至已经找好了替罪羊:一个某低阶家族平民出身的法师。没有被识破的罪恶就不是罪恶,这是魔索布莱城的通则。
但是百密一疏,薇汀的法术能力不足,但她也没有别人想象得那么弱小。在愤怒中,她的某个法术击倒了若斯塔,接着她就被其他人找到机会杀死了。
卓尔对伤者并不同情,但他们还是检查了若斯塔的伤势,毕竟这是帮他们出谋划策的人。吉萨家的王子给了这位导师一点治疗药剂,幸运的是,若斯塔没有生命危险,甚至还能站起来。但不幸的是——若斯塔看不见了。
薇汀在绝望和愤怒中使用的是一个配合毒剂的法术。当若斯塔睁开眼,他本应出于黑暗视觉下眼睛失去了红色光泽,旁边的法师和战士们都知道,他看不见了。
若斯塔驱赶走那些人,实际上按照预定计划他们确实也要离开。吉萨家王子负责带走昏迷的替罪羊,临走前还象征性地安慰了自己的导师兼情人一下。
“我没事,很快就会好的。”若斯塔这么回答。
卓尔们都离开后,格尔才敢靠近过去。“主人,主人您……”他凑近,想要伸手过去,但又犹豫着这样是否不敬。
“点一支火把。”若斯塔命令。
格尔照做了。他想,大概若斯塔是想确认失去的是黑暗视觉,还是全部的视觉。点好火把后,格尔擎着它跪在主人面前,担忧地看过去。
他知道,若斯塔依旧看不见。也许若斯塔连他是什么时候点亮火把的都不知道。
卓尔们的眼睛在黑暗视觉状态下是红色,而在普通光线视觉下则是各种浅色,从灰蓝色到蓝色等等。格尔在书房中见过若斯塔眼睛的本来颜色,那是一种钴蓝色,像某种矿石,有点像小时候母亲提起天空时所形容出的颜色。
但现在若斯塔的眼睛变成了灰色。
“你点亮火把了?”若斯塔问。格尔正在他眼前挥手,虽然他看不到但能感觉得到,所以他抬手推开了那只多余地晃来晃去的胳膊。
黑暗视觉和普通视觉同时失去。这对卓尔而言简直是致命的打击。这个残酷的种族从不照顾伤残者,他们不把伤患直接处决就已经算仁慈得过分了。通常身上有缺陷的卓尔都活不长,他们会死于各种各样的意外,而无人援助。
“先带我回去。”若斯塔站在那里,向着格尔伸出手。
格尔在震惊中久久不能回过神。他搂紧主人,趟过湖水,走进藏着地底蜥蜴坐骑的隧道。回去的路上是格尔负责牵着蜥蜴,若斯塔戴上兜帽,银白色发丝垂在脸颊旁,挡住他的眼睛。
格尔有些担忧,生怕在路上出现什么危险情况,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保护若斯塔。但他也有些兴奋,因为他吃惊地发现自己之前的想法并不是错觉……若斯塔真的信任他。
回到家族的房子里,若斯塔一只手搭在格尔的前臂上,让格尔引领着他。路上没有碰到别人,回到书房时若斯塔明显松了一口气。
格尔还以为他非常冷静,但明显并不是。若斯塔现在非常焦躁,他命令格尔带着他到处翻找东西,一个接一个的在自己身上试验还能用得了的法术。
折腾了不知道多久,若斯塔叫格尔去帮他看远方纳邦德尔时柱上火光的位置。格尔重新走进屋时,看到若斯塔坐在地上,身边一堆零七八碎的魔法物品和卷轴,眼睛直直地看着黑暗深处,面无表情。
格尔避开地上的东西,靠过去跪在若斯塔面前,先回答了他的问题然后静静地看着他。
若斯塔轻轻伸出手摸到格尔的肩膀,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格尔知道,但又不想回答:“你会好起来的。你的姐姐还需要你……”
“如果我不再有用,那她很快就不需要了,”若斯塔撑着他的肩膀站起来,“我也许很快就会死,不管是死于什么事情。但只要我现在还活着,就要继续做该做的。”
你该做的是什么?格尔在心里默默问。
“格尔,我相信你,因为我也不得不相信你,”若斯塔说,“如果你依旧忠于我,我就能晚些死;如果你愿意伤害我,我就早些死。就这么点区别。”
“我忠于您,主人。无论何时。”格尔回答。
这天起,若斯塔允许格尔进入他的卧室。因为失明,他的一切都需要有人照顾,但是他不想把这交给其他卓尔来办。
薇汀死后,替罪羊也被象征性地公开处理掉,这件事很完美地结束,葛林蒂亚又少了一个威胁。
后来格尔才明白这一切的原因:这个家族的主母行将就木,而且已经在女神面前失宠。她其实根本还不算年老,但却原因不明地逐年衰弱,生命就像风中残烛。长女葛林蒂亚自己也育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次女契尔娜没有孩子,三女薇汀则有一个儿子。她们三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新的主母,而一旦新的主母确定下来,其余的姐妹要么服从她,要么死去或离开家族,主母姐妹的孩子也将不能再算作贵族。
葛林蒂亚要慢慢除掉自己的姐妹,减少最后一刻的竞争。
那天若斯塔靠在躺椅上,喝着一种在格尔的协助下调配的药剂,口气随意地讲了这些事。格尔能看出来他是站在葛林蒂亚这一边的,于是大胆地向他求证。
“是的,我……算是协助她吧。原因很多,一时很难说清,说了你也不一定能理解。”若斯塔放下杯子,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
若斯塔失去视力的消息不可能完全被保密。不久后,至少他的姐妹和弟弟就都知道了。至少他们都懒得伸手打破某个平衡,懒得做多余的事情。
葛林蒂亚对若斯塔的各种要求并没有因此减少,她只在乎他能否继续提供帮助,而不在乎他是否会因一些意外而死。若斯塔失明的原因是个大家心知肚明、但又没法说破的秘密,因此契尔娜即使面对绝好的机会,也没有主动出手除掉若斯塔——如果这么做了,反倒也许会引起她姐姐的注意。
格尔负责搀扶若斯塔去各种地方,负责为他牵着蜥蜴坐骑,甚至负责帮他梳理头发。有一次格尔轻轻笑了起来,若斯塔感觉到了,问他在笑什么。
“希望您不要生气,主人。”
“你说吧,我哪有那么爱生气。”
“我想起母亲给我讲过的故事,”当时格尔正扶着若斯塔回到书房并引导他坐下,“她给我讲起地表,地表有一种犬科动物……”
“喔,我知道那东西。实际上在幽暗地域也有类似的物种。”若斯塔说。
“在地表,也有一些人类或精灵……我是说地表妖精,因为某些原因失明……当然您是会好起来的。”
“不用安慰我。关于地表嘛,”若斯塔撇了撇嘴,“那个被大火球每天炙烤、审判着的地方,人们会失明也是理所当然的。”
格尔出生在这里,没去过地表,他也不知道若斯塔说的对不对。他继续说:“在那里,有一些失明的人会用犬只来引导自己走路,那些犬只被训练过,和作为玩赏宠物的不同,它们被叫做导盲犬。刚才我只是想起了这个,我觉得自己就像导……”
说到这里,他又把话吞回去了。本来他每天都说主人的眼睛早晚会恢复,但现在说起这个……又像是在说他会一直失明似的。
“很好,很有趣。”若斯塔伸出手,似乎是想要什么。格尔把手迎过去,若斯塔皱眉说:“头。”格尔这才把头伸过去。
若斯塔摸了摸他那枯黄打卷的头发,手上的动作情温柔得不可思议:“看来地表的生物们也很聪明,他们知道某些时候不能相信同类,宁可相信其他生物。”
格尔总觉得主人的理解有哪里不对,但又说不出。“您去过地表吗?主人?”他问,一点都没意识到自己现在说话变得有多随便。
“法师是不被允许上地表的。战士们会有机会参加地表奔猎,杀死那些妖精献祭。”
“那么耶吉尔大人上过地表?”格尔问。
听到自己弟弟的名字,若斯塔皱了皱眉。格尔意识到自己也许过于多话了。
若斯塔没有回答,而是压低声音说:“说到他。他是站在契尔娜那边的。出门时如果你发现了他,尽量带我避开他。”
“是的,主人……但是,为什么?”格尔有些吃惊。他以为这对兄弟是一个阵营的。
“契尔娜暗示过他,如果她成为主母,会扶持他成为家族中的武技长。这样他就还是贵族。而另外两个姐妹——现在只有一个了,她有自己的孩子,将来她会让自己的儿子地位高于耶吉尔。”
格尔感到自己脑袋上的手收了回去,他想


![[黑客]自由男神不自由封面](http://www.xxdzs2.com/cover/15/1505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