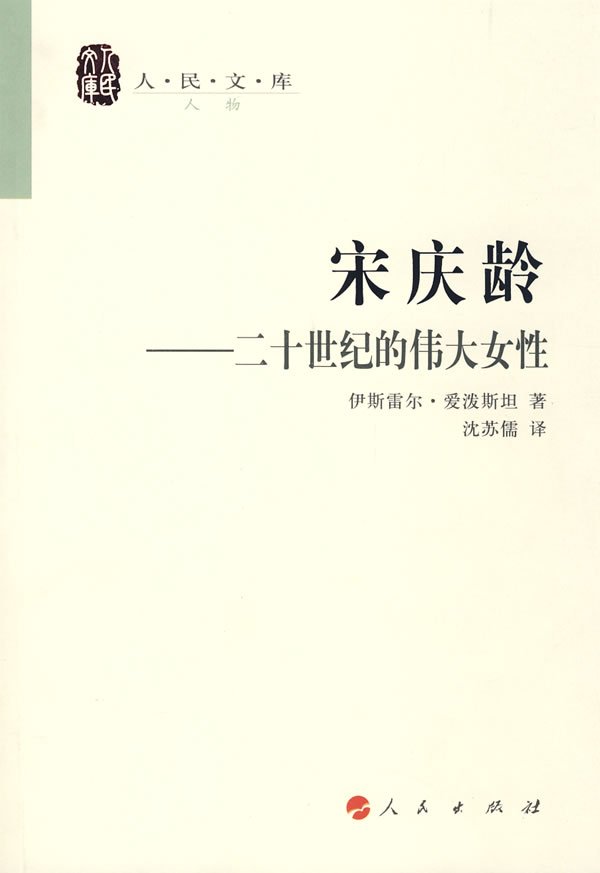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1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得意。谁知一脚才跨进房门口,耳边已听得一声‘唗’!温月江吃了一惊,连忙站住了。抬头一看,只见他夫人站在当路,喝道:‘你是谁?走到我这里来!’月江讶道:‘甚么事?甚么话?’他夫人道:‘吓!这是那里来的?敢是一个疯子?丫头们都到哪里去了?还不给我打出去!’说声未了,早跑出四五个丫头,手里都拿着门闩棒棰,打将出来。温月江只得抱头鼠窜而逃,自去书房歇下。
这书房本是武香楼下榻所在,与上房虽然隔着一个院子,却与他夫人卧室遥遥相对。温月江坐在书桌前面,脸对窗户,从窗户望过去,便是自己夫人的卧室,不觉定着眼睛,出了神,忽然看见武香楼从自己夫人卧室里出来,向外便走。温月江直跳起来,跑到院子外面,把武香楼一把捉住。吓得香楼魂不附体,登时脸色泛青,心里突突兀兀的跳个不住,身子都抖起来。温月江把他一把拖到书房里,捺他坐下,然后在考篮里取出一个护书,在护书里取出一迭场稿来道:‘请教请教看,还可以有望么?’武香楼这才把心放下。定一定神,勉强把他头场文稿看了一遍,不住的击节赞赏道:‘气量宏大,允称元作,这回一定恭喜的了!’月江不觉洋洋得意。又强香楼看了二、三场的稿。香楼此时,心已大放,便乐得同他敷衍,无非是读一篇,赞一篇,读一句,赞一句。及至三场的稿都看完了,月江呵呵大笑道:‘兄弟此时也没有甚么望头,只望在阁下跟前称得一声老前辈就够了!’香楼道:‘不敢当,不敢当!这回一定是恭喜的!’
“从此以后,倒就相安了,不过温、武两个,易地而处罢了。这一科温月江果然中了,连着点了。谁知他偏不争气,才点了翰林,便上了一个甚么折子,激得万岁爷龙颜大怒,把他的翰林革了,他才死心塌地回家乡去。近来听说他又进京来了,不知钻甚么路子,希图开复。人家触动了前事,便诌了一句小说回目,是‘温月江甘心戴绿帽’。这位喜雨翁要对上一句,却对了两天,没有对上。”我道:“这个难题,必要又有个那么一回实事,才诌得上呢。若是单对字面,却是容易的,不过温对凉,月对星,江对海之类就得了。”喜雨亭道:
“无奈没有这件实事,总是难的。”
当下我见伯述不在,谈了几句就走了。回到号里,只见一个人在那里和亮臣说话,不住的嗳声叹气,满脸的愁眉苦目,谈了良久才去。亮臣便对我说道:“所谓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这句话真是一点不错。”我问是什么事。亮臣道:“方才这个人,是前任福建侯官县知县裘致禄的妾舅。裘致禄他在福建日子甚久,仗着点官势,无恶不作,历署过好几任繁缺,越弄越红。后来补了缺,调了侯官首县,所刮得的地皮,也不知他多少。后来被新调来的一位闽浙总督,查着他历年的多少劣迹,把他先行撤任,着实参了他一本,请旨革职,归案讯办。这位裘致禄信息灵通,得了风声,便逃走到租界地方去。等到电旨到日,要捉他时,他已是走的无影无踪了。后来访着他在租界,便动了公事,向外国领事要人。他又花言巧语,对外国人说他自己并没有犯事,不过要改革政治,这位总督不喜欢他,所以冤枉参了他的。外国人向来有这么个规矩,凡是犯了国事的,叫做国事犯,别国人有保护之例。据他说所犯的是改革政治,就是国事犯,所以领事就不肯交人。闽浙总督急的了不得,派了委员去辩论,派了一起,又是一起,足足耽误了半年多,好容易才把他要了回来。自然是恼得火上加油,把他重重的定了罪案,查抄家产,发极边充军。当时就把他省城寓所查抄了,又动了电报,咨行他原籍,也把家产抄没了,还要提案问他寄顿之处,裘致禄便供家产尽绝了,然后起解充军。
“这裘致禄有个儿子,名叫豹英,因为家产被抄,无可过活,等他老子起解之后,便悄悄向各处寄顿的人家去商量,取回应用。谁知各人不约而同的,一齐抵赖个干干净净。你道如何抵赖得来?原来裘致禄得了风声时,便将各种家财,分向各相好朋友处寄顿,一一要了收条,藏在身边。因为儿子豹英一向挥霍无度,不敢交给他,他自己逃到租界时,便带了去。等到一边外国人把他交还中国时,他又把那收条,托付他一个朋友,代为收贮。其时他还仗着上下打点,以为顶多定我一个革职查抄罢了。万不料这一次总督大人动了真怒,钱神技穷,竟把他发配极边。他当红的时候,是傲睨一切的,多少同寅,没有一个在他眼里的。因此同寅当中,也没有一个不恨他入骨。此次他犯了事,凡经手办这个案的人,没有一个不拿他当死囚看待的。有时他儿子到监里去看他时,前后左右看守的人,寸步不离,没有一个不是虎视眈眈的。父子两个,要通一句私话都不能够,要传递一封信,更是无从下手。直到他发配登程的那天,豹英去送他,才觑了个便,把几家寄顿的人家说个大略,还不曾说得周全,便被那解差叱喝开了;又忘记了说寄放收条的那个朋友。豹英呢,也是心忙意乱,听了十句倒忘了四五句,所以闹得不清不楚,便分手去了。
“代他存放收条的那个朋友,本是福建著名的一个大光棍,姓单,名叫占光。当日得了收条,点一点数,一共是十三张。每张上都开列着所寄的东西,也有田产房契的,也有银行存据的,也有金珠宝贝的,也有衣服箱笼的,也有字画古董的,估了估价,大约总在七八十万光景。单占光暗想,这厮原来在福建刮的地皮有这许多,此刻算算已有七八十万,还有未曾拿出来的,与及汇回原籍的呢,还许他另有别处寄顿的呢。此刻单占光已经有意要想他法子的了。等到裘致禄定了充军罪案,见了明文,他便带了收条,径到福州省城,到那十三家出立收条人家,挨家去拜望,只说是裘致禄所托,要取回寄顿各件,又拿出收条来照过,大家自然没有不应允的道理。他却是只有这么一句话,说过之后,却不来取。等十三家人家挨次见齐之后,裘致禄的案一天紧似一天,那单占光又拿了收条挨家去取,却都只取回一半,譬如寄顿十万的,他只收回五万,在收条上注了某月某日收回某物字样,底下注了裘致禄名字。然后发出帖子去请客,单请这十三家人。等都到齐了,坐了席,酒过三巡,单占光举起酒杯,敬各人都干了一钟,道:‘列位可知道,裘致禄一案,已是无可挽回的了。当日他跑到租界,兄弟也曾经助他一臂之力,无如他老先生运气不对,以至于有今日之事。想来各位都与他相好,一定是代他扼腕的。’众人听了,莫不齐声叹息。单占光又道:‘兄弟今天又听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不知诸位可曾知道?’各人齐说:‘弟等不曾听得有甚消息。’占光道:‘兄弟也知道列位未必有那么信息灵通,所以特请了列位来,商量一个进退。’众人又齐说:‘愿闻大教。’占光道:‘兄弟这两天,代他经手取了些寄顿东西出来,原打算向上下各处打点打点,要翻案的。不料他老先生不慎,等我取了东西,将收条交还他时,却被禁卒看见了,一齐收了去,说是要拿去回上头。我想倘使被他回了上头,是连各位都有不是的,一经吊审起来,各位都是窝家,就是兄弟这两天代他向各位处取了些东西,也要担个不是,所以请了各位来商量个办法。’众人听了,面面相觑,不知所对。占光又催着道:‘我们此刻,统共一十四个人,真正同舟共命,务求大家想个法子,脱了干系才好。’众人歇了半天无话。占光又再三相促。众人道:‘弟等实无善策,还求阁下代设个法儿,非但阁下自脱干系,就是我等众人,也是十分感激的。’占光道:‘法子呢,是还有一个。幸而那禁卒头儿,兄弟和他认得,一向都还可以说话。为今之计,只有化上两文,把那收条取了回来,是个最高之法。’众人道:‘如此最好。但不知要化多少?’占光道:‘少呢,我也不能向前途说;多呢,我也不能对众位说。大约你们各位,多则一万一个人,少则八千一个人,是要出的。’众人一听大惊道:‘我们那里来这些钱化?’占光把脸一沈,默默不语。慢慢的说道:‘兄弟是洋商所用的人,万一有甚么事牵涉到我,只要洋东一出面,就万事都消了。兄弟不过为的是众位,或在官的,或在幕的,一旦牵涉起来,未免不大好看,所以多此一举罢了。各位既然不原谅我兄弟这个苦衷,兄弟也不多管闲事了。’说着,连连冷笑。内中有一个便道:‘承阁下一番美意,弟等并不是不愿早了此事,实系因为代姓裘的寄存这些东西,并无丝毫好处,却无辜被累,凭空要化去一万、八千,未免太不值得,所以在这里踌躇罢了。’占光呵呵大笑道:‘亏你们,亏你们!还当我是坏人,要你们掏腰呢。化了一万、八千,把收条取回来,一个火烧掉了,他来要东西,凭据呢?请教你们各位,是得了便宜?是失了便宜?至于我兄弟,为自己脱干系起见,绝不与诸位计较螅晷晃要乙张收条,你就那么放心我!你就那么糊涂!哼,我看你也不是甚么糊涂人!你不要想在这里撒赖!姨娘急的哭起来,又说老妈子干没了。老妈子急的跪在地下,对天叩响头,赌咒,把头都碰破了,流出血来。杨太史索性大骂起来,叫撵。姨娘只得哭了回去,和兄弟商量,只有告官一法。你想一个被参谪戍知县的眷属,和一个现成活着的太史公打官司,那里会打得赢?因此县里、府里、道里、司里,一直告到总督,都不得直。此刻跑到京里来,要到都察院里去告。方才那个人,便是那姨娘的兄弟,裘致禄的妾舅了。莫说告到都察院,只怕等皇帝出来叩阍,都不得直呢!?
正是:莫怪人情多鬼蜮,须知木腐始虫生。不知这回到都察院去控告,得直与否,且待下回再记。
第103回 亲尝汤药媚倒老爷 婢学夫人难为媳妇
我这回进京,才是第二次。京里没甚朋友:符弥轩已经丁了承重忧,出京去了;北院同居的车文琴,已经外放了,北院里换了一家旗人住着,我也不曾去拜望;只有钱铺子里的恽洞仙,是有往来的,时常到号里来谈谈。但是我看他的形迹,并不是要到我号里来的,总是先到北院里去,坐个半天,才到我这边略谈一谈。不然,就是北院里的人不在家,他便到我这边来坐个半天,等那边的人回来,他就到那边去了。我见得多次,偶然问起他,洞仙把一个大拇指头竖起来道:“他么?是当今第一个的红人儿!”我听了这个话,不懂起来,近日京师奔竞之风,是明目张胆,冠冕堂皇做的,他既是当今第一红人,何以大有“门庭冷落车马稀”的景象呢?因问道:“他是做甚么的?是那一行的红人儿?门外头宅子条儿也不贴一个?”洞仙道:“他是个内务府郎中,是里头大叔的红人。差不多的人,到了里头去,是没有坐位的;他老人家进去了,是有个一定的坐位,这就可想了。”我道:“永远不见他上衙门拜客,也没有人拜他,那里象个红人?”洞仙道:“你佇不大到京里来,怨不得你佇不知道。这红人儿里头,有明的,有暗的;象他那是暗的。”我道:“他叫个甚名字?说他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