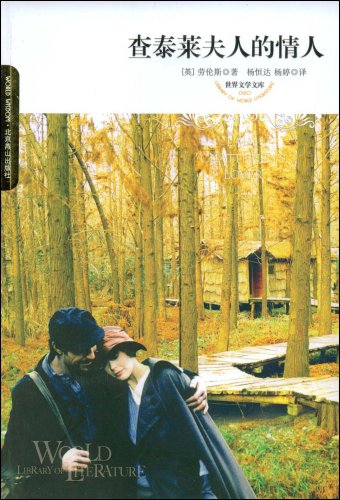野狗的情书作者:指环-第3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畎愕娜司突岷弈阋槐沧印5比唬阋部梢匀镁鸦魇稚绷宋遥灰沂苌嘶蛘咚赖簦游倚脑嗟淖爸眉词币茏坪椭芨缚删投蓟曳裳堂鹆恕N抑廊嗣谘钌傺劾锵蚶淳头指叩凸蠹鹑说拿疾凰闶裁矗茏频拿仁廊酥登?墒撬盖啄兀垦钌伲羰悄闩阄彝嬲庖痪郑闼的慊嵩趺囱。俊�
梁诺给出的三个选项,困死成一团,全都同等卑鄙和邪恶。我想叫他杀了我,放了我父亲。然而胶条让我支支吾吾,没有说话的余地,梁诺一拍我后颈,放荡地笑了,“很难以抉择?那么在杨少做出选择之前,暂且玩个小游戏如何?你看,你的小情人都已经等不及了。”
梁诺说着,又在我颈上划了一刀,“听到他血流的声音了吗,这是我给你的计时器。在最终做大题前,咱们先玩玩四个小题。杨少可千万要抓紧时间,否则我还没开枪,你的情人自己先倒,可就得不偿失了。”
“第一道题,你是愿我在你小情人左腿打一枪,还是愿意给自己左腿一枪呢。杨少,请选吧。”
我低垂着头,努力睁大眼睛,在药剂和失血的双重作用下昏昏欲睡。不知道梁诺内心原来还有这样偏执而疯狂的一面。也不知道他要挟和玩弄人的技巧,居然这么好,比他那个同样疯狂的哥哥明悦要高明得多。可是这样有什么意思呢。我尽力想摇头,提醒杨宽不要着梁诺的道。总有一种预感,梁诺的疯狂也许远不止如此。而一旦杨宽向梁诺妥协,在自己身上开了这个头,那么我亏欠他的,可能一辈子也还不清了。
杨宽沉默许久,从自己身上撕下一截衬衫,抛过来道,“蒙住他眼睛。”
梁诺配合接过,宽大布条利落系上我眼,帷幕落下了,第一声枪响。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可是从眼睛深处,不知为什么,开始慢慢涌上一层泪水。
“不错,有情有义。第二枪,右腿。我不多话,杨少请便。”
第二声枪响。我听到风擦过耳廓的温度,血腥味溅起来,惊散了澄庆湖四处的水鸟和渡鸦。
“第三枪,左手。”
第三声枪响,我感到滚烫热辣的眼泪串成一串,迅速湿透那薄薄的衬衣布条,直至滴下我冰凉的双颊。
“第四枪,唉,既然杨少只剩下一只手了,还得留着做大题,那咱们这第四枪,也就不玩儿了。想必杨少已经看出来,大题无解。但看在杨少这么有诚意的份上,我可以勉强给你一个解。”
“今天这个局面,谁死我都得死,反正我无所谓。可是杨少想必很有所谓。是让周灼死,周父死,还是将我挫骨扬灰,再看着他们俩一起死?关心则乱,杨少要操心的事太多了,选不出来了吧?那就别选了。干脆,你自己死吧。反正你是一切的缘起,你死了一切也都结了。周父能够得救,周灼不会再痛苦,我哥哥明悦在九泉之下也得安心。至于我,只要看到你子弹穿过心脏,我就束手投降。这么多狙击手,等你倒下了,他们自然不必再顾及我。放心吧,我肯定没想活着出去。”
我想阻止这疯狂的一切,大声说不要,可是已经晚了。梁诺今天巧舌如簧,超常发挥,也许这就是这个沉默笨拙男孩一直在内心默默演练的一幕,也许这就是他这一生所想要迸发的最后的华彩,总归不知为何,他表现得一直异常稳定,超出我以往对这个天真狂妄勇猛怯懦男孩子的所有认知。可是当场中变得死一样寂静,所有人都听到杨宽以不紧不慢的语调,低声叹道,“我选。”梁诺一直紧紧掐着我后肩的手,居然不可遏制地颤抖起来。在这关头,他居然怂了。
湖边最后的枪声惊散了暮色中的天鹅,我听到许多水鸟凄惨地嘎嘎作响。也许风也在那一刻变得更冷了,所有情节和故事都被冻住。当杨宽往自己胸膛射出那一枪之后,狙击手迅速出手,制服了一直嚣张不可一世的梁诺。梁诺仿佛自己也没有想到居然能够得逞,居然得逞得这么轻易,两手交叉背在身后,所有的骄傲和轻蔑都被击碎,脸色惨白,跪倒在我面前。我无暇他顾,扯开眼罩,在保镖搀扶下迅速向杨宽跑去。一切仿佛就发生在转瞬之间,我还来得及看到从杨宽唇间吐出的鲜血,他用尽最后力气冷冷朝我看了一眼,然后两个膝盖就此跪下去,再也说不出话。
我想就算时间过去再久我也会记得那一个傍晚,杨宽身体温热地摔倒在我面前,然后我将他抱在怀里,亲眼看着他身上关节节节破败,皮肤变软,直至眼睛也失去颜色,从他下摆只剩半截的白衬衣上绽开大朵血污,像是许许多多莲花,在水面冰凉一望无际的澄庆湖面前,只一个回眸就永久凋谢。
☆、第 42 章
梁诺说,周灼,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踏进了一个死局,但是我最终也没有舍得对你下手。你能不能,看在这一点情谊份上,稍微多记得我一点点?
我看着他,看了很久一会儿,他讪讪放开抓住我腿的手,被几个保镖从地上拎起来,套上手铐带走了。
随行有救护车,那之后,我和杨宽都被紧急送进了病房,我在担架上没撑一会儿就晕过去了。一睁眼就是三天后,他们告诉我这是在北京。杨宽没醒,还在重症加护病房,可是也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了。我不信,等体力稍微恢复,便扶着墙,一瘸一拐向医生申请过去看他。
不知谁也来看过他,从南半球给他带来一束花枝,上面用英文手写了几张明信片,罩在无菌玻璃罩里,神采飞扬,很是温馨。那束花枝看着像梅花也像桃花,花苞很小,骨朵分明,红红粉粉的,给干净到不正常的病房内带来了一丝春意。我很喜欢那束花,每天给它加水,闲时坐到床边,给杨宽读两页书,或者帮他翻检一下身体。由于失血过多,我的指尖现在还像瓷片一样透明,倒是床上的重症病人,状态比我要好一点,只是睡得太沉,永远不醒。
他们告诉我,子弹从杨宽身体里穿过,打在四肢的那几枪,有效避开了八成以上可能造成大范围伤害的血管和骨骼组织,手法之精准,可以作为同类绑架案教科书。至于胸口那一枪,完全听天由命,救过来是万幸,救不过来,也只能算命数。
我疑心这一切,杨宽究竟知不知情,又或者他前来赴约那天,就已经安排好了这样的结局?然而这个男人睡着了,不懂说话。我看他躺在床上,乖得谁都可以在他脸上乱戳的样子,也不再好意思拿任何话去质问他。
一晃十天半月,我快出院,正主还没醒。师兄得知我到北京,主动前来帮我收拾行李。临走前,看我欲言又止犹犹豫豫的样子,挠门问我,“你还想过来看他?”我感到脸上有点发烧。师兄叹道,“算了,想来就来吧。大不了这混球下次负你,我冲到美国,买把枪逼他为你再死一次。”“不要这样说话,”我亦步亦趋跟在师兄后面,极小声道,“他下半辈子都不知道会不会变成残废……”“祸害遗千年,”师兄横我一眼,气势如虹地单手扛起两个大箱子,在医院长廊内骂骂咧咧道,“看他还有几条命用来渣。”
话虽这样说,可我每次来医院看杨宽,师兄还是会开车载我。我给杨宽准备的礼物,师兄全都要不放心翻开来看,“什么鬼东西。”仿佛生怕杨宽这一醒来,我一不小心,把整个灵魂也拱手送出去。我说不会的,再怎么说,我也是个成年人,有自己的尊严。师兄说,“怎么不会?你贱死了!”我望着车窗前道路,愣了两三秒,然后不知为什么,忽然有点控制不住。
“怎么了,那男人不过受点皮肉伤,你还因此变成哭包了。”师兄乱七八糟往我身上砸了很多包纸巾。绕过下个路口,把车停到路旁。“师兄错了!你是我最疼爱的师弟,师兄口无遮拦,说什么都好,就是不该说你贱……”我被他那副耍宝的样子逗笑,接过纸巾,胡乱擦脸道,“没什么。杨宽在医院睡了快一个月了,老不醒,我压力大。”“唉。”师兄长叹一声,搂过我,一边徐徐开车,一边给我做了半小时心理辅导,“师弟啊,你可千万不能再犯贱了……”
“你看这北京城里,有多少外围女整容小gay将土大款捏在手心里耍得团团转,不出半年,有车有房,要啥有啥,连矿泉水都只喝进口的。偏你跟个不知道是官二代还是富二代的二代谈恋爱,就把自己这小半辈子给谈到旮旯角去了,傻吗?听师兄一句,做人得乖觉点。只要捞到了他的钱,咱不在乎捞没捞到他的心。你男人那么有钱,要复合是吧?好啊,把条件摆到桌上,直接跟他讲,先给我支付宝打几千万过来!不打免谈!等这钱到了手,咱们再慢慢地玩弄他,先玩弄他的身,再玩弄他的心……”笑得我推车门时,差点跌到地上。都走了老远,师兄还在身后冲我吼,“五千万!外加两套车!两套房!北京户口!美国绿卡!不能再少!”
幸得有师兄相伴,我到北京之后独自等待杨宽醒来的这段日子,才不至于愁云惨淡,没有一点生气。我对着镜面整理一下衣襟,踏出电梯门,忽然意识到整个医院十八层,变得前所未有地忙碌。抓个人一问,才知道特护那位终于醒了,据说主治医生又对这次案例特别重视,闹得整个十八层鸡飞狗跳。我独自缩在角落,希望等这阵混乱过去,能有相熟的医生或者护士过来带我。就在这时,走廊一角拐过几个人行色匆匆,为首的那个目不斜视从我身旁走过,又回过身来指着自己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被问得莫名其妙,摇头说,“不知道啊。”那人似乎被我这样糊涂的态度呛到,瞪大眼睛噎了一句,“那你就不懂得多关心我一句,问我一下?”“我为什么要关心,”我一头雾水,“您该不会是认错人了吧。”穿黑色中式制服的大叔估计真是什么重要人物,连续两次被我无视,快要气晕,指着我骂,“你……他怎么就看上了个你这样的!”身旁人忙扶住他。大叔平静了一会儿,脸色恢复正常,看算命看相似的,将我从头到脚扫了一遍,渐渐叹了口气,“也好,什么都不懂,一辈子才有福气。”我正琢磨着,这句话哪里不对,大叔又拍拍我的肩膀,冲我指了指病房,“那里面,有个男人为你粉身碎骨,我们希望你好好考虑,别错待他了。”
说完那伙人齐齐往前走,从拐角消失了。我站在走道莫名其妙了一会儿,有医生过来唤我名字。我跟着护士小姐,一路向他们打听病情。他们只说病人醒过一次,情况在好转,但是也不一定,你进去看了就知道了。说着将我一把推进去,加厚防菌隔离门在我身后骤然关闭,我立在病房内,茫然地转了转,杨宽躺在病床上,全身灰败了无生气的模样,再一次无比清晰地展现在我面前。
大概有人刚来看过他,床头简单地搁置了一些礼品,我伸出手,将它们一一摆好。转身搬座椅时,手肘又碰到那束旧花枝,居然已经开了。有人给它的花瓣也洒了水,在室内不充足的光线下,花朵一片片倾吐着饱满的生命力,居然是那样粉晕湿透的颜色。我愣愣看了一会,木然落座,伸出一只手,紧握住落在床边的杨宽手指,然后垂下头,看到一粒粒透明的雨水,也顺着我下巴,流到杨宽苍白的掌心和指腹上。
我用两手握着杨宽右手,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