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第15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是,皮埃尔还没有把话说完,就忽然受到了三方面的攻击。攻击他最利害的是一个他的老相识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阿普拉克辛,此人是玩波士顿牌的能手,对皮埃尔一向怀有好感。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身穿制服,不知是由于这身制服还是由于别的原因,此时,皮埃尔看见的是一个完全异样的人。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脸上突然露出老年人的凶相,向皮埃尔呵斥道:“首先,启禀阁下,我们无权向皇上询问此事;其次,俄国贵族就算有此种权利,皇上也可能答复我们。军队是要看敌人的行动而行动的——军队的增和减……”
另外一个人的声音打断了阿普拉克辛的话,这个人中等身材,四十来岁,前些时候皮埃尔在茨冈舞女那儿常常看见他,知道他是一个蹩脚的牌手,他今天也因穿了制服而变了样子,他向皮埃尔迈进一步。
“而且现在不是发议论的时候,”这是那个贵族的声音,“而是要行动。战火已经蔓延到俄国。敌人打来了,它要灭掉俄国,践踏我们祖先的坟墓,掠走我们的妻子儿女。”这个贵族捶着胸脯。“我们人人都要行动起来,勇往直前,为沙皇圣主而战!”他瞪着充血的眼睛,喊道。人群中有些赞许的声音。
“为了捍卫我们的信仰,王位和祖国,我们俄罗斯人不惜流血牺牲。如果我们是祖国的男儿,就不要净说漂亮话吧。我们要让欧洲知道,俄国人是怎样站起来保卫祖国的。”那个贵族喊道。
皮埃尔想反对,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他觉得,问题不在他的话包含什么思想,而是他的声音总不如生气勃勃的贵族说得响亮。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在那个圈子的人群后面频频点头称赞;在那个人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有几个人猛地转身对着演说的人说:
“对啦,对啦,就是这样!”
皮埃尔想说他并不反对献出金钱、农奴,甚至他自己,但是,要想解决问题,就得弄清楚情况,可是他张口结舌,一个字也说不出。许多声音一起喊叫,发表意见,弄得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应接不暇,连连点头;人群聚了又散,散了又聚,吵吵嚷嚷,一齐向大厅里一张桌子涌去。皮埃尔的话不但没能说完,而且粗暴地被人打断,人们推开他,避开他,像对待共同的敌人一样。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对他的话的含义有所不满——在他之后又有许多人发表演说,他的意见早被人忘记了——而是因为,为了鼓舞人群,必须有可以感觉到的爱的对象和可以感觉到的恨的对象。皮埃尔就成为后者。在那个贵族慷慨陈词之后,又有很多人发了言,但说话的都是一个腔调,许多人都说得极好,而且有独到的见解。《俄罗斯导报》出版家格林卡①被人认出来了(“作家,作家!”人群中传出喊声),这位出版家说,地狱应当用地狱来反击,他曾见过一个孩子在雷电交加的时候还在微笑,但是我们不要做那个孩子——
①谢·尼·格林卡(1776~1847),俄国作家。
“对,对,雷电交加!”几个站在后边的人赞许地重复着。
人群向一张大桌子走去,桌旁坐着几位身着制服,佩带绶带,白发秃顶的七十来岁的达官显贵,差不多全是皮埃尔常见的,看见他们在家里逗小丑们取乐,或者在俱乐部里打波士顿牌。人群吵吵嚷嚷地向桌旁走去。讲话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有时两个一齐讲,说话的人被熙熙攘攘的人群挤到高椅背后面。站在后面的人发现讲话的人有什么没讲到的地方,就赶紧加以补充。别的人则在这热气腾腾和拥挤的气氛中,绞尽脑汁,想找点什么,好赶快说出来。皮埃尔认识的那几个年高的大官坐在那儿,时而看看这个,时而看看那个,他们脸上的表情很明显,只说明他们觉得很热。然而皮埃尔的情绪也高昂起来,那种普遍表示牺牲一切在所不惜的气概(多半表现在声音上,而不是表现在讲话的内容上)也感染了他。他不放弃自己的意见,但是他觉得他犯了什么错误,想辩解一下。
“我只是说,当我们知道迫切需要是什么的时候,我们的牺牲就会更有价值。”他竭力压倒别人的声音,赶忙说。
一个离得最近的小老头回头看了他一眼,随即被桌子另一边的声音吸引过去。
“是的,就要放弃莫斯科了!它将要成为赎罪品牺牲品!”
有人喊道。
“他是人类的敌人!”另一个人喊道。“让我来说……先生们,挤死我了!……”
23
这时,这群贵族让出一条道来,拉斯托普钦伯爵快步从闪开的人群中走进大厅,他身着将军服,肩挎绶带,下巴向前突出,转动着一对灵活的眼睛。
“皇帝陛下即刻就到,”拉斯托普钦伯爵说,“我刚从那儿来,我认为,处于我们目前这样的景况,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蒙皇上降旨把我们和商人召唤来。”拉斯托普钦伯爵说。“那边已经有数百万人献出来了(他指了指商人大厅),而我们的任务是提供义勇军且毫不吝惜自己……这是我们至少能够做到的!”
坐在桌旁的那些大官开始开会讨论了。整个会议都非常安静。在经过先前的喧哗之后,听到老人们的嗓音一个跟一个地说“同意”,有的为了变个样,说:“我也有那个意见,”
等等,会开得沉闷极了。
文书奉命记录莫斯科贵族的决议:莫斯科贵族和斯摩棱斯克贵族一样,每千名农奴抽义勇军十名,并配备全副装备。开会的先生们仿佛松了一口气,发出移动椅子的响声,一个个都到大厅中间蹓蹓腿,随便挽起哪一位的胳膊,闲聊起来。
“皇上!皇上!”突然的喊声传遍了整个大厅,所有的人都拥向门口。
贵族们站成了两堵人墙,皇帝经过这宽阔的人墙之间的通道走进大厅。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既恭敬又畏惧的好奇神情。皮埃尔站得较远,皇帝的话听不十分清楚。他只听懂皇帝谈到国家处境的危险,谈到他寄予莫斯科贵族的希望。有一个人向皇帝报告了刚才贵族做出的决议。
“诸位先生!”皇帝的嗓音颤抖了;人群动荡一下又静了下来,皮埃尔清楚地听见皇帝十分感动的、富有人情味的悦耳的声音,他说:
“我从来就不怀疑俄罗斯贵族的热忱。然而今天贵族们的热忱仍超出了我的估计。我代表祖国感谢你们。诸位先生,我们要行动——时间最宝贵……”
皇帝停住了,人群开始拥挤在他的周围,四周都是欢喜的赞叹声。
“是的,最宝贵的是……皇帝的话。”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在后面痛哭失声地说,其实他什么都没听见,一切全是他自己想当然。
皇帝从贵族大厅步入商人大厅。他在那里逗留了十来分钟。皮埃尔和其他的人都看见,皇帝从商人大厅出来时,眼里噙满感动的泪水。后来才听说,皇帝刚一开始对商人讲话,就热泪直流,他用颤抖的声音讲完了话,当皮埃尔看见皇帝的时候,他正走出来,两个商人陪伴着他。一个是皮埃尔不认识的胖胖的承包商①,另一个是商人的首领,面容消瘦,焦黄,留一撮山羊胡子。两人都啜泣着。那个瘦子两眼含泪,而体胖的承包商像孩子似的号啕大哭,一个劲儿说:
“既要生活,也要捞取财富,陛下!”——
①19世纪在俄国向国家承包税收或承包某项专利、某种企业等等的商人。
皮埃尔此时已经没有什么别的感觉,他只表示他对任何事都不在乎和有准备牺牲一切的愿望。他想到他那带有立宪倾向的言论,就觉得犹有内疚,他正寻找机会改正这一点。了解到马莫诺夫正在献出一个军团,别祖霍夫就向拉斯托普钦伯爵说他要送一千人和军饷给他。
罗斯托夫老头含泪对妻子述说了经过的情形,他同意彼佳的请求并亲自去给他登记。
第二天皇帝离去了。所有出席集会的贵族都脱下制服,又分别回到家里和俱乐部,不时呼哧几声地向管家发布建立义勇军的命令,并对他们所作所为感到吃惊。
01
拿破仑所以要同俄国开始打仗,是因为他不能不到德累斯顿,不能不被荣耀地位所迷惑,不能不穿上波兰军装,不能不受到六月早晨诱发出的野心所影响,不能不先当着库拉金的面,而后当着巴拉舍夫的面突然发怒。
亚历山大所以要拒绝一切谈判,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受了侮辱。巴克莱·德·托利尽力以最好的方式指挥军队,是为了竭尽自己的天职,从而获得大统帅的荣誉。罗斯托夫所以跃马向法军冲锋,是因为他在平坦的田野上就忍不住要纵马驰骋,正是这样,参加这场战争的无数的人,他们都是按照各自的特性、习惯、环境和目的而行动。他们感到害怕,徒骛虚名;他们感到高兴,义愤填膺;他们发表议论,认为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并且是为了自己而做的;其实他们都是未意识到自己当了历史的工具,做了他们自己不明白而我们却了解的工作。所有实际的活动家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这样,他们所处的地位越高,就越不自由。
现在,一八一二年的活动家,他们早已退出自己的历史舞台,他们个人的兴趣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留在我们面前的只有当时的某些历史后果。
天意差使所有这些人竭力追求他们自己的目的,从而造成一个巨大的历史后果。当时任何一个人,无论是拿破仑还是亚历山大,更不用说战争的某一个参加者,对这个历史后果也未曾有一丁点儿预料到。
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一八一二年法军覆灭的原因。谁也毋庸再争辩,拿破仑率领的军队覆灭的原因有二:一是他们深入俄国腹地,却迟迟未作好过冬的准备;二是由于焚烧俄国城市和在俄国人民中激起对敌人的仇恨,从而形成了战争的性质。但是,当时不仅没有人预见到(现在这似乎很明显的了),只有这样,世界上最优良、而且由最优秀的统帅所指挥的八十万军队在碰到与自己弱一倍的,也没有经验,而且也由没有经验的统帅所指挥的俄国军队时,才能遭致覆灭;与此同时,不仅没有人预见到这一点,而且俄国人方面一切的努力经常都是妨碍那唯一能够拯救俄国的事业的实现,而法国人方面,尽管有所谓拿破仑的军事天才和战斗的经验,但却用尽一切的努力,在夏末向莫斯科推进,也就是在做使法军必然走向灭亡的事情。
在有关一八一二年的历史论著中,法国的作者总是喜欢论及与时拿破仑如何感到战线拉长的危险,如何寻觅决战的机会,拿破仑的元帅如何劝他在斯摩棱斯克按兵不动,并援引类似一些别的论据,证明与时就已经意识到战争的危险性;而俄国的作者则更喜欢谈论,从战役一开始就有一个引诱拿破仑深入俄国腹地的西徐亚人式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有人认为是普弗尔拟的,有人认为是某个法国人拟的,有人认为是托尔拟的,有人认为是亚历山大皇帝本人拟的,而且引用有笔记、方案和书信为证,其中确实有这种作战方案的暗示。但是有关预见所发生的事件的一切暗示,不论是俄国人还是法国人所为,之所以现在公诸于世,只不过因为既成的事件证明了其暗示的正确性。如果事件没有发生,那末这些暗示就会被人遗忘。就像现在成千上万相反的暗示和假设,在与时很流行,但是被证明是不正确,因而被人所忘了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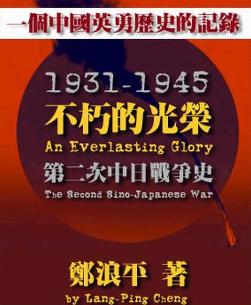


![[综漫]为了世界和平封面](http://www.xxdzs2.com/cover/2/2068.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