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第1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四幕里出现了一个扮鬼脸的人,他一面唱歌,一面挥手,直到有人抽掉他脚下的木板,使他陷落下去为止。在第四幕中娜塔莎只看到这一个场面。有一件事使他激动,使她受折磨,而库拉金正是造成她心绪不宁静的人,她一直情不自禁地注视着他。他们从戏院出来的时候,阿纳托利走到他们跟前,并把他们的四轮轿式马车叫来,搀着他们上马车。他在搀扶娜塔莎时,握住她的肘弯以上的手臂。娜塔莎觉得激动不安,涨红了脸,她回头望了望他。他两眼闪闪发光,凝视着她,流露出温和的微笑。
娜塔莎在回家后才清醒地考虑到她偶然遇到的一切,她突然想起安德烈公爵,觉得害怕,在大家从戏院回来,坐着喝茶的时候,她在大家面前惊叫一声,涨红了脸,从房里跑出去了。“我的天!我毁灭了!”她自言自语。“我怎能容许别人这样做呢?”她想道。她坐在那儿,坐了很久,她用蒙住自己的通红的脸,极力地使她自己认识清楚发生了什么事,然而,她既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也不能明白她意识到什么。她仿佛觉得一切都昏暗、模糊而且骇人。在那里,在灯光明亮的戏院的大厅里,迪波尔身穿一件金光闪闪的上衣,裸露着两腿,在湿漉漉的木板上用音乐伴奏跳舞,无论是少女们、老人们,还是裸露胸肩的脸上流露着骄傲而安详的微笑的海伦,都欣喜若狂地喝彩,——在那里,在海伦的身影出现的地方,这一切都很简单而且明了;但是目前她独自一人却认为一切都变得不可思议了。“这是怎么回事?他使我感到恐惧,是怎么回事?现在我受到良心谴责,是怎么回事?”她想道。
深夜,娜塔莎只能在自己床上把她心里想到的一切讲给老伯爵夫人一个人听。她知道索尼娅有她严整的看法,她或则什么都不明白,或则很害怕她倾诉衷肠。娜塔莎独自一人竭尽全力地解说那个使她感到痛苦的问题。
“我为安德烈公爵的爱情而毁灭了?还是没有毁灭呢?”她问自己,又带着聊以自慰的嘲笑回答自己的话:“我多么愚蠢,我为什么要问这种事呢?我究竟出一什么事?没有发生什么事。什么错事我也没有做,也没有招致这种是非。谁也不会知道。我永远不会再看见他了,”她自言自语。“显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安德烈公爵会爱我这样的人。但是他会爱我这样的人吗?唉,我的天,我的天!干嘛他不在这儿!”娜塔莎安静了片刻,但是后来又有一种本能仿佛对她说,尽管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尽管没有发生任何事,本能在对她说,从前她对安德烈公爵的爱情的纯洁性完全丧失了。她又在她的想象中重复她和库拉金的全部谈话,她脑海中浮现着这个俊美而大胆的人在握住她的手臂时的面孔、手势和温和的微笑。
11
阿纳托利·库拉金住在莫斯科,他是父亲把他从彼得堡送来的,他在那里每年要耗费两万多块钱,而且债权人还要向他父亲索取同样多的债款项。
父亲告诉儿子,说他最后一次替他偿付一半债务,只不过是希望他到莫斯科去做个总司令的副官,这个职位是他父亲替他谋求到的,而且希望他尽力设法在那里成一门好亲事。他言下要把公爵小姐玛丽亚和朱莉·卡拉金娜指给他看,作为物色的对象。
阿纳托利同意后,启程前往莫斯科,住在皮埃尔家中。皮埃尔起初不乐于接待阿纳托利,但后来和他混熟了,有时候一同去狂饮。皮埃尔以借贷为名,给他钱用。
申申恰如其分地谈到阿纳托利的情况,说他来到莫斯科后,竟把莫斯科的女士们搞得神魂颠倒,尤其是因为他蔑视她们,显然是他宁可喜爱茨冈女郎和法国女伶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立,指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据说她和法国女伶的头目乔治小姐的关系密切。丹尼洛夫和莫斯科其他乐天派所举办的饮宴,他一次也不放过,他彻夜狂饮,酒量过人,还经常出席上流社会举办的各种晚会和舞会。大们谈论他和莫斯科的女士们的几次风流韵事,在舞会上他也追求几个女士。但是他不去接近少女,尤其是那些多半长得丑陋的有钱的未婚女子,况且阿纳托利在两年前结婚了,除开他的最亲密的朋友而外,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两年前他的兵团在波兰驻扎时,一个不富有的波兰地方强迫阿纳托利娶他女儿为妻。
阿纳托利寄给岳父一笔款项,以此作为条件,不久后就遗弃妻子,取得做单身汉的权利。
阿纳托利向来就对他自己的地位、对他自己和他人都感到满意。他整个身心本能地深信,他只有这样生活下去,他平生从来没有做任何坏事。他不善于全面考虑他的行为会对他人产生何种影响,也不善于考虑他这种或者那种行为会引起何种后果。他深信上帝创造鸭子,使它不得不经常在水中生活,上帝创造他,他就应该每年挣得三万卢布,就应该在社会中经常占有最高的地位。他坚信这一点,别人观察他时,也相信这一点,他们不会不承认他在上流社会中占有最高的地位,也不会拒绝他借钱,他向在路上随便遇到的任何人借钱,他显然是不想归还他的。
他不是赌徒,至少从来不希望赢钱。他不慕虚荣。无论谁心里想到他,他都满不在乎,而在贪图功名方面,他更没有什么过失。他所以几次惹怒父亲太虚中国古代哲学范畴。①指元气本体。北宋张载《正,是因为他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他嘲笑所有的荣耀地位。他不吝啬,任何人有求于他,他都不拒绝。他所喜爱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寻欢作乐和追求女性,依照他的观念,这些嗜好没有任何不高尚的地方,但是他不会考虑,一味满足他的嗜欲对他人会引起什么后果,因此他心里认为自己是一个无可指摘的人,他无所顾忌地藐视下流人和坏人,心安理得地傲岸不群。
这些酒鬼,这些悔悟的失足男人,就像悔悟的失足女人一样,都有那种认为自己无罪的潜在意识,这种意识是以获得宽恕的希望作为依据的。“她所以获得一切宽恕,是因为她爱得多,他所以获得一切宽恕,是因为他玩得多。”
是年,多洛霍夫在流放和波斯奇遇之后,又在莫斯科露面了,他还过着邀头聚赌和狂饮的生活,和彼得堡的一个老同事库拉金很接近,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他。
多洛霍夫聪明而又剽悍,阿纳托利真诚地喜欢他。多洛霍夫需要阿纳托利·库拉金的名声、显贵地位和人情关系,藉以引诱富有的青年加入他的赌博团伙,利用他,玩弄他横流,政治走向霸道,历史趋于退化。自然科学方面亦有建,但不让他意识到这一点,除开他存心借助于阿纳托利而外,对多洛霍夫来说,控制他人的意志本身就是一种享受、习惯与需要。
娜塔莎库拉金留下一个强烈的印象。在看完歌剧回家吃夜饭的时候,他带着行家的派头在多洛霍夫面前评价她的臂膀、肩头、两腿和头发的优点,并且说他已决定追求她。阿纳托利无法考虑,也无法知道这种求爱会引起什么后果,正如他一向不知道他的每一种行为会引起什么后果那样。
“老兄,她很美丽,但不是送给我们的。”多洛霍夫对他说。
“我要告诉我妹妹,叫她邀请她吃午饭。”阿纳托利说,“好吗?”
“你最好等她出阁之后……”
“你知道,”阿纳托利说,“j’adorelespetitesfilles①,她马上就局促不安了。”
“你有一次上了petitefille②的当,”多洛霍夫知道阿纳托利结婚这件事,所以这样说,“当心!”——
①法语:我很喜欢小姑娘。
②法语,小姑娘。
“啊,可一不可再!是吗?”阿纳托利说,他和善地大笑起来。
12
看完歌剧后的第二天,罗斯托夫家里的人什么地方都不去,也没有人来看他们。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瞒着娜塔莎跟她父亲商量什么来着。娜塔莎心里琢磨,认为他们在谈论老公爵,打定了什么主意,这使她惴惴不安和受委屈。她每时每刻都在等待安德烈公爵,当天曾两次派管院子的人到弗慈德维仁卡去探听他是否抵达。他还没有来。她在目前比刚刚到达的头几天更加难过了。她不仅显得不耐烦,常常想念他,而且不愉快地回忆她跟公爵小姐玛丽亚和老公爵会见的情景,她莫明其妙地感到恐惧和焦虑不安。她心中总是觉得他永远不能回来,或者在他还没有到达之前她会发生什么事。她不能像从前那样独自一人心平气和地、长时间地想到他。她一开始想到他,他就在她头脑中浮现出来,而且还会回想到老公爵、公爵小姐玛丽亚以及最近一次的歌剧表演和库拉金。她的思想中又出现一个问题:她是不是有愧悔之意,她对安德烈公爵的忠贞是不是已被毁灭,她详尽地回想那个在她心中激起一种百思不解的可怕的感觉的人的每句话、每个手势和面部表情的不同程度的流露。在她家里人看来,娜塔莎比平常更为活跃,然而她远远不如从前那样安详和幸福了。
礼拜天早晨,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邀请客人们到她自己的教区圣母升天堂去做日祷。
“我不喜欢这些时髦的教堂,”她说道,她因有自由思想而自豪。“到处只有一个上帝,我们教区的牧师文质彬彬、循规蹈矩地供职,光明磊落,就连助祭也是如此。唱诗班里响起协奏曲,还讲什么圣洁?我不喜欢,真是胡作非为啊!”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喜欢礼拜天,而且善于欢度礼拜天。礼拜六她的住宅就清扫、刷洗得干干净净,家仆们和她在这天都不工作,大家穿着节日的服装去作日祷。老爷在午餐时加馔,也施给仆人们伏特加酒、烤鹅或烤乳猪肉。但是节日的氛围洛克(John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政治家。,在整幢住房的任何物体上都不像在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那张宽大而严肃的脸上那样引人注目,礼拜日她的脸上一贯地流露着庄重的表情。
他们在日祷之后畅饮咖啡,在那取下家具布套的客厅里,仆人禀告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就四轮轿式马车已经备好。她披上拜客时用的华丽的披肩,现出严肃的神态,站立起来,说她要去拜访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博尔孔斯基公爵,向他说明有关娜塔莎的事。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走后,夏尔姆夫人时装店的女时装师来到罗斯托夫家,娜塔莎关上客厅隔壁的房门,开始试穿新连衣裙,她对这种消遣感到很满意。当她试穿那件还没有缝好衣袖、粗粗地缭上几针的束胸,转过头来照镜子,看看后片是否合身的时候,听见客厅里传来她父亲和一个女人兴致勃勃地谈话的声音,她听见女人的语声之后涨红了脸。这是海伦的说话声。娜塔莎还来不及脱下试穿的束胸,门就敞开了,伯爵夫人别祖霍娃穿着一体暗紫色的天鹅绒的高领连衣裙,面露温和的微笑走进房里来。
“Ah,madélicieuse!”①她对涨红了脸的娜塔莎说,“Charmante!②不,这太不像话,我可爱的伯爵书》。,”她对跟在她后面走进来的伊利亚·安德烈伊奇说,“怎么能住在莫斯科,什么地方都不去呢?不,我决不会落在您后面!今天晚上乔治小姐在我那里朗诵,还有一些人也会来团聚,如果您不把您那两个长得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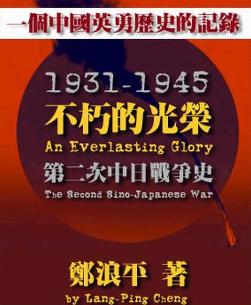


![[综漫]为了世界和平封面](http://www.xxdzs2.com/cover/2/2068.jpg)
